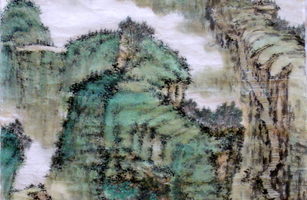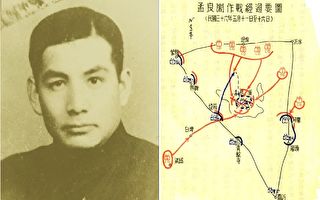这时,我已预感到又要把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拿来当“活靶子”当替罪羊了。果然,1968年7月10日,学校造反派“兵团”勒令我和一些人立即去兵团报导,这是“文革”以来,我第三次被揪出来当“草人”使用。

社会/纪实文学
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根本原因,是上层的权力斗争,群众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联想到57年上当受骗,被愚弄的教训,因此我决心“绝不乱说乱动”,甘心当个“死老虎”。
随着以后形势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醒悟,我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由此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看透了这一切,这些都是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敌刘少奇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
没有经历过那个“阶级斗争”年代、没有挨过整的人很难体会到当阶级斗争“草人”的滋味:先以阶级斗争为名把人冤枉打入地狱,然后绝不准你喊冤叫屈,叫你永远不得翻案。
花工李见喜同志(所谓有“历史问题”,文革初被揪出当“牛鬼”,后被辞退)是位约50多岁的老头,为人忠厚。我主动帮他担水、挖坑、栽花栽树,有时彼此吹点“龙门阵”,十分相投。
我们结婚时,她娘家和亲友无一人上门,不过她老母亲心痛女儿,力排众议,同意我们两个的婚事。我们结婚那天,她老人家独自一人,从她二姐家来,跟着我俩一起去南温泉玩耍了三天,这给了我俩极大的精神安慰。
因为“灾荒年”已经过去,农场的历史任务也要结束了。1962年9月20日,听说学校要招生了,又听说农场要移交给长寿县,人心浮动不安。
过年了,大家纷纷下山回家去和亲人团聚了。场里指定几个人留守,等年过了后再回家。我无家可归,留在山上。我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悲伤,谢绝了他的好意。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人的思想意识由党的意向支配着,既然党组织承认我“改造好”了,那么他们也就敢和我接近了,但是总是不大自然,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界线似的。
此时我的内心愤怒、悲痛、羞辱、屈从、无可奈何的交织在一起,痛苦极了。但是,为了生存,我在他面前不敢流露丝毫的冤屈和愤怒的表情,相反还要装出一付“改造好了”的样子。
这些病号都是在前段时期大批饿死、累死中的幸存者。好在这时劳动强度减轻了,不再像1958、1959、1960年“大跃进”放“卫星”那样不管人的死活,连牛马都不如地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