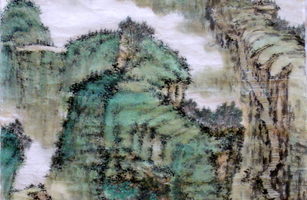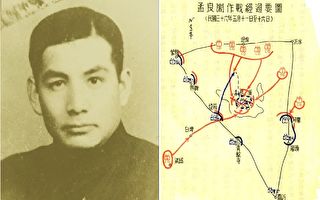真想不到“劳改”连自己照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想不到这么一件“铠甲”,竟被当成了劳改标致惹出麻烦来,也罢,比起‘破帽遮颜过闹市’来,我虽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着这“万巴衣”游一下盐源街头!

社会/纪实文学
云说:“但是那都过去了,这是现实,人不能不对现实负责而为所欲为,你的初恋女友如果对你有什么要求,或者你对她有什么过分举动,会伤害你的妻子。”
这是个冷漠的时代,只要自己的行李摆放好了,安全了,谁会去管别人怎样。我冷眼看着云气喘吁吁的擦着汗,微笑着请大家帮忙给她行李腾个位置,谁也没有反应,最后,她的行李被塞到了卧铺的床下——一个最不安全的地方。她笑了笑,跟大家说了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