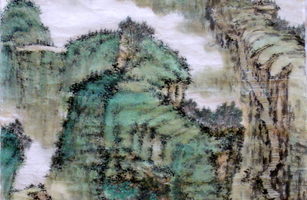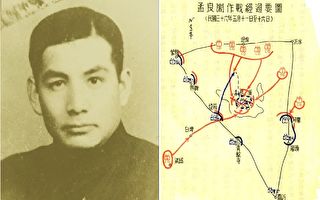在马可仕宣布自己胜利后的第二天,大量艾奎诺的支持者涌入马尼拉,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他们举行了一场“人民胜利大游行”。在这场大游行中,艾奎诺对她的支持者说,如果马可仕不让步,“我们的行动就要升级。

报告文学
第二天的公民投票对皮诺切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据当晚同时对投票进行计数的自由选举委员会的初步统计,百分之五十三投票反对,百分之四十四投票赞同。监查投票选举的国际观察员记录道,投票有秩序地进行。卫兵接到命令,允许庆祝预料中的说“不”获胜的活动,以便给镇压提供借口,但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连续数小时,政权的官方媒体对得票数避免正面答复,在内政部长告诉观众赞同票超前反对票几票之后,接着便播放美国连续剧。在天主教大学的电视台上,前内政部长贾帕与爱尔文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他平静地“定下基调:如果说‘不’获胜,世界末日也不会因而到来。”两人都同意了,看上去也像是这样的。
班.金斯利(Ben Kingsley)的电影“甘地”(Gandhi)是电影可用来教育人民、激励人们的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这一部电影对世界各地民运人士的影响之大,令人惊奇。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电视剧“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和“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对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民正产生有力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已有不同语文版本,包括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帕西文(Farsi)和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文,并且已经由卫星转播到古巴、伊朗、所有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和其他国家。
非政府机构在世界上促进民主建设,有着杰出的悠久历史。一九四一年,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kie)共同合作创建了“自由之家”,专门帮助与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的专制独裁抗争。“妇女选举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和其他民间组织,积极地促进了战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主普及运动。德国政党基金会(Stiftungen)在独裁者佛朗哥和萨拉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两国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并铺平了道路。国际劳工一贯支援民主、法治和人权,尤其是对国外的工会会员的急需,总能做出及时的回应。
和采取武力相比,虽然我们更倾向于有外援的内部非暴力民主变革,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驱赶独裁者,为民主铺平道路。举个例子,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打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并驻守军队,监视这两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正如美国企业学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说:“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国的军队。”科索沃又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鉴于米洛塞维奇在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当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准了科索沃时,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和他谈判会得到任何结果。米洛塞维奇采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办法“边谈边打”,拖延军事介入,使必要的军事干涉经费和风险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