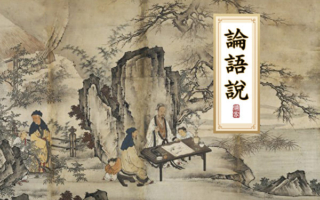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六》)
【注釋】
旅:祭名。《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按禮制,天子祭泰山,魯國君主、齊國君主亦可祭(因泰山在齊魯之境),魯國大夫季氏則無資格祭。
女:音汝。
冉有:冉求字子有,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孔門「四科十哲」之一(政事科),時為季氏家臣。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為「徐侯」, 宋璟贊:「文之禮樂,適可成人。目以政事,方為具臣。豈才不足,寧道斯屯。其謂國老,眇然清塵。」
【討論】
泰山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具有崇高的位置。按《史記‧封禪書》,歷代帝王祭祀泰山,是從舜開始的。而泰山祭祀典禮中的最高級,是封禪,不僅一般諸侯沒有資格,即使是天子,不是特別成功者也沒有資格,封禪是帝王最高的祭祀天地典禮。
然而,季氏僭越,不僅八佾舞於庭、祭祖時唱著《雍》這首詩歌來撤除祭品,甚至還要祭祀泰山。孔子當然反對。本章記載:孔子找來當季氏家臣的弟子冉有問,你不能阻止嗎?冉有答道不能。孔子道:哎呀!難道泰山之神還不及林放懂禮,居然接受這不合規矩的祭祀嗎?
前面林放曾向孔子請教「禮之本」,當然懂禮。孔子還說過「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就禮的精神而言,沒有仁義的人來祭,「神不來格」。泰山的神為大神,怎麼會享用季氏不合身分的祭祀呢!
季氏被孔子駁斥得體無完膚。(當然,說孔子亦有這層意思——以林放來勉勵冉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掉以輕心,也通。)不過,有人解說本章:孔子不責備季氏而責備泰山,溫厚婉轉到極處了。本文則以為,本章中「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無論內容還是語氣,都是悲憤的。本篇從開首的「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再到本章,內容一脈相承,文勢一氣貫注。
對古人而言,祭是國之大事。對祭的不同做法,對國家、對施政者都有重大影響。這裡舉《左傳‧哀公六年》中的一個故事來做對比。
楚昭王生了病,占卜的人說:「這是黃河的神靈在做祟,應該去祭拜河神。」楚昭王不同意,有個大臣建議:「要不,咱們來到郊外,遙遙望著黃河的方向,祭祀一下,儘儘心意。」楚昭王說:「不行!自夏商周以來的山川之祭,都只祭本土的名山大川,境外的無需祭祀。我們楚國應祭祀的是長江、漢水、雎水、漳水,黃河與我們無關。禍福的來臨,不是要經過這些川流嗎?就算我有什麼失德的地方,也輪不到黃河之神來懲罰我!」不去祭祀黃河。
孔子評價:「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昭王(約前523年―前489年)不滿十歲即位,在位期間,曾遭吳國攻伐,幾乎亡國,但能渡過難關,成楚國中興之主。楚昭王為什麼能「不失國」呢?孔子認為他「知大道」。
而對季氏,《論語·季氏》中也記載了一段孔子的著名評論,其結論是「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楚昭王和季氏為何命運各異?其中關鍵一點,是對禮——祭作為代表——的態度不同。
本章內涵豐富、深厚。現代人的思想與之相隔甚遠,但如願去深入體會,也能多有受益。
主要參考資料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四書直解》(張居正,九州出版社)
《論語新解》(錢穆著,三聯書店)
《論語譯注》(楊伯峻著,中華書局)
《論語今注今譯》(毛子水注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論語三百講》(傅佩榮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論語譯注》(金良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論語本解(修訂版)》(孫欽善著,三聯書店)
看更多【《論語》說】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