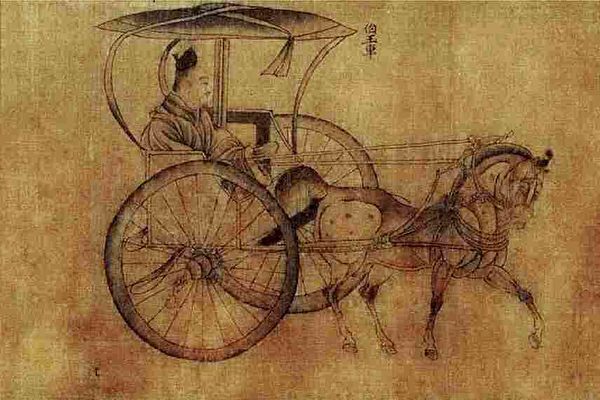「四十九年非」典故的主角叫蘧伯玉(名瑗,蘧為氏,姬為姓,伯玉為字),他是春秋衛國人,和孔子同一時代的人物。《淮南子》說他五十歲知自己過去四十九年非。
蘧伯玉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就從春秋時代的一個晚上說起。那天夜裡,衛靈公和夫人還在談天未眠。四下寂靜中,他們聽到一陣車聲轔轔,從遠趨近,一輛車子正朝向王宮這邊駛來,到了宮門外瞭望的樓臺前,車聲停了一會兒才又響起,這時車已經是進了宮闕了。
衛靈公就問夫人:「知道是誰嗎?」
夫人答說:「此人一定是蘧伯玉。」
衛靈公說:「何以知道?」
夫人說:「臣妾聽聞:蘧伯玉遵禮合節,過公門則下車、見君主之馬則撫式(*車上之橫木),表示崇敬之意。據臣妾的認識,世上的忠臣與孝子們,不會特地在人前裝模作樣標榜禮儀,也不會在人看不見的暗處違反道德準則。蘧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呀!仁而有智,事事誠敬,這樣的人即使在昏暗不明的地方也不會廢禮的,所以我知道是他。」
衛靈公就派人去看個究竟,果然是蘧伯玉。
蘧伯玉這樣的仁德君子能以德化邦,《淮南子》說他「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泰族訓》)。晉國的公卿趙簡子一度想要攻打衛國,但有人跟他說:「衛國有蘧伯玉為政。」趙簡子於是就放棄了。
蘧伯玉的仁德是天賦嗎?還是修養?

《淮南子.原道訓》有蘧伯玉「四十九年非」的名說,說他日日月月都謹慎內省己身的過失,善於懺悔遷善,今年悟到了去年作的是錯的,每年懺悔改過,「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
看到《論語.憲問》中,有一段相應的記載。蘧伯玉曾派使者去拜訪孔子,孔子請使者坐下,問他說:「蘧先生最近在做些什麽呢?」使者答:「他想減少錯誤,但還沒做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離開以後,孔子間接讚賞了蘧伯玉力求寡過的努力。
可見蘧伯玉時時以內省為念,內省而知「非」,從而改過遷善。他的仁德是透過後天日積月累的修行而來的。宋代蘇軾也向蘧伯玉的內省改非看齊:「蘧瑗知非我所師」(《次韻曹九章見贈》)。
後代就以「蘧瑗知非」比喻人不斷反省,改過遷善,重新做起的意思。「四十九年非」也成了一個有名的文化典故,例如唐人 李諒詩句:「首開三百六旬日,新知四十九年非。」就是一例。(《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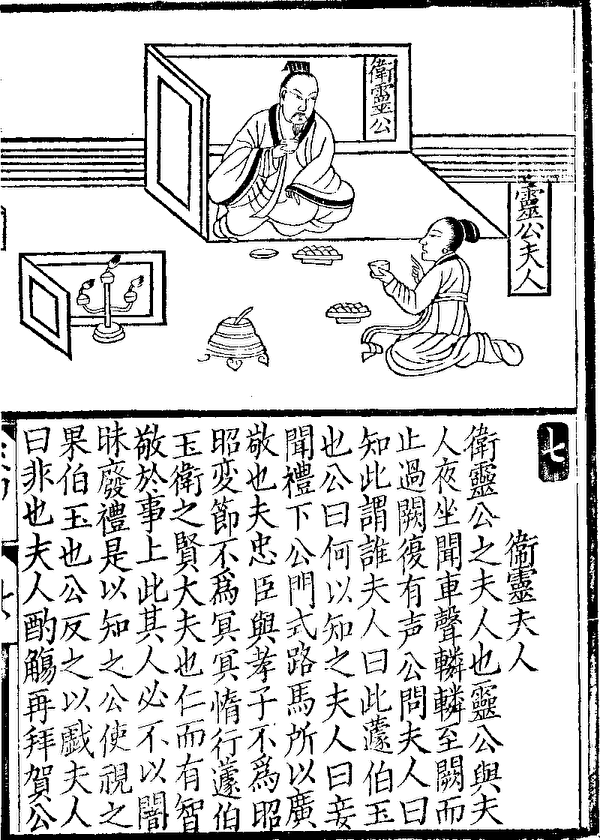
再回到衛靈公和夫人夜談的那個夜晚,故事還有精彩的後半段。
衛靈公派人查證了經過宮闕者的真實身分後,故意說不是蘧伯玉,要戲弄一下夫人。
夫人的反應也出乎他預料的鎮定。她斟了一杯酒再拜賀衛靈公。
衛靈公說:「你為何賀寡人呢?」
夫人說了:「一開始,臣妾只知道蘧伯玉這一位賢臣,現在呢,衛國又有一位和蘧伯玉一樣的賢臣,國多賢臣,是國之福,臣妾因此而賀。」
衛靈公驚歎說:「說得真好啊!」
可以看到衛靈公夫人知人的睿智,而君子蘧伯玉的品德讓她堅信不渝,更讓她的睿智灼灼發光!
隔了千百年後,唐代詩人黃滔有這樣的迴響:
流年五十前,朝朝倚少年。流年五十後,日日侵皓首。
非通非介人,誰論四十九。賢哉蘧伯玉,清風獨不朽。
(《寓言》)
日月輪流轉,時不與人遊,故而,悟道的聖人不以璧玉為貴,而珍重寸陰,因為時光難得而易失,一去不復返。人生爭先不如爭時修行,「賢哉蘧伯玉,清風獨不朽」,崇高的生命是永恆不朽的,古人說「積德」、「損德」,得到的德也將是自己生命中不死不滅的寶物。
@*#
-點閱:【成語數來寶】系列-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