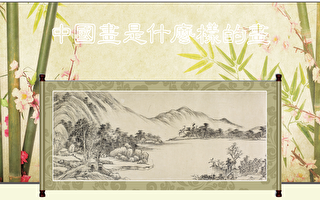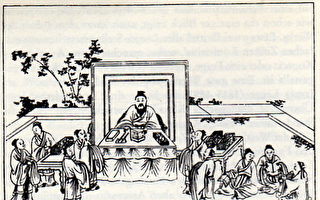上世紀中期的「二黃」現象,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黃賓虹(1865年-1955年)是頗有成就的畫家,善用宿墨,其山水畫厚重華滋。六、七十歲之前還在中國傳統繪畫的內在畫意裡面摸索,七十歲以後,他就像一隻吃飽了的獅子,在草原上盡情地撒歡兒。藝術上的超脫與自由是一個藝術的高度,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太極的陰陽理論給了這位老人足夠的畫意,他的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並用,他說畫國畫「實處易,虛處難」,是表達中國古代易、道學理念最成功、最集中、最典型的大家。
由於不去討好民間繪畫的審美情趣,很長一段時間,他的作品不被人們所接受。自古畫家多寂寥,他在世時多孤寂,少有人理解他。好心送人畫作,被人拒收的尷尬沒有讓他自卑。他自信地說,「我的畫五十年後會有人看懂」,遺囑中要求將自己的國畫捐獻給國家,可是家人幾次和浙江博物館聯繫,對方並不認可他的畫,不接受。為了一個老畫家臨終的心願,家人一再申請,博物館勉強接收,可是在黃賓虹去世三十年後,這些包裹才被打開。正如先生所說,他辭世大約五十年後,人們似乎感覺到了什麼,他的單幅畫作拍賣價格超過了六千萬元。

一直在南昌銀行工作的黃秋園(1914年-1979年),性情耿直,生活困頓,不媚時俗,不求聞達,受到地方美術界排斥,但是畫意成就極大,去世後才被人們發現畫藝了得。這位山水畫以「滿」取勝的畫家,不善言辭,不會攀附,不肯趨時獻媚,不願俯首就俗,所以在藝術界毫無名氣,沒有任何美術家協會之類的組織收納。少有的幾個朋友認定他的畫應該有一個位置,1979年,65歲的他得知有人可為他舉辦個人畫展時,竟激動得突發腦溢血,就此永遠扔下了毛筆。幾年後,人們對其山水畫逐漸激起了興趣,深感其藝術的價值,對其在世時的藝術研究資源、環境不禁扼腕嘆息。
因黃秋園鮮明的畫家個性和情懷,不願在官場、藝場渾渾噩噩,沒有為求得世人肯定而向媚俗俯首,所以其作品格調高雅,少有應酬、敷衍的畫作,在畫家群裡是很難堅持、很難做到的。滿足基本生活條件下的黃秋園,更高的追求是自己的畫境、自己的獨特的中國畫繪事語言,他的山水畫以大為多,以滿為盛,上不留天,下不留地。獨特的皴法被後人命名為「秋園皴」,為中國美術史增添了濃重的一筆。千餘年中國畫傳繼下來的構圖理論有很多的禁忌,黃秋園就像一位魔術師,一一解開這個禁忌的釦子,將全新的構圖和藝趣真誠地捧給讀者。

一些畫家、評論家都以「國有顏回而不知,深以為恥」評論說,黃秋園的山水畫有石溪筆墨之圓厚、石濤意境之清新、王蒙布局之茂密,含英咀華,自成家法。蒼蒼茫茫,煙雲滿紙,望之氣象萬千。二石、山樵在世,亦必嘆服!大陸、台灣更是將其列為自晉、唐、宋、元、明、清至近代的一百位中國美術巨匠之一。
社會性的人就要有社會性的認知和生活享受,責難畫家都像「二黃」那樣地生活,對活生生的人來說,似乎有些苛刻,本人尊重所有的藝術工作者,哪怕是在地攤用木片寫名字維持生活的人,但是作為上層的藝術和民間工藝還是有很大的距離,混亂的藝術體制縮短了這個距離,致使正統中國畫在人們心目中下架。
記得筆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學畫時,覺得學藝術很了不起,很神聖,每年幾千上萬人只錄取百十個,大學裡幾個年級大家都認識,教師和學生配備比也很小,每個人的畫風都了解,學術氛圍很濃。沒過幾年,當筆者留校任教時,教育部出台大擴招、自主解決教育經費政策。在教學設施、師資不具備的條件下,美術學院招了很多學生,一個縣級市就考來十多個學生,這些學生大多是考普通院校無望,突擊半年美術課……畢業後大多改行了。
藝術是社會運行的航標燈,是高於生活的,這個層面的人不會很多,但是會對社會文化有導向作用,它的力量是形而上的,往往和道德關係緊密,如同道家講的「虛」。大眾文化或民俗文化和百姓實際生活緊密相連,見得著、摸得到,是「實」,但是這種草根文化也是對生活要求概括和提煉,如實地再現就是實際生活,而不是藝術了,主觀的憧憬與美好的嚮往是這個層面的追求。不能寄望大眾有多麼高的審美能力和高雅的審美情趣,社會層面中「二黃」多了不一定是好事;歷來的社會文化都是在兩者扭動下運行的。一旦「形而上」的文化不能高雅,一定會使社會道德下滑,一旦大眾文化侵蝕了引領文化,這個社會便如同大海中一葉扁舟,漂浮迷航。
文化體系中的繪畫藝術能夠滿足人的主觀欲望,但是藝術不都是正面的,應該由道德的力量規範畫家的創作,否則和藝術緊密相關的道德就將下滑。作為中國人,很多引以自豪的文化正在慢慢失去,這樣成長起來的中國人的根將不純。藝術有使命「成教化,助人倫」,有良知的人都會站在天良一邊,重鑄人之為人的根本屬性,為人類的存在與新生助力!@#
(點閱【醉夢話丹青】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