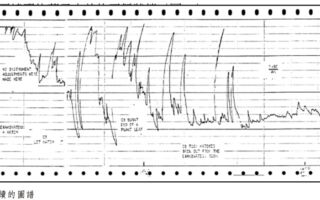【大纪元12月14日讯】
上帝的容颜
是否曾在乌云密布的门厅中显现?
而耶路撒冷
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来?
——威廉.布莱克
一
二战的死亡气息让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家阿多尔诺悲愤地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即使不了解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和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人,这句话也烂熟于胸。诗本身并不野蛮,但当罪恶已经撕碎了存在的诗意时,对 世界的“诗意描述”无异于对罪恶进行回避和纵容。诗应该做的不是粉饰,而是从生命深处出发,以剥皮抽筋的方式将对罪恶的鞭挞变成一声凄厉的呼啸。也正是在 此意义上,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对这句话作了修改:“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威辛之后 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的巨大灾难使身为犹太人的多数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深受纳粹极权主义肆虐 背后的逻辑的刺激,这个阴影出现在他们的一系列论著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启蒙”的“辩证”分析隐约可见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背景。对极权主义的敏感 使马尔库塞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的过激反应。一向理性、平和的弗洛姆也念念不忘地对希特勒这个“恋尸癖”(necrophilia)进行精神分析。在那个不能沉默的时 代,他们的表达、思考、批判、反抗达到了一个只有由痛切的耻辱感和对“人”的价值理念的持守支撑才能达到的峰巅。
二
在同样被罪恶所绞杀的这个后极权主义时代,我们说不了吗?哪怕用诗?
早就有声音说过,“xx”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更想夸张:粉饰太平是卑劣的,市民社会的肥皂剧是一种投射的心理防御机制,每个毛孔都充满了铜臭的娱乐 则是一种意淫的狂欢,借此补偿当下的耻辱状况。后极权主义时代统治的道德败坏转化为整个社会的痞化和庸俗化。在批判理论家看来在逻辑上与极权主义相通的 “文化工业”和“资本逻辑”与权力一起舞蹈,构成这个社会独特的景观。于是,没有什么是“野蛮”的,因为“生活仍在继续”。
早在层出不穷的矿难刺激下出台的“撤资令”遭到某些已没有“自我”因而早病态化为一种依赖“占有”来挽救其人格毁灭的官员表现其“宁愿丢官也不撤资”的态度时,我就说过在统治机构内已出现一种“末日心态”。就精神分析的审视而言,一个在道德的正当性上无法论证自身的人,除非存在很多同类,否则将无法通过其自设的自欺欺人的价值系统论证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以维护心理上的生存—在一般情况下,它保证自身心理生存一方面依赖于同类的存在对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论证的强化,另一方面依赖于一种论证手段的转移,即不再是用道德,而是用强力来确证自身。
一旦同类丧失,个体必被抛入一个异质的世界中, 其存在的正当性将遭受普遍的质疑,引发其更剧烈的心理危机。维护其心理生存的驱力将让它更依赖于强力的展示,并变得歇斯底里。而力量的展示因其行为更确证其存在的非正当性,它所引发的怒火又一次威胁到他心理上的生存。我们所置身的统治社会已经变成这样的一种状况,统治者恍如具有这类病理特征的个体。就统治的非正当性而言,官僚机构的腐败和黑社会化不过是这一统治逻辑的延伸,它预示一个统治机构维护自己生存的方式已经走向了它的尽头。在一个巨浪汹涌的世界里,“末日心态”支配下的官僚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船还没有沉没的时候,赶快用各种手段捞起最后一根金条。同样是在“末日心态”支配下,枪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响了—它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已撕去。
三
精神分析表明:当一个人陷于心理上的恐慌,或出现神经症的症状时,他在智力上将大打折扣。用很过分的说法就是在那种状态下,显得有些弱智或痴呆。
让我们见识一下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这个官方喉舌的弱智:
正在“热播”的一部叫《格达活佛》的电视连续剧在我看来是后极权时代愚民之作的“最杰出代表”。它继承了在中央一台播出的电视剧的那种虚伪的做作和肉麻的腔调。之所以强忍恶心看它,是因为它里面有我感兴趣的藏传佛教的内容。但是,看了几集,我几乎呕出来,恨不能砸了电视机。
电视上的那些喇嘛居然和俗人一样嬉笑打闹,偷嘴装傻,如此歪曲这些浸润了佛教精神的人的形象,不知这个电视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或者以为谁都应该和他们在以往的宣传中所塑造的“形象”一样?!而在一个活佛和某个人的对话中,居然让活佛说“异教徒”如何如何的这样的鬼话!实际上,佛教根本就没有什么“异教徒”的概念。成为一个“教徒”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一种建立在二元对立逻辑上、可以作出价值判断的教义所赋予的“身份”,而是指他可以有途径开悟,并帮助其他人摆脱痛苦。就这一点,佛教在各大宗教中的宽容忍让举世皆知,其和平主义一以贯之,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二元逻辑的破除和对各种构成“自我”的属性的抛弃上。是不是自己一贯二元对立,把别人也想像成这样了?这些人如果弄不明白,不妨做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哲学思考:一个已经破除了将自身设定为价值中心、连“自我”的逻辑都消解了的体系,会有“异教徒”这样有某种价值排异色彩的概念吗?!
令人可气又可笑的是,这些闹剧虽然利用了“文化工业”的制作程式,但好象不是用来洗脑,相反是让人的头脑警惕的。文化工业下的意识形态的虚假只是它对应的现实逻辑的虚假,而绝非其“作品”的演绎逻辑的虚假。也就是说,虽然它本质上是唤起你的虚假需要,为你制造一个可以沉醉、逃避的世界,或者将现实世界“幻化”为你的心理生活所想要的样子,但它在实现这种对你的心理的操纵时,一点也不能违背你的心理逻辑—否则它就玩不下去。而中国的“商业文化”,基本上仍处于连演绎逻辑都虚假的“文化工业”的粗鄙状态。
政治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因其“宣传”而具有的“价值判断”的内在指令使它更不必考虑这些,从而也更无耻。它要告诉你某种东西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而采用说理的形式进行逻辑演绎却有可能对这个目的进行解构,因此干脆连逻辑都不顾,而仅仅是用那些虚假的话语来构成“现实”。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恐慌”, 颇类似于恐惧症患者在恐惧刺激下为了获得心理生存所采取的一种合理化策略。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神经症患者越远离“现实”其症状也越接近精神病状态一样, 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已是纯属意淫的“合理化”了。
转自《天涯杂谈》(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