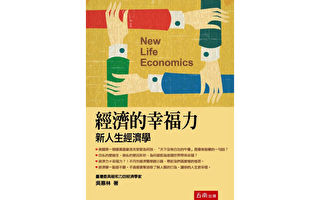【大纪元2025年02月13日讯】“独占”无疑是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据史蒂格勒翻阅1900年以前所有经济学的书籍和期刊,却发现在最近几个世纪,独占并非是严重问题。“现代经济学之父”马夏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是当时探讨一般经济学最深入的著作,但该书五十五章中只用一章讨论独占,即使他在后来的《产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 1919)这本书中,用了较多篇幅讨论独占,直到1850年时,在英国使用“独占”这个字眼,仍局限于指称贸易的排他权利,而该权利是国会赋予的特权。
“独占”问题的源起
到19世纪末,一般人对独占的关心快速提升,史蒂格勒说他记得报导在一本著名的新闻扒粪专家史代芬斯(Lincoln Stefens)所写的《城市之耻》(The Shame of the Cities, 1903)这本书中的一个插曲。该书中有一章是史代芬斯的自传,章名为《我(在纽约市)引起一阵犯罪风潮》,该场犯罪战是由两个打对台的报社记者每天在比谁写的犯罪新闻较多,在无心插柳下出现的。最后,那时的警署署长罗斯福(Therdore Roosevelt)出面劝服两位记者适可而止,恢复纽约市较守法的特色。有关独占的类似事件也曾在美国发生:一连串对贪污扒粪与改革的文章,共通地强调标准石油公司、铁路、钢铁托拉斯,以及其它成打的公司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和巨大利润的“罪行”。
经济学家应该都看了这些文章,同时也受到一些事件发展的影响:一是美国在1890年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亦即休曼法(Sherman Act),此法引出了大量有关企业组织与实务策略的文件。二是美国与英国在19世纪初都出现了大规模企业合并、形成托拉斯的热潮。三是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愈来愈多,而且都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占,“独占资本主义”在那些文章中几乎成为一个拆不开的字词,也就是没有单独的“独占”“资本主义”或“独占与资本主义”字词。
此外,“独占”这个名词的意义改变了。
史蒂格勒表示,纵观19世纪以前的历史,如果人们看到一个行业里有五家不同企业主的企业,人们就会说,这是一个“竞争”的行业。以榨橄榄油业为例,假设有A、B、C、D、E五个人在经营,他们是互相竞争的,A先生可能对好顾客提供折扣,B先生制作品质较纯的油,C先生培育果实较多的橄榄树等等。这个行业可能有和平共存的时期和激烈竞争的时期,但该行业还是被视为是竞争的。
史蒂格勒指出,每一门科学的成员持续地想对它的概念定义得更严谨,而当许多的学术界成员专职地研究该科学领域,愈有可能做到。在19世纪的后三十年,当经济成为近乎受尊重的学术主题时,此过程更加速进行。[哈佛大学在1871年任命当巴(Charles Dunbar)为第一个经济学教授,1875年授予伍德(Stuart Wood)为全美第一个经济学博士,而他后来在费城经商。]竞争就是不断地被修正的概念之一。
史蒂格勒说,一个人不必吹毛求疵就会担心,如果某个行业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时,竞争是否真的存在?为何它们不能、也不会同意订定一个利润很高的价格,尤其是他们根本不必担心新对手出现的情况下?再假想十家各自独立的厂商不太可能订定共同的价格,那么十家以上也是如此。不过,如果只有两家或三家厂商呢?
因此,经济学家相互约定说,如果一个市场里有大量的对手,就认定存在着竞争,并将该种市场称为“完全竞争”。到底多少家对手才称得上“大量”?一百家当然就足够,但有时两家就称得上多数,而为了严苛的经济分析,就假设该市场有数千家厂商。此外,也要假定所有的经济行为者,如消费者和企业家,对产品的价格和品质都有完全的认知。史蒂格勒指出,定义虽不能让我们认识真实世界,但它们的确能影响我们对真实世界的印象。假如只有拥有大量交易者的市场才叫完全竞争,而只有少数交易者的市场称为寡占(少数几位卖者的字面意义),后者不具竞争性,也不是完全竞争。
史蒂格勒表示,由于反托拉斯法的判例,使得人们对于少数交易者市场的质疑与日俱增。第一宗被美国高等法院控诉确定的案例是艾迪斯顿水管公司(Addyston Pipe)案。当时有六家制造市区供水和下水道使用的大水管公司联合订定价格。比如说,它们会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大水管工程给其中一家公司承包,一旦哥市要购买污水道水管时,六家虽然都会参与投标,但五家的标价都会高于被规划承包的那家厂商的标价。判定这种行为违法的著名判决书,是由塔虎脱(William Howard Taft,后来当过美国总统)法官于1898年撰写的。
史蒂格勒说,一件或一百件这样的案例并不足以证明当对手少时,“受限制的交易必有协议”乃是普遍、甚至常见的现象,况且这样的案例在几十年间也不超过百件。艾迪斯顿案是缘于一位被解雇的员工带走会议记录并交给司法部而起,这样的事件不会天天有。(如果真的天天有,勾结就会停止,因此,这种事是不可能天天有的。)
独占成为“原罪”
在两次大战之间,人们对独占的注意力提高了,曾经和史蒂格勒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伯恩斯(Arthur R. Burns,他必须和另一位伯恩斯(Arthur Frank Burns)共用一个信箱,后者后来当过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1932年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取了一个恶兆般的书名,叫做《竞争的消褪》(The Decline of Competition)。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1938~1941)出版了45册研究报告和三万三千页的听证会记录,指出独占的罪恶,使得阿诺德(Thurman Arnold)得以重振几近垂死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独占因此在经济学中成为普遍受到青睐的课题,其角色就像宗教里的原罪一样。不同的是,经济学家攻击独占所获的报酬高于神职人员与原罪搏斗所获之报酬。统计数字显示,在反托拉斯案中替独占那方辩护的经济学家,比政府的经济学家得到更高的报酬。这是不是显示,有原罪者总是比打击他们的卫道之士赚得更多?这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要人们背负原罪的耻辱,就要多给他们补偿。
1988年当时的一项发展,使得就算为数众多的对手,在很多情况下也较不可能出现竞争。《垄断性竞争理论》的作者张伯林,就像他书名所说的辩称,几乎所有的市场都是竞争和独占混合存在的。例如:福特和雪佛兰的车子,虽然都是交通工具,甚至销售价格一样,但它们就是不同的车子。有些人就算他们买的车比别家贵10%,还是会买他们喜欢的品牌。假如有消费者想买雪佛兰,张伯林就会认为,存在二十家雪佛兰经销商的任何一个大城市里,仍不会是完全竞争的状态。也许有的经销商具地利之便,有的业务员笑容可掬,有的业务员人种肤色较受欢迎,如此一来,就他们收费高些,消费者还是会上门来。张伯林就这么说:由于非常少的市场是买卖每件完全一样的产品,而那种市场就是完全竞争,但它们可能不存在。
史蒂格勒说,若读者认为他有点怀疑销售人员的笑容或肤色的重要性,他的确就是这样的。毕竟在大多数的市场里,商品的价格与品质系关键因素。有些人对业者的忠诚或许不是基于价格、品质与服务,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而且这些人对无法实践基本商业功能的贩卖者仍予以支持,未免太肤浅了。
张伯林穷其毕生之力都在支持、辩护和中等程度地阐释他那本由博士论文延伸而成的论著。据说他在教经济理论时,原本决心涵括价格理论的广泛课题,但最后却都集中于垄断性竞争。他创造出那个概念,但最后却受它摆布。不过,他的书在1930年代确实产生轰轰烈烈的影响,而且根深柢固地提高经济学家对类以产品的差异之研究兴趣。张伯林将其称为“产品差异性”。
在英国,独占问题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在1930年代,英国的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独占问题。1933年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夫人出版《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开启了她的事业生涯。那本书提出了一个易懂且精致的决定独占价格的理论。垄断性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各自拥护者为了争取谁是“正名”的广泛论战,帮助凸显了经济学中的独占问题。
尽管史蒂格勒并不相信,但直到1950年代以前,他仍然接受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此即“独占颇为普遍”。在制造业和矿业里,独占是主导性的市场组织中的优势形态。史蒂格勒曾经是个积极批判大企业者,倾向于支持有名的伯克(Robert Bork)法官所写的《反托拉斯矛盾》(Antitrust Paradox)里的反托拉斯政策之有趣观点。他说有个杰出的律师(此君后来成为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曾将反托拉斯法比喻成美国拓荒时期的城镇警长之传统—不查看证据、辨别嫌疑犯来破案,只是走过主要街道,时时拔出手枪殴打几个人即可。警长需要时常拿出手枪殴打几个牛仔,至于当时那些牛仔是否有惹麻烦已经不重要,因为这些动作已经提醒了整个社区法律与秩序的存在。
史蒂格勒当时所持观点的特色,可由他少数几次出席国会委员的其中一次经验来窥知一二。1950年时,勒威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研究钢铁业独占势力的次委员会之顾问,他要求史蒂格勒出席公听会作证。作证过程的对话如下:
勒威:假如我们采纳你的建议,将美国钢铁公司分割成多家公司,就能完全解决独占竞争的问题吗?
史蒂格勒:我想这样是可以解决雇主方面的独占问题,但受雇者方面还是会有独占的情况。因此,我个人希望反托拉斯法同时适用于雇主和钢铁工人工会。
主席[塞勒(Emanuel Celler)]:要把美国钢铁公司的日内瓦厂依据国界割离,并非难事,不是吗?
史蒂格勒:我想,除了政治考量外,不会太难。事实上,几乎美国钢铁公司的每个厂在未并入该公司前,都是独立的。
主席:要把日内瓦厂分割给别家公司经营,或把盖瑞(Gary)厂分割给另一家公司经营,均非难事,可是也要把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罕厂分割给他人经营吗?
史蒂格勒:我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主席:你认为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反托拉斯法案的法律结构,看看是否需要修改,好让这些寡占者的过分行为或罪恶能受到适当的制裁?
史蒂格勒:当然,这是我的信仰—由经济学者而非律师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由法条或法院的判例或反托拉斯局的行政命令来看,反托拉斯法的基本麻烦在于未能认知到,当一个行业只有、或只受控于少数几家大厂时,其市场结构必然不符效率竞争的运作。
史蒂格勒说他对那时讨论经营钢铁公司的适当方法之信心表示叹服,他之后都不敢再说他对任何行业(包括高等教育在内),拥有那样的知识。而更令他困窘的是,他不再相信他曾说过的经济学内容。
不过,史蒂格勒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规模大不会导致效率较佳的大胆推论,后来得到史实的强烈支时。假若某一个人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用一千美元买下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并将股利再持续投入,则到1986年的最后一天时,价值总额为一万零六百美元。若此人在当时将那一千美元买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各类股票,则他在同一时间可得到五万零四百美元。史蒂格勒说他真希望当时可以劝得动他的父亲,把其所拥有的美国钢铁股票卖出去。
因此,在1950年时,史蒂格勒相信,独占是美国公共政策的重要问题,要解决该问题,必须强硬地将掌控市场的大厂分割、严惩相互勾结的企业。他说他惧怕钢铁公司独占行为的辩解理由,是经济学里的传统观点,就是该行业“集中”于少数厂商。当时美国钢铁公司有30%的市场销售量,贝斯里汉(Beth Lehem)的占有率稍低于15%,瑞帕布里克(Republic)占有9%,而琼斯和拉夫林(Jones and Laughlin)占了约5%,前四家公司就占了60%的产品市场,在建筑用钢上所占的比例更高。包括史蒂格勒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这么高的产业集中会带来大量的非竞争行为,而这样的想法是来自共识,并非立基于证据。在维持这样的立场近十年后,史蒂格勒对独占的惧怕开始消退。他觉得其立场转变的理由值得详述,因为其中多数理由也影响整个经济学界,以致整体立场也有一些同方向的变化。
不必怕独占
史蒂格勒指出,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些人为私人企业说话,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就是其一,他是第一位对独占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稍具深度质疑者。这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奥地利教授颇为吸引人,很值得提一提其人其事。
在第一次大战前,熊彼德在维也纳展开颇为绚灿的学术生涯。据传他曾发誓要成为维也纳最好的经济学家、骑师和情人,但他从未达成最佳骑师的愿望。经过几次事业上的起落,包括当过奥地利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短命财政部长。熊彼德在1932年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治学严谨认真,而且相当聪明,但在谈论经济理论时喜欢装腔作势。1940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纽奥尔良召开年会,史蒂格勒才遇到他,很诚恳地跟史蒂格勒招呼,并提到已经读过史蒂格勒的一些著作,而且随即问说:“亲爱的同行,当你研读现代数理物理学时,难道不记得经济学里的一般均衡理论吗?”史蒂格勒说他忘记了当时他是否勇敢地承认他悲哀地忽略数理物理学,但他确定他没敢对熊彼德说他怀疑熊彼德对该领域知多少。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这本书中,熊彼德描绘出一幅与传统不同的资本主义过程的图像。熊彼德辩称,宾州和纽约州中央铁路公司间的竞争,或许只是偶尔发生,甚至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卡车、汽车、飞机等新型交通工具,对铁路的竞争威胁才真是大事。他是这么写的:
“重要的竞争是来自新商品、新科技、新的供应来源、新组织型态(例如:最大规模的控制单位)。握有决定性的成本与品质优势的竞争,其对既存厂商的打击并非降低它们的利润与产出,而是威胁它们的基础与生存。此种竞争比他种竞争(比如厂商之间的价格竞争)来得更有效果,有如炮轰相对于推门。……”
史蒂格勒认为多数经济学家反对这种异端观点,但对他对于独占的立场之转变却是有影响的。而另外有第二个人对他更有影响力,这个人是达瑞克特。
当史蒂格勒在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开始时常去拜访达瑞克特。达瑞克特和勒威合开一门反托拉斯法的课,他清楚的思路改变了芝加哥学派思考产业问题的方法,史蒂格勒举了一个例子说,世人当时多谣传,历史悠久的标准石油公司主要是以掠夺性策略获取主控市场的地位,比如采行贿胳对手的员工,恶意破坏对手的生产设备,尤其是在各地区削价竞争等等。削价的手法是标准石油公司在某市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贩卖,直到当地的油商宣布倒闭,洛克斐勒(John D. Rockfeller)再以怜悯的姿态买下对手。
达瑞克特不相信这样的故事,理由有二:一是价格战对胜利者而言也相当昂贵,甚至是特别对胜利者不利,因其产出和损失都超过那些小对手。二是只要价格一回升到独占价格水准时,那个市镇就会有新对手出现。有个能干的年轻同事马吉(John S. McGee),小心地查阅厚达13,500页的记录,没发现有显示掠夺性削价的证据。马吉说:“我相信标准石油公司假如有的话,并未有系统地在任何地点削降零售价来减少竞争。”相反的,该公司经常发现,把售价订得比对手高些,反而更有利可图。
史蒂格勒指出,达瑞克特研究经济学相当认真。在分析每年不同的措施(搭售、专利、维持转售价格等……)时,他都尽力找出促使生意人采用此手段逐利的理由。独占力量的运用是一个理由,但有时采用此手段是可以达到极大效率。在解释商业行为时,独占已不再扮演“几近独占”的地位(因为人们也会考虑其它理由)。佩尔斯曼(Sam Peltzman)、邓塞兹(Harold Demsetz)、特尔色(Lester Telser),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更加快独占角色的消褪。
史蒂格勒说他往往受到经济理论的影响:让我们回到五个业者的榨橄榄油业例子。假设每个业者榨出2,000担油,每担油的成本为1.6锥可马(drachma, 古希腊货币),若能以独占价格4锥可马卖出,每季可获得4,800锥可马的独占利润[2000×2.4(4—1.6)]。若其中一人能偷偷地将价格降到3.5锥可马,且掌握住最大买主大约400担油的生意,他将额外获得760锥可马[400*(3.5—1.6)]的独占利润。他会被揭穿吗?史蒂格勒认为不太容易。此人和他给予折扣的买者都没有泄露这种暗盘交易的明显动机。史蒂格勒对此问题所写的论文〈寡占理论〉(A Theory of Oligopoly)曾讨论侦察作弊的课题,结论是:作弊往往不易完全被看穿。这也就让同谋较难形成,即便能形成,但结盟力较弱。此一论点乃是延伸史蒂格勒在资讯经济学上的研究。
进一步说,事实乎肯定了这个结论。最让史蒂格勒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有人组成承销银行团准备购买和转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当德州或底特律或华盛顿核能俱乐部要债券时,系透过广告标售。有一群承销业者结合在一起,并出价99美元购买十年到期附年息5%面值100美元的该种债券(免税)。有时只有一个银行团投标,有时可能有20家银行团都参与投标。得标者再将99美元买到的债券,以100.5美元转售,则“承销者的利益为1.5美元。根据凯塞尔(Reuben Kessel)对数千种此类标购的研究,发现当20家竞标时,承销利益为14美元;当只有一家投标时,则为20美元。不过,即使是两家竞标,利益则由20美元降为17美元;若有三家竞标者,又降为16美元。这就是说,即使只有一家或两家对手,该利益也出奇地接近竞争的水准。所以,就算是只有少数几家独立的厂商,竞争还是很难被压制的。”
竞争是坚硬的杂草
史蒂格勒于是认为,不管是因为上述因素或其它理由,愈来愈多的济学家开始相信竞争是坚硬的杂草,而非细致的花朵。这样的观念转变发生在先,后来才出现在美国市场的强力国际竞争,比如汽车、钢铁之类的行业。这种国际竞争或许更强化了“独占是普遍存在的”论点。因此,人们对反托拉斯的热忱减弱了,尽管那种热诚还未消失。当时,史蒂格勒开始在几件反托拉斯案中以专家身份出庭作证,其中包括1982年摩比石油公司(Mobil)企图买下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这个案子。
反托拉斯案例通常是难以置信地耗时又花费庞大的,但掌控多家公司的出价却很快,假如被相中的公司反对让渡,不管是要求较高的价格,或是要保护原有公司干部的工作机会,它都会请求法院签发强制命令,阻止掌控企图,而摩比—马拉松案的审判只花了一个星期。这个案子的最大症结在于:摩比和马拉松同为中西部数个州的汽油大批发商。如果这些州单独或联合地来看,为不同的市场,则合并“可能”伤到竞争;假若这些州皆为广大的中西部市场之部分而已,则合并不可能降低竞争程度。史蒂格勒作证指出,这个石油市场远大于这些受影响的州。而另一位名教授则作证唱反调。史蒂格勒的看法主要基于底特律、芝加哥和纽奥尔良三地批发价格的变动趋势一致。如果买卖者无法经常变换交易地点来买低卖高,这三个城市的价格为何如此相似?也就是说,这三个城市是属于同一个市场。另一方的经济学家则争辩说:买者就是无法在别的地方价格较低时,跑到那儿去买。可是,他们并不能解释何以价格的变动如此相似。
法官判定摩比输,这也等于判定史蒂格勒输。史蒂格勒感到苦恼,他说他的难过可能来自虚荣心作祟,但实在也有一点利他成分在内。因为美国钢铁公司也有意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但出价比摩比低了十亿美元,因此,马拉松股票持有人(史蒂格勒表示他不是其中之一)是此判决的真正输家。史蒂格勒愤愤不平的说,让被相中的公司得以选买主,使其干部受益而股东受损,就是反托拉斯法政策的一项目的吗?事实上,反托拉斯政策经常、甚至是有增无减地导致如此不当的结果,是保护了而不是挑战低效率的企业。而且,反托拉斯法己成为律师们打猎的证照,胜诉的案件还可请求受损额的三倍补偿作为奖励。
反托拉斯法是律师们打猎的证照
史蒂格勒特别要大家看一下民间反托拉斯的行动:有一位在波士顿地区的加油站主人,为所有的加油站主人的利益控告主要的石油炼油厂。他的控诉内容为,他在德士古(Texaco)的加油机(帮浦)中,只能卖德士古的汽油,不能卖其它公司的汽油,如此剥夺了他选择竞争的供给来源之机会。
史蒂格勒认为这个案例完全没有优点。若依原告的意见,则德士古公司根本无法监控透过它的加油机所卖出汽油的品质,因其品质会因每次储油槽的汽油来源有而有所不同。德士古这个商标是“品牌”(generis),较适当的名字是“未烙印品牌”(maverick)。德士古对于经由它的加油机所卖出的汽油负有责任,尽管德士古无法完全控制汽油品质。再者,该加油站主人并不是受到德士古的胁迫,才在他的加油站中只拥有德士古一家的加油机。并没有明显的障碍使他不能转用其它较有名或较无名的品牌,也没有证据显示炼油业者间在品牌使用权的契约条款上相互勾结。所以,史蒂格勒深信被告们是站得住脚的(史蒂格勒是其中一家公司的顾问)。不过,炼油业者担心没经验的法官会做出难以预测的判决,因此他们中途就丢出小毛巾认输(拳击赛中提前认输的做法)。他们赔了三千万美元,大致上由二十位律师与二十万个加油站主人分。
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可能上演许多次,因而史蒂格勒相信,管理民间反托拉斯法案件的法律应该有所改变。至少必须强制这些同阶级共同行动的原告,在被告嬴得诉讼时负担被告的诉讼成本,这样做就可大幅减少胜诉概率不大的案件来搅场,且大大降低诉讼件数。
上一章已讨论过史蒂格勒认为敏斯这位经济学家,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对经济思考的显着影响力。到1950和1960年代,史蒂格勒仍认为,敏斯对美国一般民众与经济学界,在思考有关美国经济究竟是如何运作上,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敏斯对下列四个问题给了这样的答案:
受制于大公司的行业会不会在景气衰退时降低价格?
答:通常不会。
大公司的前途系由干部控制,抑或由股东掌控?
答:干部。
美国人大部分的财富是掌控在两百个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手中?
答:是的。
实证上,我们如何确定一个产业是竞争或独占?
答:以它对产出的控制集中度来评估。说得更具体点,就是看它的集中比率:该行业中四家最大公司的销售占有率。假如这个比率相当高(如75%或更高),则此产业可能不是竞争的型态。
史蒂格勒说,前两题的答案虽并非敏斯首创,但他当然是每题答案的最有影响力说明者。史蒂格勒表示,虽然他相信这四题的答案都是错误或严重误导,但这些答案就是他作证时所回答的。
史蒂格勒说他和敏斯意见不同近十年的课题,就是上提的第一个命题,也就是“价格是由大公司单方面决定,一旦决定后,不论制造成本改变或对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价格都会一直停在此水准颇长一段时间。”这个论点是1935年首度出现在提报给农业部长华列斯(Henry Wallace)的备忘录中,稍后即由美国参议院出版成《产业价格及其相对僵固性》(Industrial Prices and Their Relative Infexibility, 第七十四届国会第一会期第十三号文件)。上一章已提过,敏斯将1932年至1940年的经济大恐慌时期的严重程度,归咎于价格体系无法在价格管理的新世界中有效运作之故。
史蒂格勒表示,在1940年代末之前,有很多经济学家跟他一样怀疑这种说法,但直到1950年代,敏斯以类似的论调,企图解释通货膨胀的出现之后,他才忍不住驳斥敏斯的理论。敏斯说明通货膨胀时辩说,巨型企业之所以抬高价格只是单纯地要增加利润,它们乃是利用企业的大规模及市场力量所赋予的订价上之“自由决定空间”(Zone of discretion)。这个论调受到参议员凯发佛(Estes Kefauver)青睐,因为他自1957年起所举办的一系列听证会中(司法委员会反托拉斯及独占次委员会第一部分)攻击大企业的工具。在那段期间,敏斯成为作证的明星学者,他利用漂亮的图表解释1953到1957年间价格的提升,只是受到价格被操弄的产业提高价格所致,也就是说,大公司冷静决定的价格根本不理会供需状况。
不过,史蒂格勒说他一直怀疑价格僵固性的存在,而他在不久之后,就获得一个机会去进行检测。那是他成为联邦政府物价统计委员会的主席(此委员会是在1959年由当时的预算局之要求而成立),该委员会专门研究“趸售物价”,这是敏斯的研究发现之基础。一个由麦克阿里斯特(Harry E. McAllister)所做的研究发现,买者所实际支付的价格是相当有弹性的,而且还常常变动,这都是相对于卖者呈报给物价搜集单位(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而言。这个证据和其它数据让史蒂格勒肯定地推论说,没证据支持敏斯对通货膨胀的解释。他又说,如果依敏斯的作法,应用于1957年以后的资料,将观察到:某个公司的价格上涨率以及管理价格的存在程度,或某产业销售额中几个大公司的占有率之间,是负相关而不是正相关。
史蒂格勒说他记得,大概就在这个时期,他和敏斯在经济发展委员会举办的一场会议中相遇,敏斯对史蒂格勒说:“我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笨。”当时史蒂格勒大吃一惊,之后竟然忘了他当时结结巴巴地究竟回答了什么。史蒂格勒说他希望当时没有认为敏斯是愚笨的,就像他之后绝对没有这样认为一样。他补充说:“真的,一个蠢货怎可能犯下如此重大且成功的错误?”
由于价格体系的本质对经济学家以及经济体系的运作相当重要,史蒂格勒乃回到价格的研究,实际上是由寻求重要价格数据的企业所赞助。史蒂格勒劝诱金道尔(James K. Kindahl)离开Amherst学院,两人两年间走访各大企业,询问它们十年来的“购买”价格。他们之所以选择购买价格而不选销售价格的理由是,如果某位业者对顾客收取较低的价格,则他可能会被控以罗宾逊—派特门(Robinson-Patman)法案中的价格歧视罪,但以较低的价格承购者则可免责。他们的研究成品取名为《产业价格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Industrial Prices),于1970年由国民经济研究中心(NBER)出版。他们在书中辩称,他们的证据足以显示,真正的价格反映市场需求减缓之程度,趗过官方的劳工统计局所公布的价格资料(那些大部分是订价,并非实际交易价格)。敏斯强烈且重复地否认该研究推论的正确性。当1982年一场为庆祝现代公司(The Modern Corporation)成立50周年的研讨会,在史丹福大学召开时,敏斯仍以他一向的充沛力现身卫护他原始的假说。
史蒂格勒认为,敏斯的学说在经济学里受到的支持,不及它们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受到支持的程度。不过,敏斯学说的持续存在,正是它们能嬴得主导的政治思想的喜好之关键因素。史蒂格勒表示,这种说法是公平的。毕竟某个概念一旦广被接受,就保证有某些程度的不朽性,其受欢迎程度的降低,往往是大家兴趣转移的结果,较少是因为提出相反的证据所致,而且不论该证据是多么的具有说服力都是一样。
(待续)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