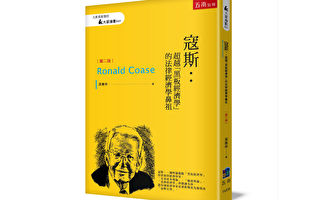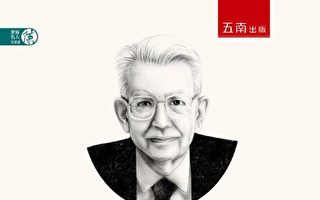【大纪元2025年01月31日讯】“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顾名思义,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onald Coase,1910—2013年)的理论,如今已名闻遐迩、大家琅琅上口,即便其真意或许不那么地被真懂,而且其出现也经过一番的波折,有意思的是这个名称还是史蒂格勒命名的呢!
万岁!我找到了!
史蒂格勒指出,科学的发现常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探索才产生的,在其背后总有许多漫长却走不通的死胡同。半熟的概念形成假说,而更生涩的概念要克服马上会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像阿基米德(Archimedes)那样,突然想到一个伟大的概念就大叫“万岁!我找到了!”是难得一见的英雄。史蒂格勒的专业生涯都是在一流学者的群体中度过,但只有一次经历到类似阿基米德那样突发的狂喜表态,而且他还只是个旁观者呢!
话说1885年到1924年,在英语系世界里,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夏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夏尔是一位具有丰沛想像力和奇思怪想的人,开创了很多课题,包括“外部性经济”——这个东西会影响一个企业,却不会受任何一个企业的明显影响。例如:假设在一个区域有三十个煤矿,假如它要进行开采的话,就要用帮浦把水从较低的竖坑中弄出来。若这片土地有很多相通的孔,若其它的矿坑以帮浦排出越多的水,自己的矿坑就可以少抽些水,可是,没有“一个”煤矿以帮浦排水的行动会显著影响水位。因此,越多煤矿坑进行开采,每个矿坑抽出的水越多,任何一个煤矿抽水的成本就越低。
马夏尔是“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在剑桥大学的“教授”头衔是由庇古(A.C. Pigou,1877—1959年)承继而来。庇古在他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这本名书里,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由于没有一个煤矿的抽水会对这地区的水位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每个矿坑的所有主在决定要抽出多少水时,会忽略它的抽水行为对其它煤矿的好处,因为他没有分享这些好处。所以,从整个产业来看,抽水会抽得太少。庇古于是建议,这类的“外部经济”可由政府补贴,譬如给每个煤矿主10%的抽水成本。
相反地,“外部不经济”通常是以一个排放黑烟的工厂来说明,该工厂所排放的黑烟会使邻近的一千户人家每户每年多花费十美元的洗衣费。庇古乃建议政府对这家工厂课税,或更正确地说,对该黑烟课税。最理想的结果或许可以减轻一半的黑烟排放,从而带给邻近住户五千美元的利益,但只增加该工厂三千美元的花费去减少一半的黑烟排放。
这种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其导致私人和社会利益的不协调,早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真理。经济学家接受这个真理的方式,就像他们接受供需决定价格的主因一样,本能而且毫不怀疑地接受。所以,当1960年寇斯在一篇精妙地分析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的管制不当的论文里(这篇论文被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极度称赞为“论文范本”),相当不经意地批评庇古的理论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寇斯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竟然会犯如此明显的错误。由于该文投稿到芝大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编达瑞克特(Aaron Director)虽认为该文杰出,但对寇斯的论点存疑,于是询问多位芝大经济学教授,大家都有同感。达瑞克特将所有的反对观点都转达给寇斯,但寇斯坚持己见不认错,坚持不改,这样的书信往返很多次,最后寇斯回信说:“就算是我错好了,你也不能否定我错得很有趣味,那你应照登吧!”达瑞克特回信说:“我照登是可以,但你必须答应在发表之后,到芝加哥大学来做一次演讲,给那些反对者一个机会,亲自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寇斯回说:“演讲是不必了,但假如你能选出几位朋友,大家坐下来谈,我很乐意赴会。”达瑞克特乃顺从寇斯,邀请近二十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和寇斯,在某个晚上会集在达瑞克特家里,由他请客吃晚餐。饭后大家坐下来,由寇斯先发言,他要求大家暂时假设,世界上没有交易成本。史蒂格勒认为这要求是合理的,因为经济理论家跟所有理论家一样,都习惯于(其实是被迫的)处理简化的,因此常是不实际的“模型”和问题。不过,史蒂格勒说,零交易成本仍是一个大胆的理论架构。比如说,零交易成本意含,购买汽车时,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经销商的售价(对任何人而言,没有时间或金钱的成本),那么,每个人都可以非常确定所有保证包换有缺陷零件,或提供服务的真正内涵,而且也对保证的执行具有充分的信心(没有争议)等等。零交易成本意谓这个经济世界没有冲突或暧昧。
接着寇斯要求与会者推论,在这样的抽象世界哩,将没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史蒂格勒猜测,他们没有太多争论就接受了这个推论。上述例子的三十位煤矿主可拟订一份契约,注明每个人应抽多少水(或予适当补偿),使该行业的利润最大。既然明订契约的会议和执行这个契约没有成本,这个结果自然是可能的。事实上,就算有三千个煤矿主,这种会议还是免费的。在零交易成本的国家中,律师将会消失。
不过,寇斯要求与会者也相信,在零交易成本里的第二个命题:不论谁承担法律上赔偿损坏的责任,或不论谁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都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使用方式!史蒂格勒他们强力反对这种异端说法。史蒂格勒说,跟平常一样,弗利曼说了最多话,也思考了最多。该场历时两小时的争辩,从原先二十位反对,一位赞同寇斯的观点,竟然转变为二十一位赞成寇斯观点,没人反对的局面。史蒂格勒感性地说:“这真是令人愉悦的交谈!”也在事后对于他们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把它录音下来,大叹可惜。
该场辩论由寇斯举出的一个栩栩如生例子开始:一个牧场主人与谷物农夫为邻,有时牧场的牛会侵入毗邻的农地,因而破坏农人的谷物。究竟是牧场的主人要赔偿农人的谷物损失,或是谷物的主人要自负损失,这对牧场的养牛数量和谷物的产量,是否会有差别呢?寇斯的回答是:“不会”!
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寇斯的答案似乎有道理,那就是让谷物农地和牛只牧场都是一个人拥有,再问所有主会怎么办。这位单一的所有者应会结合两种事业,俾达到最高利润。譬如,若增一头牛会使养牛的利润增一百美元,但会降低谷物利润一百二十美元,他就不会增养那一只牛。同样地,若围起一个篱笆,在其使用年限里,能节省谷物损失的价值抵得上围篱笆的成本,他就会建一个围篱。如果牧场和农场分属两人,他们也可以利用契约达到那种最适状况,而他们之所以会同意这样做,就是因为这样会让他俩可以瓜分一个更大的利润饼。推定谁承担谷物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只是决定谁要给付给谁的分配问题,并不会影响农地的谷物种植和牧场的牛只饲养之最适方式。
“寇斯定理”出炉
史蒂格勒希望这一个命题经解释一次后,就会显得合哩,甚至会变得极其浮显。该命题是:当没有交易成本时,法律上产权的指定对经济企业中资源的分配没有影响。对于这个命题,专业的经济期刊还是刊登了相当数量的“反驳”论文。史蒂格勒宣称,是他将这个命题命名为“寇斯定理”的,迄今已脍炙人口、广为人知。由于科学的理论很少依据第一个发现者命名,所以,这是正确的归属贡献者给首创者的罕见例子。
回到现实世界来,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为“零”的,即使是简单的交易,如美元兑换德国马克,也要交易值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成本。若你将一美元兑换为马克,再将马克兑换为美元,你若能剩下九角六分就算幸运了。若你将一千美元兑换为马克,再兑换回美元,就会剩下九百六十美元多,因为愈大笔的交易,手续费相对低。兑换现金是需要成本的,观光客必须支付。不过,寇斯定理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交易成本的大小限制了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程度。
如果你不是经济学家,很可能会说,寇斯这个论点是蛮漂亮,但有什么令人兴奋的呢?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其实是很难达到的环境,或者说是现实人间根本没有的,哪里还会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呢?史蒂格勒要大家想想看,一个社会如果质量定律不再运作,而且每咬一口就缩小体积,那将可能产生哪些古怪的事情!
史蒂格勒说他必须公正地说,怀疑寇斯定理有啥值得兴奋的,是有几分道理在的。他说:“理论家喜爱新而奇怪的架构,用以创建一个新的世界或改变看待当前世界的方法。”在1980年代末,学人们已开始研究“交易成本”的本质和大小,那是过去应做而没做的。不过,在寇斯定理公开后大约三十年间,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出奇地少。史蒂格勒认为,值得为寇斯定理兴奋的理由有一些不同:这个精巧作品立即改变人们看待和研究许多层面的经济问题的方式。史蒂格勒举了一个例子。
他指出,职业棒球的“保留”条款长期以来让球队控制职棒球员自由转队的权利(该条款在当时已删除了)。该条款意谓着,如果某个球队成功地首先和某个未来明星签约,该球队就可以说该球队能够永远留住他——即使他转去别队可能会更有价值(就门票收入而言)。寇斯定理告诉我们,这种说法是错的,球员还是会被卖到他最值钱的球队去。因为契约的协商并不是太难的事,而新旧球队和这个球员都会因该球员转队而获利。保留条款只是影响到该球员能分到多少他对门票收入的贡献,保留条款并不会让他待在错误的球队里。
寇斯定理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棒球员的契约这个例子,史蒂格勒认为应该可以说明它使人兴奋的本源。寇斯定理出现以后,人们看待很多问题的方式是改变了。人们希望知道,经由协商是否可以找到双方都能获益的解决方案。而寇斯定理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史蒂格勒认为,已经引起广大的效果。他说,想想法律诉讼解决争论的做法:为什么对契约有争议的双方不进行妥协,从而节省双方必须为诉讼所作的花费?而事实上,一般而言,争议双方通常会互相妥协,只有一小部分的争执会对簿公堂。大部分的法院诉讼案件,都缘于双方预估胜诉的可能性时,存在很大差异所致。当事实和法律条文都很清楚时,诉讼案应该会在审判前解决。因此我们并不讶异看到,寇斯定理渗入卓越的法律学院,并在课堂和法律期刊上引起莫大的注意,且被广泛运用到民事、财产和契约等方面。寇斯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正是他这个天才的适当归宿。
史蒂格勒认为,开创性通常是要用新的方法来看待熟悉的事情或想法,他对经济理论的最重要贡献,自己认为或许是把资讯当成是有价值的商品,可以生产、也可以购买。史蒂格勒之所以对资讯问题的研究感兴趣,是起源于他注意到——就好像历史上每个购买者都会注意到——一个人可以货比多家,从而买到较便宜的东西。但是,经济理论里的标准定理,是假设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在一个市场里只有一种同质的财货和一种价格。这个定理只是简单地指称,买卖双方都会探询价格,且排除价格上的差异。例如,只要有一个卖者愿意接受比买者想付的更低价格时,这位买者就会找他买。为了让这个定理得以适用于可观察到的价格差异——即使是同质的产品(比如三十家五金店对某个特定工具的售价)也有价格差异,史蒂格勒探索人们完成搜寻更好的价格之障碍,终于在资讯成本中找到答案。要发现每一位卖者的售价和他所提供其它服务的品质,如充分的存货和退换瑕疵品的迅速成度,必须花费时间和交通成本。这项结果可以说是寇斯的研究成果之补充说明,因为史蒂格勒考虑了交易成本的主要成分,且事实上,他的文章跟寇斯的文章大约是同时出现。
资讯理论的开创
资讯这个角色,在经济理论里早已快速扩大。曾经有一年出现了十二篇以上的文章,讨论当一方(如卖方)比另一方(买方)拥有更多的产品品质资讯时,会产生哪些问题。艾克罗夫(George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柠檬”‧(lemons,意即次级品)理论。该理论是说,假设只有二手货汽车的卖方才知道车子的品质,潜在的买主将会正确地假设劣等品质汽车所有者,才会特别想要卖掉他们的车,所以这些潜在买家只会愿意支付最劣质汽车的价值之价格——这样一来,只有最劣质的旧车才会卖到二手货市场。(这种不好的循环是可以打破的,如卖者设法取得值得信赖的品质保证。)
曾是史蒂格勒学生的奈尔逊(Phillip Nelson),把资讯理论作了基础性的延伸,运用到广告行为上。他证明所谓的“金字招牌”广告招式(“我们公司是这行业里最老牌或最大者”)就是要对顾客提供值得信赖的保证:这个公司一定对待顾客非常好,不然他就不会有这么多老顾客了。而经济学界在讨论促销广告上,已经比过去数十年细腻许多了。
由于科学的发现通常起源于,以不同的观点看待熟悉的现象,所以,很多科学理论会由几个人各自不相干地发现。时常发生的情形是,先驱的研究领域碰到障碍,而该领域的数位学者可能都会找到解答。的确,即使是这些多重发现者,也可能只是再次发现者而已。譬如说,1871年时,杰逢斯(W.S.Jevons,1835—1882年)和孟格(Carl Menger,1840—1921年),以及三年后的华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年)都指出,消费者行为可从每个人会努力运用他的资源购买财货以获取最大的满足(边际效用理论),来加以了解。这个观点导入经济学后,产生了所谓的“边际革命”。史蒂格勒说,有一位可怜地遭忽略的德国小公务员哥森(Heinrich Gossen),早在他们十七年前,就已经用较好的方式提出了这个理论,而且还有其他更早的前辈呢!
创见者的争执
在此情况下,谁是最先提出者,自然会引起争执。社会科学的伟大人物摩腾(Robert K. Merton,1910—2003年),曾经就提出科学发现的先后次序对学者的重要性,做过一次扣人心弦的演讲。他指出,为了争取被肯定为最先提出某个概念的地位,平常镇定而宽大的学者,都会变成粗鲁的斗士。他举出很多例子,如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6年)和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之间曾争执谁是第一位发现微分学中的差分内容。
到1980年代末,诸如此类的争执不再激烈或冗长,事实上,在20世纪或可能也包括19世纪的经济学界里,没有真正有趣的争执谁优先发现的重大事件。不过,确实常有人宣称他是遭受忽略的发现者,但并没有彻底的挑战,遑论有重大剽窃的指控。根据史蒂格勒的印象,在其它的科学领域,争论谁是最早的发现者之现象也同样退烧。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专业性期刊已是学者间沟通的唯一重要管道,而提出概念的日期比较容易判断了。
史蒂格勒认为,任何当代的概念或理论,要说是没有先驱者曾提出其中的一部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充满了聪明、富创造力、好奇的心灵,意欲解答大部分的实际问题和很多想像的问题。一个当代学者只是一群有能力、同心致力于特定领域或主题研究者之一,并且把一点点的新知识(包含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频繁地加入知识的共同池塘。这个既存的知识池塘就是下一个新发现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不隐含新发现必然会产生;每一个科学领域都曾经有过或停滞,或缓慢,而且进展平淡的时期。
学者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他们共同依赖于已经完成的研究之现象,早已有日趋强烈的趋势。就经济学来看,英国的研究重心在十九世纪后半移到大学里(英国是当时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和西欧的情形,在时间上也差不多。经济学家的数量,在马尔萨斯对人口成长做了可怕的预测后暴增。美国授予经济学博士的人数,在1900年只有将近十人,而1980年时,已达677人。
随着经济学家数目的增加,经济学术期刊也开始出现:1886年哈佛大学发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92年芝加哥大学发行《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90年英国王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发行《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到1980年代,英语系经济期刊的数量有150—200种。由于研究的交流急速增加,对一个主要大学的经济学家来说,不知道重要的发现,或完全了解许多的新发现,是很有困难的。
科学家数量的成长和交流方面的长足进步,使得人们怀疑,个别的学者恐怕很难做到英雄式的往前跃进的新发现。物理和化学诺贝尔奖早就愈来愈多次颁发给两个或三个得奖人,就是那些得奖人个别的贡献还不够深远之明证。而经济学这门较年轻的学科,自1969年开始颁发诺贝尔奖,就是两位学者同时获奖。1901到1920年间,物理和化学诺贝尔奖有31次颁给单一得奖人,3次颁给两位得奖者,只有一次是颁给3个得奖人(得奖人数的最高限)。从1961年到1980年,有18次颁给单一得奖人,12次颁给两个得奖人,11次颁给三个得奖人——平均而言,每次大约颁给两个得奖人。至于最晚成为诺贝尔奖学门的经济学奖,在1969到1978年十年间,五次颁给单一得奖者,也有五次颁给两位得奖者;在1978到1988年十年中,有九次颁给单一得奖者,只有一次颁给两位得奖者;在1989到1998十年间,有五次颁给单一得奖者,三次颁给两位得奖者;有两次颁给三位得奖者;在1999到2008年十年中,三次颁给单一得奖人,五次颁给两位得奖人,两次颁给三位得奖者;在2009到2018年十年中,有三次颁给单一得奖者,五次颁给两位得奖者,两次颁给三位得奖人;至于2019到2024年最近六年中,各有一次颁给单一得奖者和两位得奖者,其余四次都颁给三位得奖人。似乎单一位得奖者愈来愈少了。
史蒂格勒设想:人们可能会问每一位诺贝尔奖得奖人,如果没有其他未得奖者的研究成果,你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些成就?他想诚实的答案大部分是很快地回答“不可能!”史蒂格勒进一步指出,探讨科学里主要或甚至次要概念的源起,不可避免地会使科学研究的本质传奇化,它会成为英雄式进步的小故事,或是勇敢而成本高昂的努力。尽管如此,重要的个人进展以及大胆的冒险都只是科学工作的一小部分,就好比冰山一角的表皮。科学研究是一个市场过程,跟杂货店老板或电脑制造商的活动相较,只是形式大不相同而已,本质上鲜少差异。个别的学者,借着自利行为推销自己。如果总体经济学或电脑科学开始蓬勃发展,那刚毕业的学生进入这些领域的人数就会开始增加。
史蒂格勒指出,学者的酬劳通常不是依其研究件数来按件计酬,但实际上还是相关的,研究成果愈好,就愈能在较有威望的期刊发表。杰出的研究者会被较好的大学聘用、升等也较快速,也比较容易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私人基金会的补助,而且教学的负担也会较轻。在物理学界,还会较容易主持人手齐全的实验室。而学者的组织(如各式各样的学会)也会选举较杰出的学者,以及较具技巧的学界政客,作为领导干部。
谁能决定要研究什么主题,以及谁能判定每项研究成果的优良程度?短期间(一年以内)是由同侪科学家来判断。如果这个主题有点复杂,立法委员、官吏和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就很难了解这个正在进行的研究,也就更无法指导其研究方向了。科学的掌舵者乃是该领域中卓越的专业人才,他们拥有使自己不朽和自我选择研究方向的特质。
史蒂格勒认为,藉由自我选择精英来组成科学的管理体系,可能会产生类似18世纪牛津和剑桥大学那种显得愚蠢的停滞且墨守传统教条的结果,而这些弊病却没在美国出现。美国拥有很多好大学、很多基金会、很多科学期刊,使得每一科学领域都成为完全竞争的行业。没有一个正统的模型可以主导一门科学,但在联邦政府赞助研究扮演有力角色后,集中管理的趋势可能性已经升高。
竞争性环境较佳
边大卫(Joseph Ben-David)这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认为,美国的某些科学领域之所以能取得世界领导地位,主因是美国的科学界比法国或德国较不集中控制之故。竞争性的科学环境相较严密组织的科学体系,对新的概念较为开放。既存的体系反对完全创新的概念,并不只因为它们经常是错的这个好理由,还因为一旦新的概念是对的,目前掌控体系的领导者的知识,就会变得过时或毫无价值。
史蒂格勒认为,竞争的过程会产生实质的共识,当他在史丹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Behavioral Sciences)工作那年(1957—1958年),同僚经济学家有亚罗(Kenneth Arrow,1921—2017年,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弗利曼、瑞德(Melvin Reder,1919—2016年)和梭罗(Robert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群人的最大共通处是能力高超。有一次,中心主任泰勒(Ralph Tyler,1902—1994年)拿出一长串未来可能会聘入中心的名单,要他们从“绝对赞成”到“绝对不赞成”四个层次表达意见。由于他们几个人的看法极为接近,泰勒指责他们相互勾结,其实他们并没有。
史蒂格勒表示,从长远角度来看,科学的组成和问题并不能自我不朽,迟早掌握权力者一定会要求成果或更好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并不需要只是实用的(如治疗某种疾病或某种不景气),但他们得满足社会的一项重大要求,那就是研究成果必须值得其所花的费用。史蒂格勒觉得,即使在这方面,竞争的特质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比如以不同的科学领域间的竞争来解决重要的课题——物理和化学的结合就是显例,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科学界也以竞争来决定领导地位。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学界,数代以来都受控于非理论的传统(德国是历史的分析,法国则是社会学的分析),两个国家都臣服于较成功的英、美的经济学。
遭妒的美国经济学界
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学家在推销他们的成果上,成效卓著。每一家大企业至少雇用一位经济学家,政府这家最大的企业则设有经济顾问委员会,而在适当的时机下,该委员会得以进驻白宫。自从诺贝尔奖设立后,唯一增设的奖项是经济学奖。而经济学通常是大专院校里最受欢迎的科系:要么进法律学院,要么进商学院。所有那些关于经济学家之间意见差异的乏味幽默(五个经济学家会有六种意见,其中两种意见是凯因斯提出的),或是他们沉迷于抽象的思考(“实际上是可行的,但是理论上行不通”)。史蒂格勒认为,这些事实上都是嫉妒的嘲弄,而公然责难美国则是统合欧洲知识分子的唯一法宝,批评经济学是联合其它社会科学对抗美国的主要武器。毕竟嫉妒比起同情,是会多出几许甜言蜜语的。
1982年,史蒂格勒由于对资讯经济理论和公共管制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说自己在得奖前,并没有听到任何传闻,只是听到其他经济学家将会获奖的传闻,所以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让他有若奇迹式的惊讶。
史蒂格勒回忆,在斯德哥尔摩的庆祝会是很棒的盛会。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太太及四个孙子,他的老朋友比恩(Water Bean),以及弗瑞德兰(Claire Friedland)陪他一起参加颁奖典礼。他觉得人们一定会对瑞典王室致以最高的尊敬,特别是王室成员包括一位妩媚迷人的王后。
不过,史蒂格勒却对该种奖的目的和它为得奖人博得巨大尊崇的理由感到困惑,特别是他在阅读过札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1997年对诺贝尔奖有趣的研究——《科学精英》(Scientific Elites)——这一篇文章之后。诺贝尔(Alfred Nobel)当初是希望这些慷慨的奖金,可以提供给得奖者充分的经济独立,以便他们能奉献余生于研究上。可是,即使是1901年时的原始奖金(4万2千美元),也不能提供经济独立所需,而1980年代末的奖金(通常由两个或三个得奖者平分,且自1987年起还需缴税)最多只相当于一位杰出教授一年薪水的三或四倍。当然,得奖人也会因为获奖而有别项收入,在经济学界,演讲费和演奖的邀请会倍增,但这种收入必须去赚取才能获得。
诺贝尔奖的目的,并不是要引起该科学领域的同侪去注意得奖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毕竟平均而言,得奖者获奖的研究成果要发表大约十三年之后,才会得奖。在这十三年间,有能力的科学同侪就已知道得奖人的研究,并应用这些成果了,只有不够能力的人,才会认为得奖对研究目的具有新闻价值。
史蒂格勒认为,诺贝尔奖倒是对具有获奖资格的科学领域,提供了吸引人才的额外诱因。他说,如果亚当‧史密斯的信念是对的,亦即,人们会高估他们赢得任何彩券巨额奖金的概率,那么,诺贝尔奖就可能已稍微鼓励了有能力的年轻学者进入可获奖的领域里,且稍微压低了这些领域的平均收入。史蒂格勒认为,这种聪明才智的重分配,是否对社会有好处,还很难说,因为我们没理由相信,可获奖的领域会吸引到才能较差的人,而不能获奖的领域会吸引到才能较佳的人,盖一切仍依个人预期的边际产值而定。
诺贝尔奖的迷思
史蒂格勒认为,诺贝尔奖的主要效果,就是让得奖人在非科学家里获得崇高声望,而在这方面,该奖已显著成功。每年的颁奖典礼受到媒体的广大注意,这一定让每个促销人员嫉妒。对受过中等教育的公民来说,他们不可能了解得奖人的研究成果,也难以找到那些成果和当代幸福的关联性。即使是没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知道,获得这个荣誉标志的人是科学中的男爵。
不过,如此的荣誉提供了什么社会服务?而该声誉招惹了一些损害则颇明显:一大堆由得奖人署名的公开声明集结出版,而那些声明的内容根本不是得奖人熟悉的专业,且这种出版品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公众尊崇的声誉之好处何在呢?
史蒂格勒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遮掩式的抱怨。公众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理由,而发现这些好理由则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尽管很多人会觉得,去取笑公众的行为比发现行为背后的理由更有意思。史蒂格勒是这样推测的:公众想要崇拜在适当行业里的杰出表现,例如运动、军事以及科学层面等。如果有衡量科学表现的客观标准,例如次原子(质子和电子)的发现数量,公众就会以这个基础来选举冠军,而不会去依靠可能犯错的瑞典学院和其它学术机构。可是,这是他们目前拥有的最好准绳,因而他们把荣耀堆积在得奖者身上。
史蒂格勒问说:为什么公众要对各领域的杰出表现给予喝采?难道他们拥有一个崇拜基金,必需把它用掉?他的推测是:这种喝采是希望刺激各领域真正重要的成就。而重大的科学成就经常是高风险工作的成果。这种引出学术圈中的重大成就之诱因结构,总是依赖于声望和研究设备。即使是在前五十名优秀大学里的最高薪教授,他的薪水也很少是最低薪教授的三倍。既然瑞典学院愿意集中焦点于少数几个人的杰出成就之声望,自然有助于矫正大学和当前社会平等主义结构之弊病,从而得以提供诱因去进行高风险的研究。
这样看来,诺贝尔奖得奖人数未能与可获奖的科学领域数目维持相称的增速(得奖人数太多),并非重大缺失。而重大缺失之一是它排除了一些知识上的竞争激烈、且历史上曾大放光彩的科学领域之获奖资格。因此,至少到1980年代末,史蒂格勒指出,像拉帕勒斯(P.S. Laplace)那样伟大的人,都没资格得诺贝尔奖,因为天文力学尚非该奖涵盖的科学领域。史蒂格勒自忖:不知道许多其它的奖项(如数学界的Field奖)是否足以满足这种需求?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