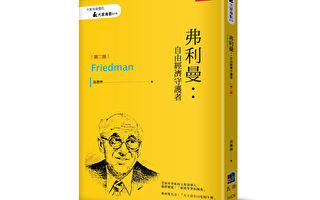【大纪元2025年01月21日讯】
一、东欧移民家庭
1911年1月17日,乔治·史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 1911~1991)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郊区小镇栾栋(Renton)出生,是家中独子,一直到二十岁大学毕业,都住在西雅图,之后才动身到美国东部念研究所。史蒂格勒的父亲乔瑟夫(Joseph)在二十世纪初就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移居到美国,在美国认识了伊莉莎白·杭格勒(Elizabeth Hungler),两人结了婚并生下了史蒂格勒。伊莉莎白在十多岁时就由匈牙利(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移居到美国,夫妻俩的家族都是务农的。
在禁止私自酿酒的法律出现之前,史蒂格勒的父亲乔瑟夫曾以酿酒维生,但禁止私酿酒法令出现后,就尝试做过多种工作。乔瑟夫是个强壮者,曾当过一段时间的码头装卸工。史蒂格勒回忆说,他的母亲会哭着送携带短棍的乔瑟夫去参加码头装卸工人工会的聚会。不久之后,乔瑟夫转进房地产市场,因为那时正值经济大恐慌,西雅图也遭到重创,造船厂被迫关闭,而波音飞机制造厂的规模仍小。乔瑟夫和伊莉莎白是以买下破落的房子,再重新整修并予以出售谋生。在史蒂格勒十六岁之前,已在西雅图十六个不同的地方住过,但他的家庭在迁移当中仍维持着舒适,而且乔瑟夫也吸收到房地产的丰富知识。
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移入者通常是从低工资的工作做起;他们可能年纪轻且不具有任何职业所需的技能﹐史蒂格勒的母亲就是如此,或者根本不会说英语,史蒂格勒的父母刚到美国时就是这样。不过,移民者是具有活力、身体健康者,而且富有冒险精神。以史蒂格勒的母亲伊莉莎白来说,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女孩子,只身到美国,又不懂当地语言,要自己养活自己,这是多么大的挑战?还好的是,伊莉莎白是落脚在一个只讲德语的社区。
研究发现,经过一、二十年后,从欧洲移到美国者,会比同年纪、同教育水准和相同资历的在地美国人,赚更多的钱,乔瑟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史蒂格勒本身也是种族熔炉的典型产物。他在三岁以前只会说德语,但在跟不同背景的小孩玩在一起之后,就拒绝再讲德语,直到上大学修习德文之前,对德文可说一窍不通,而其父亲到后来,在德语中夹杂的英文字词比重愈来愈大,相对地,讲英语时夹杂的德文字词比重愈来愈少。
史蒂格勒觉得他和其他移民者的子女有着一项差异,那就是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利用时间。直到十二岁进初中之前,他的父母亲都工作得很辛苦,而且都工作得很晚,根本无暇管他;即使上了初中,史蒂格勒也大都和自己所拼装的东西相处,例如他和朋友们会从湖底拖出一艘弃置的小舟,将舟底涂上焦油,之后就在湖面划着玩,而那个时候他们还都不会游泳呢!史蒂格勒曾参加第四十四队童子军,那是一个极富冒险心的童子军团队。该团获得许可,在当时隶属海军的一个狭小航空基地“沙点”(Sand Point)的一处森林区建造一座小木屋。
在1920年代中期,飞行是不拘形式的。史蒂格勒的童军团和那里的飞行员玩“胆小鬼”(chicken)的游戏。他们会从华盛顿湖上的木筏下来游泳,那些飞行员就驾驶飞机掠过木筏,逼吓他们跳下木筏,结果是飞行员赢了。当沙点基地扩张时,史蒂格勒他们的童子军营地就被收回,但他们很快找到新家。1928年,巨北铁路完成了北美最长的隧道,在泰镇(Tye)的旧隧道就被弃置,童军团要求巨北铁路把泰镇送给他们,对方竟然答应了。
泰镇曾经叫做威灵顿(Wellington),1910年发生一场雪崩,停在威灵顿的一辆火车掉到山谷下,造成96人死亡。巨北铁路后来就加建了挡雪板,但人们仍可在白天的山谷里看到该场意外事故留下的扭曲钢铁。在史蒂格勒的童军团拥有泰镇之前,该镇曾遭焚毁,但他们却是得到一个完好的火车站。相对于沙点,泰镇的交通并不便利,搭街上的电车就几乎可到沙点,但泰镇距西雅图五十英哩。不过,史蒂格勒和朋友们在数年间仍相当规律地利用泰镇,那时史蒂格勒担任的是童军团助理团长,是协助而非听命于团长。每到夏天,童军团都会攀爬奥林匹克山(Olympic Mountains),再进入凯斯凯山(Cascade Mountains)到东部。在那四、五天的远足结束时,史蒂格勒通常都疲倦而脚痛,且全身湿淋淋的,并对所吃的食物非常厌烦。因此,每次史蒂格勒都会发誓那是最后一次,但来年夏天一到,他们又会再上山。
由这些活动可知,史蒂格勒在暑假是不工作的,只偶尔打打小零工。当他十六岁左右时,曾到威纳奇山谷(Wenatchee Valley)从事梳弄苹果树的工作。苹果是整丛生长的,必须适当地予以稀疏,才可使每粒苹果顺利生长。史蒂格勒的工资是每小时四角、供膳宿。他工作了三个礼拜,是他一生中唯一用体力赚钱的经验。史蒂格勒的一生从来没游手好闲,在十多岁时,一半时日的暑假都在打网球,终其一生,史蒂格勒都是自己油漆房子,而且做一些手工制品。不过这些蓝领工作生涯是很短的。
史蒂格勒举他父亲为例,证明巴伐利亚人非常不同于典型的普鲁士人,非常地个人主义,而且完全不排斥冒险。1932年,美国的政治生态起了大变动,长期以来属于共和党重要据点之一的华盛顿州,就处在政治风暴中心。民选的州政府职位中,只有教育督察没有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格勒的父亲想要登记参选。但在史蒂格勒的劝阻下放弃了,而竞选连任的教育督察,是在那次州政府职位选举时,民主党大胜中唯一获胜的共和党员。
事后回想,史蒂格勒认为其劝阻父亲参选是对的。虽然其父是个聪明人,但对政治、官僚体系和教育行政却一窍不通。是有很多成功的商人进入政府担任全国性的行政职位,但大部分人在政治界都没成功。他们被消息灵通和自我保护的部属环绕和控制,必须和冷酷需索的立法议员周旋,而且他们所任职的单位必须改变的部分几乎都动不得,而教育行政人员通常还有伪装虔诚的需要。史蒂格勒庆幸他的父亲没去当官,否则他往后就得采取支持官员的立场,也就无法有往后的成就了。
多年之后,史蒂格勒的父亲参加了西雅图市民代表委员会的选举,约三十位候选人角逐数个席位。他的竞选费用仅2.75美元,用来印制一些宣布参选的卡片,由于他的德文名字,获得数千张选票,但落选了。
二、求学生涯点滴
在进入华盛顿大学之前,史蒂格勒对书籍是贪得无厌而不加以选择的,也是个没什么规划的学生。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成绩相当优异,大都是企业管理的课程,本来是想用来做事业生涯准备。但1931年大学毕业时,企管方面的工作不太好找,于是史蒂格勒接受了西北大学的免服务奖学金,一年之后就获得硕士学位。
当史蒂格勒离开西雅图到芝加哥西北大学就学时,并没有考虑到要发展学术生涯,当时的史蒂格勒对他的生涯没有什么概念。他的父母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的大学修习课程都是自己选择的,而且都没受到家庭文化的影响,不像他自己的儿子就不可避免地沉浸于他所受的教育中。就因为没有这种影响,史蒂格勒才读了许多愚蠢的书,也修习了太多类似房地产原理的“实用”课程,并且没有去修数学。
在西北大学那一年,史蒂格勒遇到一个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伍德贝瑞(Coleman Woodbury),是头一个激发他对学术生涯感兴趣的人。渐渐地,经济学使史蒂格勒觉得是他值得全力去研究的一门智识学问,而非作为企业经营的导读工具而已。当史蒂格勒从西北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回华盛顿大学念了一年,这时的史蒂格勒,其兴趣和目标的转移已很明显,于是他又收拾行囊往东部走,再也不回西雅图了。这次往东的目的地是芝加哥大学,而那时的史蒂格勒并不知道芝加哥大学是经济学界的主流。
史蒂格勒之所以会选择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完全是他在华盛顿大学的老师告诉他的,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和范纳(Jacob Viner, 1892~1970)都是优秀的经济学家。史蒂格勒也认为芝大将会比哥伦比亚大学或哈佛大学给予个别学生更多的关注,哥伦比亚大学只寄一本印刷的小册子给申请入学者,里边与申请者有关的段落打了勾,譬如“我们将在五月十五日以前,必须收到你的成绩单”以及“你必须在六月十五日以前寄来二十五美元”。史蒂格勒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十一年的教授,对于该校经济学系一贯的高品质深感尊崇和喜爱,但在1933年时,该单位却显示出人际关系淡泊且不太有人性化。哈佛大学是由经济学系系主任的秘书寄了一封回应申请人的入学申请,而芝大则是由经济学系系主任米立斯(Harry Millis, 1873~1948)亲自回信给申请人。史蒂格勒就由人际关注这个面向,选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就读博士班。
1933至1936年三年间,史蒂格勒在芝大就学,确实发现芝大经济学系提供了一种热烈的智识生活。影响史蒂格勒最深的老师是奈特,他时常不客气地批评学者和体制,对于所有权威都抱持怀疑态度,这也显示出奈特的智识精力。有时奈特会无法阅读他手中拿着的重要书本,因为书中写满了他的看法,即使是两行字之间的空白处也是一样,于是原书文字就难以辨识。那时的奈特已从经济学转入哲学和宗教的研究,在宗教上表现得有如学识渊博的不可知论者。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虚拟人物“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是个完全理性的人,能准确计算每项行动的成本和利益(或效益),并采行利益大于成本的行动。奈特曾经在芝大神学院的一次演讲说:“经济人和完美的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会有朋友。”
史蒂格勒将奈特比喻为摩西(Moses),奈特会在教室里批评该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新且荒谬的错误,而有经验的学生会带着不怀好意的神情,看着新来的学生想努力地记下极无秩序的笔记。史蒂格勒说他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上课中,奈特告诉他们,如果不懂得即将讨论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地租理论,那就可以别念经济学了。但在十五分钟过后,奈特却说他自己直到两年前才了解那个理论。有时候,奈特会出现在其他老师的课堂上,提出某些大家公认是没有意义的争论。
史蒂格勒认为奈特是一个值得敬爱、不屈不挠、不可思议的人。奈特对学生的重大影响力并非靠怪癖和魅力,而是他追求知识的专注。奈特表现出毫无保留地崇尚“真理”的态度,其崇尚的程度鲜有人能及。追求真理是危险或痛苦的,但又是必要的。没有一个权威会因为太威严而不能加以挑战,没有一个当代的学者会因为太有影响力而免于批判性的检视,而且通常会被公开抨击。权宜性的妥协根本不在奈特的思维之内,因此,若问他属于哪个政党,是很荒谬的问题,因为两大政党均未丝毫拥有他。不过,奈特支持朋友和门生时,却是毫无保留的。
奈特执意支持赛蒙斯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有两大著名经济学家在争吵,一位是奈特,他出身自伊利诺州贫家且子女众多的农家,性格颇为奇特。由于家境清寒,奈特经历奇异的教育过程后,到30岁才从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在爱荷华大学待了将近十年,才在1927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当时他已因一本探讨经济学理论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s, 1921),以及一些相当具煽动性的哲学论文(集结于《竞争的伦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1935)这本书中)而声名大噪。奈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高度独立思考的人,他怀疑很多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也怀疑对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所有公开讨论之完整性品质。
另一位当事人是道格拉斯(Paul Douglas, 1892~1976),他和奈特的出身类似,也是在贫穷环境中长大,而且还有个破碎的家庭。道格拉斯和奈特各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奈特是心思细腻的理论家,不断深入探讨经济分析和社会哲理;道格拉斯则是想像力丰富的实证工作者,而且是个积极而快乐的自由派改革者。在其自传《丰盛的年代》(In the Fullness of Time, 1972)中,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只是一笔带过,而在参议院的十八年是他人生的巅峰期。在他很不情愿地离开参议院后,史蒂格勒邀请他到芝大演讲。当人们告诉他气色很好、精神饱满时,他回答说他宁愿是个疲累的参议员。
奈特和道格拉斯这两个人性格南辕北辙,一个是胸怀开阔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是在知识上反对崇拜偶像主义者,只因同在一个小系里(只约十位教授),才勉强使两人凑在一起。奈特在1927年到芝大后的最初几年,与道格拉斯的接触只是断断续续,因为道格拉斯在1930年暂离芝大六个月,到史瓦斯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研究失业方面的问题,不久之后又参与多个公共委员会。不过,这两人的对立还是形成了,而最后主要的是以书信往返交锋。
在史蒂格勒1933年进入芝大就读之前,奈特和道格拉斯早就争论不休,两人关系冷淡,很少有同学同时修他们两人的课。1934年秋,由于赛蒙斯(Henry Simons, 1899~1946)面临拿不拿得到永久教职的事情,两个人杠上了。赛蒙斯是奈特的爱徒,随着奈特由爱荷华大学来到芝大任教。道格拉斯反对给赛蒙斯永久教职,甚至反对继续聘任,因为赛蒙斯只写了《自由放任的实是计划》(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这本好书,没有其他的作品,而且又是不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奈特极力袒护赛蒙斯,甚至以相当感情化的字眼为其辩护,他是这样说的:“说到感觉,我必须承认我的弱点。我不认为我能够以抽象的优点和弱点的冷静语气来谈论此事。我‘觉得’排斥赛蒙斯就等于在排斥我。如果他真的被排挤掉,我就会在道德和感情上对这个团体‘绝望’。但这绝不是冲着任何人而来,只是事情的本质确是如此。当然,这种感觉和我体认自己在这情境下乃属多余有关。在我擅长的领域中,我们不是站得很稳,而特别是我在其他方面又不是很有分量。此外,就‘品质’来说,如果这些人不属于这个团体,那我也不属于此。”
这个争议事件最后以所罗门王式的聪明,很有技巧地解决:留用赛蒙斯,但让另一位奈特的门生卷铺盖走路。
史蒂格勒在其1988年出版的自传中评论此事件,说:“奈特是我论文的指导教授,终其一生都对我很好。可是,读到这些信件,发现他以自己的饭碗和尊严力保赛蒙斯,心感悲痛。这是不能常用的险招,否则会使系上很难做决定。当然,教授们还是会强力‘促销’他们的指导学生,但正确的态度对成熟的学门是重要、甚至可说是关键的一环。”
史蒂格勒同意道格拉斯所指称的,赛蒙斯的资格在1935年时是不符合要求的。不过,赛蒙斯从那时起就开始写论文,在他后来仅活的十年中,发表了许多关于货币政策、公会,以及反托拉斯政策的重要文献,以及一本讨论个人所得税的必读书籍。这位英年早逝的赛蒙斯,之后在芝大法律学院开始教经济学时,又为法律教育开创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方向,也在法律学院先拿到永久教职,后来才获经济学系的永久教职。
这个事件显示奈特比道格拉斯对于赛蒙斯的前景看得更清楚,也显示奈特慧眼识英雄,并对其得意的门生之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道格拉斯在1939年当选芝加哥市议员,离开了学术界,不久之后进入海军陆战队任职,尔后又成为美国参议院参议员。
早年芝加哥大学的重要人物
奈特无疑是早年芝加哥大学的最主要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可证明其对知识的专注。奈特不当人家的顾问,不论是大小人物或企业,也不论是公开或私下。奈特也不到处演讲,他没在广受欢迎的传播媒体寻找立足点。奈特的行事风格显现出“追求学术知识,是值得第一流的心灵、全心全力投入的事业生涯”。即使是在奈特给予学生这种好印象的那个年代,该种行为在经济学界都不常见,而史蒂格勒认为,该种学者风范是伟大教师的主要修养。奈特的学者风范衍生出“不断地怀疑权威”,他只服从道理,绝不向权威低头,形成一种“反权威”的特殊形式:奈特跟学生相处完全没有一丝优越感。他在聆听任一学生的建言时,与聆听著名学者的建言都一样的认真。史蒂格勒感叹道:“他那么专心地注意听我们不够深入的观点,有时候真让我们备感尴尬!”
史蒂格勒在奈特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十九世纪末尾三分之一年代的经济理论的历史”博士论文。史蒂格勒感到很纳闷的是,奈特对学生那么好且帮助大,为什么找他指导的学生却是那么的少。就史蒂格勒记忆所及,他是奈特在芝大那些年指导过的三、四位学生之一。在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琼斯(Homer Jones, 1906~1986)、瓦利斯(Allen Wallis, 1912~1998)、罗宾斯(Lionel Robbins, 1898~1984),以及史蒂格勒合力下,在1935年奈特五十岁生日时,将奈特的极佳论文集结出版,那就是《竞争的伦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这一本书。
芝大第二位重要人物──范纳
奈特是当时芝大第一号人物,范纳(Jacob Viner)则是第二位重要人物。他是国际贸易专才的第一把交椅,对于经济史更有惊人的学问。有这样一则流传的故事:一位年轻学者急促地跑去找范纳,说:“我刚发现美国第一位数理学家!”范纳回说:“你是指伊雷(Charles Ellet, 1810~1862)?”这位学者惊道:“你怎么知道?”范纳说:“他是唯一没被发现的美国早期数理经济学家。”
这则故事显示出范纳的丰富经济史学识。范纳在课堂上是个相当严厉执行纪律的老师,他的身教和言教,形塑出芝大小心运用价格理论的传统。1934年时,范纳在他著名的经济理论课程“经济学301”刚开始教课时,询问一位同学:“哪些因素决定产品的需求弹性?”那位学生先回答说:“要视替代品多寡而定。”随后又补充说:“以及供给情况”。范纳脸色一沉说:“X先生,你可以不用上这门课了。”
史蒂格勒当时也修这门课,霎时和大部分同学的脊椎都感到刺痛。之后,史蒂格勒又修了范纳的国际贸易理论课,范纳强迫学生们要打分数。这是史蒂格勒在芝大修过的课中唯一有分数的课,通常选课的学生是拿”R”而不打分数。数年之后,史蒂格勒才体认到范纳伟大情操的一部分。范纳的武断远不如奈特或赛蒙斯,而且认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效果都在于那时或现在的知识不足,因而公共政策的唯一作用只是增进知识。范纳对智识历史的研究很广泛,比奈特还有过之。奈特闯出名号的文章是研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理论,该文列出七项李嘉图作品的缺失,而范纳分析李嘉图时则是融入感知与同情。因此,读范纳的文章可以“听到”李嘉图的声音。
上文提到的赛蒙斯是芝大的另一位名家,他是公众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公认的芝加哥学派核心理论大师。他致力于鼓吹“以私有(竞争的)市场来主导财货的生产和消费”,而“政府只扮演有限的经济性功能”。他在1934年出版的《自由放任的一项实是规划》让许多人着迷,因其文笔犀利而且有许多大胆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该书是在现代最萧条时期的谷底时写出的,传达了赛蒙斯的一项理念:西方社会正接近无法回头的关键时刻。
史蒂格勒自认对赛蒙斯的了解程度胜过对奈特和范纳,他还将赛蒙斯介绍给包尔小姐(Marjorie Powell),两人最终修成正果,结为夫妻。史蒂格勒也和内夫(John V. Neff)这位经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交往,但和经济计量学家休兹(Henry Schultz, 1893~1938)和道格拉斯这两位著名的教授则较少接触。
教授间争论不休
史蒂格勒在芝大求学的当时,教授之间激烈的争论,显示芝大经济学系没有主导性的思想学派。范纳和奈特两人一直在争论的是:生产财货和服务的成本到底是心理上的成本(像是令人厌烦的劳动),或者只是不将这些资源用于别处所损失的利益(如休闲的快乐)。
史蒂格勒说他无法理解,为何两个那么杰出的人会持续在字词上进行激烈争论。他俩利用学生传达争论的内容,使争论从一个教室蔓延到另一个教室。据说有位参加博士学科考“经济理论”的学生,在回答某个问题时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奈特教授请阅此;第二部分:范纳教授请阅此。”据说芝大没有鼓励这位学生继续念下去。赛蒙斯虽是奈特的爱徒,但两人也会为相左的见解争论得不可开交。
史蒂格勒的杰出同学们
在芝大求学时,史蒂格勒遇到多位杰出的同学,他形容说有如教授群那样重要的同学。第一位是瓦列斯(W. Allen Wallis, 1912~1998),他和史蒂格勒同一年来到芝大,两人从此开始了一辈子的友谊。他们挪用了一间空的研究室,搬来一些桌椅,并对每位老师的表现进行严格的检视。研究室张贴着一些标语,其中一张标语是这样写着:“数学里没有表达混淆概念的符号”。那是一句荒谬的句子。瓦列斯有着批判性、探索性心灵,很明显和史蒂格勒相同。瓦列斯在1962到1970年担任罗彻斯特大学(Univ. of Rochester)校长,也当过美国经济部次长。1958年时,瓦列斯协助史蒂格勒回到芝大当教授。
第二位是弗利曼,他早就在1932年到芝大求学,当时已经是一个可敬畏的智识人物。弗利曼不只可以非常严谨地、富有创意的思考,而且过程非常快速。多年之后,曾是弗利曼学生的凯塞尔(Reuben A. Kessel, 1923~1975)告诉史蒂格勒,有一段长时间每当他拿问题去请教弗利曼,总是搞不懂弗利曼的回答,因为弗利曼与他的讨论很快就跳到其他课题,弗利曼已快速地进入那个问题之分析,而且进到更多层次的探讨了。史蒂格勒提到可以显示弗利曼早熟的事件,当弗利曼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研究生时,曾因感冒卧病两天,但当他返校上课时,已经写好了一篇新论文。该篇论文指出,世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对于应用家庭收支资料估计需求弹性所建设的方法之错误所在,但庇古并未看到该篇登在《经济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论文,因而也未承认错误。由于此一事件,史蒂格勒也就时常揶揄弗利曼,说如果他在滑雪时跌断腿,一定会有新的作品出现。
第三位是包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他是从英国来到芝大的,拿的是大英国协研究员(Commonwealth Fellow)奖学金,既聪明又勇敢,敢于跟奈特争论资本的本质。
第四位是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2009,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当时选修经济学研究所的课程,他曾说是瓦列斯和史蒂格勒劝说他去修高等数学,使他成为数理经济学家。不过,史蒂格勒并不认为有这么回事。
芝大经济学系的学习活动
当时芝大经济学系的学生们和资浅教授,规划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而且邀请一群客座教授(包括蓝格(Oskar Lange, 1904~1965)、玛哈禄普(Fritz Machlup, 1902~1983)等人)演讲,带动了很棒的讨论。但当系主任问学生们是否想将研讨会列为一个课程时,却被拒绝了,因为他们担心教授们会对运作有意见。这也显示芝大年轻研究生的自信、傲慢、顽皮,而史蒂格勒是其中佼佼者。
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可证明。莱特(Chester Wright, 1879~1966)教美国经济史,上课时间是下午四点到六点,在五点休息时有十分钟喝所谓的“社会科学茶”时间。虽然这堂课的内容还不错,但莱特的上课方式不够吸引人,所以史蒂德勒往往只上半堂。有一天莱特宣布说,有人写了一张匿名便条,警告他不要超过六点才下课。课堂中所有的学生都转头看史蒂格勒,就是都认为是他写的。这让史蒂格勒很懊恼的想:“为何我没写那张便条!”莱特老师其实是很温和的,在史蒂格勒后来考经济史的学科考试时,还特地出了一题有关美国太平洋岸西北部的经济发展问题,那是史蒂格勒的家乡,应对史蒂格勒有利,可惜的是史蒂格勒不会这一题。
史蒂格勒认为,一个人在学校或大学所获得的知识,至少有一半是跟同学学习的,毕竟同学们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无所顾忌的交流、论辩,而师生之间就不可能如此。不过,学校若能聘请到众多好的教授,是能够吸引好学生就读的,芝加哥大学就是个好例子。
芝大对史蒂格勒的影响非常大,他学到重要的一课是:对于公认的信仰和权威的声望予以质疑。他确信:广为人接受的概念,很少有支持其正当性的证据。不过,史蒂格勒认为,芝大未能让学生往应用统计资料估计经济关系,以及检定经济理论,是一大遗憾。因为这一门成为往后的一股热潮。其实,当时芝大有两位老师在鼓吹这种潮流,一位是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另一位是休兹(Henry Schultz)。
道格拉斯是劳动市场统计研究的先驱者,更重要的是,开启了生产理论的统计研究,亦即研究生产商品或服务的过程或数量时,劳动和资本使用量之间的关系。
休兹开了一门数理经济学的课,课名是“相关和曲线配置”(Correlation and Curve Fitting),是个很爱引经据典的学者。休兹虽无太多自己的深入创见,却有刻苦耐劳、穷追本源的特质,精研的是个很狭隘领域,那是统计上的需求曲线,多年来都在撰写其毕生巨著《需求的理论和测量》(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他聘请当时就读研究所一年级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助理,帮助他从事此工作。弗利曼虽然认为休兹的学术才智有限,对纯粹分析不专长,但不偏不倚追求真理,坚持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深耕的态度,使休兹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远胜于其他更能干,但治学较不严谨较不心胸宽阔的学者。不幸的是,休兹在他的专书出版前,开车载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赴加州度假,车子在公路上坠崖,全家丧生,年仅四十五岁。
史蒂格勒日后觉得当年忽略现今称作“计量经济学”的内容,是自己造成的错误。他从未修道格拉斯的课,因为道格拉斯和史蒂格勒的指导教授奈特不和。而史蒂格勒对休兹的教学方式则不感兴趣,因而错过修习计量经济学。不过,日后史蒂格勒却以“实证研究”得到尊崇,这是管制经济学中检视政府的管制政策主要成分,需要应用计量技巧,而且只要中等程度的技巧就够了。如果当初史蒂格勒能上休兹的课,就不需要大费周章向弗利曼、瓦列斯、伯恩斯(Arthur F. Burns, 1904~1987)、费布利肯(Solomon Fabricant, 1906~1989)和摩尔(Geoffrey H. Moore, 1914~2000)等同窗好友以及老板学习了。
在芝大求学时,史蒂格勒对历史深感兴趣,由他的博士论文是探讨经济理论的历史,就可得到印证。其实,终其一生,史蒂格勒对历史都抱持着浓烈的兴趣,即便经济史在学术界早就不受重视,甚至已被边缘化了。不过,史蒂格勒对自己选走经济史这条路,还是耿耿于怀,自觉当初没预测到四十年后的经济研究之方向,也就是数理化和计量经济的走红,他对自己当年求学时没选读计量经济,以致在数学和统计技巧方面没能得到很好的训练深感遗憾,尤其因为对数理化不够专精而错过1946年被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此,更让他至死都无法释怀。
史蒂格勒对大学学费的明显改变有深刻感受。当他在1933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每年的学费是三百美元,相当于1988年的两千八百美元,非常便宜,而两个时代的生活水准差异也很大。他举实例说,1930年代的学生都没汽车,而十年后,弗利曼曾因为主动提议要载几个学生去西北大学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遭到拒绝,而吃了一惊。那些学生每个人都说要自行开车去。史蒂格勒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奖学金也很少,而他是在研究所里打零工赚取学费的。不过,他觉得不同时代的本质并没改变,也就是说,研究生就好像生活在一个紧密结合的小型社会,整天都沉浸在经济学中,基本上是一个竞争的智识中心。
1936年,史蒂格勒接获埃姆斯(Ames)的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 State College,之后升格为大学)助理教授聘书。也就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和美可小姐结婚,他们是在芝加哥的国际学舍(International House)认识的,而大家都昵称美可为“小宝宝”(Chick)。美可生长于宾州的印地安纳市,其父是当地律师。她从郝约克山学院(Mt. Holyoke College)毕业后,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之后才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在他们结婚的前一晚,美可的父亲将她叫到一旁,警告她说,匈牙利人有打老婆的习惯。其实,这位岳父大人是多虑了,因为史蒂格勒只有四分之一的匈牙利人的血统。
史蒂格勒夫妇共生养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史蒂芬(Stephen)是统计学家,次子大卫(David)是康乃迪克州的律师,小儿子乔瑟夫(Joseph)是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企业家。史蒂格勒的夫人小宝宝于1970年8月,在加拿大马斯科卡湖(Muskoka Lakes)边的农舍过世,那是史蒂格勒一家人过暑假生活的地方。直至1991年史蒂格勒去世,他从未再婚。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