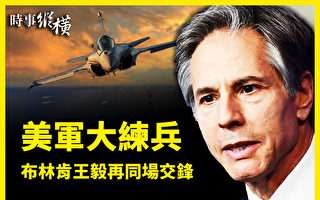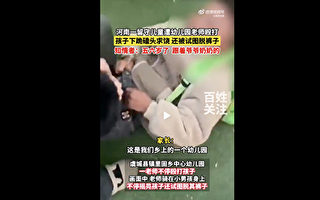【大纪元2024年07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蔡溶纽约报导)在纽约移民社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正在发生:卫星宝宝问题。这些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像卫星一样被发射”送往中国,几年后再被回收重返美国,通常在宝宝美国护照5年有效期到期前。在国内则被称为“留守儿童”,在缺乏父母陪伴的情况下成长。
近期,在布碌崙八大道发生的连串华裔青少年聚众霸凌事件,凸显了这一问题。许多“卫星宝宝”回到美国后,面临一系列情感困惑,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加入帮派或参与暴力行为。这不仅是对社会的挑战,也是对家庭的挑战。

虽然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一现象涉及的人群有多少,但福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偷渡高峰、201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后的偷渡减少,再到疫情后的偷渡再次兴盛,都影响了这一现象。当地人表示,现在纽约的福建社区几乎每家都有过“卫星宝宝”。
1990年代以后偷渡出国的年轻人,大多年纪很小,他们在国外站稳脚跟并偿还偷渡债务后,逐渐成家生育。但忙碌的生活、育儿知识的缺乏,加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他们的孩子——大部分是“卫星宝宝”——面临着更多成长上的挑战。
这些在90年代偷渡高峰期出生的“卫星宝宝”,如今已是三十多岁的成人,他们往往继续父母的轨迹。而现在的青少年很多就是那一批“卫星宝宝”的孩子,他们也面临着很多成长上的挑战。
黄妮可,一位曾经的留守儿童,现在是亲子互助会的会长,她深刻地理解这些孩子的感受,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黄妮可指出,“卫星宝宝”现象的延续带来了不少家庭和社会问题。

01:留守孩,在父母缺失下成长
黄妮可一出生就被送由她的亲戚负责照顾。福建很多地方重男轻女,黄妮可现在仍记得:家中对男孩的关注度比女孩多更多。
黄妮可的父母远在外地务工,无暇照料她。于是黄妮可一直待在寄养家庭,基本每年跟爸妈就见一次面,直到她10岁以后才回到父母身边,19岁的时候全家移民到美国。
回忆起这段留守儿童的经历,黄妮可说:“当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父母,但彼此没有任何的情感连接。”
黄妮可高中没读完来到美国,到美国后虽然有机会继续升学就读高中,但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她只能出外工作。抵达纽约仅一周,她便前往外州的餐馆打工。
“一到美国的第二步就去找工作,我们就知道怡东楼在哪里,这里有专属福州人的职业介绍所,当时大家都很自然地走这个套路。”黄妮可说,全家五口原本在八大道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寓,但抵美不足一个月,就把其中一间房分租出去,因为家里大部分人都分散到外州打工了。
这时的黄妮可不会说英语,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去一个陌生城市的中餐馆见雇主。一个陌生人来接她,把她带到宿舍。每天下班后,她独自待在房间里,面对一群陌生的人,两眼发呆,不知道该干什么。
隔年,年仅20岁的黄妮可就被催促着嫁人。福州移民大多很早结婚,且订婚时男方需要送女方家聘礼。2007年的礼金是3万8千元。黄妮可淡淡的说:“现在要十几万了吧,水涨船高。当时也没有什么基础就⋯⋯反正找个人结婚,感觉就是按照所有人的步骤一样的走。”
怀孕后,先生和她在不同州的餐馆打工,夫妻俩半年才见一次面,这其实也是很多华人社区婚姻的常态。整个怀孕期间的检查都靠自己,生孩子也自己去医院,生下的孩子也是自己学着带。那时她22岁左右,面对天天哭闹和生病的儿子,吃不好睡不好,寒冬时打开冰箱却什么食物都没有,感到非常崩溃。身边的人都劝说她赶快把孩子送回去,因此在儿子五个月大的时候,她也按照身边亲友的方式,把孩子送回中国福建长乐让爷爷奶奶抚养。
由于夫妻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尽管他们在结婚3年内就有了一儿一女,婚姻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随着家暴的反复发生,黄妮可最终决定离婚。
02:离婚后,单亲妈妈带两孩
决定离婚时,两个孩子分别只有两岁和三岁,孩子的养育和归属影响着4个人的人生。她选择带着孩子离开,尽管作为单亲妈妈抚养两个幼童很困难,但她坚信孩子的陪伴是她活下去的意义。
面对家人的反对,她依然坚定。她表示,她不会因为可能的第二次婚姻而放弃孩子,因为她不想对孩子的未来或她的决定感到后悔。她问道:“你能保证不要这个孩子,我的第二段婚姻就能幸福吗?你拿什么来保证?当孩子成长中遇到问题,你能承担得起内心的自责、不会有一点后悔?哪怕第二段婚姻幸福,但是你的第一个孩子过得很惨,那时你又能做什么?你的幸福和孩子的痛苦经历,你要怎么平衡?如果你能过得了心里的那道坎,那你或许可以丢下孩子。”
“我的人生可以说已经是这样了,但我可以改变孩子的未来。”她说,因为自己从小留守过,所以再辛苦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留守。就因为这一念,黄妮可把孩子接回美国,带着他们住在出租屋里。
孩子到美国后,生活费用增加。黄妮可询问了多家机构,发现并没有专门为单亲妈妈提供的福利。但只要收入低,就可以申请福利。一位马来西亚移民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帮助她申请了福利。她很快得到了粮食券和托儿补助,孩子也能上托儿所了。
白天她可以做一些临时工,虽然一天就赚50块钱,但足以支付房租。粮食券帮助她解决了日常饮食问题,孩子的衣服也有人赠送。工作后,她还能通过退税积攒一些钱。黄妮可表示,美国政府的帮助让他们渡过了难关,“政府真的帮了很大的忙,这些福利支撑着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03:改变思维,单亲妈走出一条路
但是慢慢的,黄妮可感到力不从心。她说,小孩子有各种行为问题,在学校,儿子因行为问题面临被送进特殊教育班的压力,而她对特殊教育的误解让她对此极力抗拒,“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是我的孩子没傻,为什么要去IEP?”她说,直到儿童福利管理局(ACS)介入并提供支持后,情况才开始好转。
她表示,当时学校怀疑她涉嫌儿童虐待或忽视儿童,因此报告了ACS。面对ACS差点将孩子带走的情况,她坦诚地反映了家庭状况和孩子的经历。
她说:“我有完整的医疗记录和治疗师的记录,证明我没有虐待孩子。哪位母亲能够持续几年不断地带孩子去曼哈顿的各大医院进行检查,去看行为科医生和寻找治疗师呢?”黄妮可表示,在ACS的调查结束后,他们认为她已尽最大努力,于是在资源上给予了她各种帮助。
后来,她了解到个别化教育计划IEP(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是为了帮助孩子,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辅导他,因此她表示同意。由于老师了解特殊教育孩子的需求,孩子在学习上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在医生的介绍下,她还参加了亲子课程,在那里她是最年轻的母亲。“在上课前,我觉得好像天都快塌了,但听完其他人的分享,就觉得我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事情。大部分人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比如青春期问题、自杀、吸毒、不出门等。”她说,通过亲子课程,她学到了更多教育孩子的方法。恰逢孩子的评估结果出炉,显示他需要更多情绪和行为管理的帮助。

回想起来,她对这段经历感慨万分。她说:“我们父母那一代人通常采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孩子,不知道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沟通。后来我才明白,沟通有其技巧。比如以前接到老师电话,整个人就炸了,认为孩子又闯祸了,回家便责怪孩子。孩子会感到被指责,变得沮丧,不愿意与我交流。实际上,在学校抱怨之前,他可能已经经历了另一段故事。我们总是忽视他的感受,只看到事情的结果,而不去了解背后的原因。”
“后来我了解到,沟通是一个技巧,比如可以这样告诉孩子:‘我今天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老师告诉我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描述事件时不带有情绪,而不是直接责怪孩子。前者是求证,后者是定性。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她补充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当我的孩子行为问题严重时,我曾感到非常绝望,全身无力,严重到下不了床,每天就一直掉眼泪,甚至有轻生的想法,而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你的痛苦点是什么。那时,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在带孩子看治疗师的同时,我自己也在接受治疗和服药。”
她坦言自己在情感方面的缺失,那时她常感到崩溃和自责,对孩子的行为的原因感到困惑和无助,无法给孩子足够的情感支持。这是她在咨询治疗师后才意识到的。
“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亲子课程不能更早一些提供给妈妈们?怀孕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上课。”因此,她创办了非营利机构“纽约亲子互助会”,慢慢地起步。

这样的改变不仅帮助了她的孩子,也让她自己在情感方面有所成长。她说:“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你不要带着观念去给人定性,而是去了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用爱的方式、善的方式去沟通,这条路才能够走通。否则,你自己都撑不住,别说孩子了。”
04:案例警示的心理健康问题
在2016年3月,一起悲剧发生在八大道的福建社区,一名两岁女童在家中浴缸溺水身亡。其母亲被控以惩罚孩子尿湿裤子为由,将孩子的头按压在水下进行惩罚性训导,最终被裁定过失杀人罪,判处18年监禁。案情显示,该母亲幼年曾被领养,童年生活也非常不幸。
2017年1月,俄亥俄州一对来自长乐的夫妇报警称其5岁女儿失踪,警方在他们餐馆的冷冻室内发现了女孩的遗体。经调查,女孩头部遭受重击,身上有多处伤痕,其父母随后被逮捕。母亲供述,由于餐馆的工作太繁重,她只有两只手,分身乏术,就将孩子摔到地上,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在于,两位闽籍行凶者的犯案动机都与精神状态有关,这凸显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生活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黄妮可说,这些案例反映了华裔移民在压力下,可能采取错误和极端的育儿方式,“其实她们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她说,“卫星宝宝”还没到青少年时,你还看不出来社会问题这么大。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许多家长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社区,许多家庭仍在为生计打拼,无法顾及太多,加之家长本身教育程度就比较低,在孩子的美国教育上无能为力。他们每天工作劳累,没有时间和孩子沟通交流。“卫星宝宝”回来后,父母也不管他,又把他丢给其他亲属寄养,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
“在这不断送来送去的过程中,孩子很容易学坏,甚至加入帮派。因为他们在家庭中得不到关爱,便在外面寻求认同感,去干那些打架斗殴的事情。在这个团体中,他觉得自己很威风,走在街上,觉得大家都怕他,其实他只是想得到一些所谓的价值感。他走了错误的方法,有时候就很难回头了。”黄妮可说。
她说在福建家庭中,一种情况是父母双方都不带孩子,把孩子直接送回中国,等孩子5岁再接回美国,放到其他亲戚家寄养。另一种是丈夫在外州打工,妻子自己带孩子。再有一种是父母离婚,孩子被送回中国后就没有机会再回来,因为他们的护照过期了,需要父母双方签字办理新护照,但父母双方都找不到,由爷爷奶奶带着。“这种只能等到成年后再自行去领事馆办理身份。因为他们未成年,即使护照没过期,找不到父母也无法出境。这样的孩子往往对父母抱有深深的怨恨。”黄妮可说,这类孩子其实不少,但缺乏官方的具体数据统计。
黄妮可曾遇到一位14岁的女孩,她在12岁时来到美国。女孩的母亲向黄妮可求助,因为女孩不愿上学,整天在家抽烟。母亲在外州工作,很少回家,将女孩留在舅舅家中,但舅舅管不了她,并催促母亲回来。而母亲作为单亲母亲,认为她需要工作来维持生计,但同时也在逃避女儿的问题。
黄妮可说,女孩不愿上课,因为语言障碍,听不懂课程内容,也可能在学校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人真正关心她,舅舅虽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无法与她深入交流。“她抽烟其实是因为内心痛苦。国内外环境差异巨大,她从国内的宽敞住宅搬到八大道拥挤的居住条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突然被带到陌生且艰苦的环境,自然产生怨恨,认为母亲多年不管她,现在把她带到美国还是不管她。”
她说,在合租的房子里,女孩半夜在客厅打游戏,大喊大叫,不能顾及他人的感受,也不考虑同租者从餐馆工作回来需要休息,“她放任自由惯了,突然被置于合租的生活规范中,她也受不了。”
此外,黄妮可说,青少年之间的冲突经常被学校忽视,而这些问题往往源于家庭。她曾询问那些参与打斗的青少年为何会这样做,他们表示这是为了出一口气,因为家里没人教他怎么做。
这些孩子中,有些已辍学,成为街头的问题少年。由于父母不管、祖父母无力管、学校管不着,“三不管就变成野孩子,只能靠社会的鞭打了”,黄妮可叹气说。
“现在社区的毒品问题很严重,青少年吸毒问题也越来越多”,她感叹说,社区总是有很多无奈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么多,咨询这么多,现在的问题是毒品和赌博,接下来会更乱。”
05:寻找解决之道

黄妮可说,2021年纽约市扩展“全民3岁幼儿班”(3-K for All)项目,为三岁儿童提供免费、全天、高品质的儿童早期教育,对福建社区的帮助甚大。
她提到,自从3-K计划推广后,将孩子送回国寄养的情况有了显着减少。过去,孩子们到四岁才读书,但现在三岁就能够接受免费教育,减少了早期育儿的经济负担。“因为早期育儿的开销非常大,3K推广后,3岁就可以把孩子接回来,越早接回来越好,避免寄养造成的心理问题。”
她说,疫情期间,很多人回不去,孩子也出不来。疫情前送走的“卫星宝宝”现在准备回来了。她建议这些父母与孩子坦诚地谈论,提前做一些心理建设,以帮助他们在情感上应对即将到来的重大生活变化,“告诉他们将经历什么过程。全部让他知道,就不会感到意外。”
黄妮可强调,在孩子12岁之前,家长应多花时间陪伴,创造亲子时光,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和有价值。父母应带孩子认识世界的美好,“有能力的就带他们到处走走看看,就是不要局限在一个空间里。有些妈妈自己带孩子却不出门,她说自己社恐,但又希望孩子是社牛,这不可能的事情嘛。然后她一边自责,一边责怪孩子。其实是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社区可以做的,就是举办各种活动,让家长融入社区和社会,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生活中的挑战。有些父母没有学习的欲望,这一点就很糟糕。比如说她的孩子去上学了,她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学英文,跳出这个井去看外面的世界。接触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知识,开阔眼界。”她说,父母的观念也得改,然而她也理解“很多人早年偷渡过来,他本身的童年经历和创伤,也是一大问题。”
黄妮可分享了她参加不同社区活动和座谈会的经历,听别人谈论自己的家族和成长经历的感受。她说:“我很惊讶,原来黑人也痛恨毒品,这打破了很多华人的偏见,以为黑人都是贩毒和作奸犯科的。但其实,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也痛哭流涕,他们也在努力改变。”
她表示,每个族裔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无奈,华人也一样。华人常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愿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现在青春期的问题非常多,精神疾病也非常非常普遍,很多事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有苗头,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她认为,家长应理解孩子的感受,不要一味苛责,“大原则没有错的情况下,小事要放开,不要什么都碎碎念。一旦度过了青春期,孩子自然会明白,比如饭少吃一点,少吃不会怎么样。体重身高没问题,你焦虑啥?说白了就是观念问题,看你怎么想。”她建议家长应该多反思自己的观念,并通过心理科普来提升自己的育儿技巧。
最后,黄妮可建议新移民和走线客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避免毒品,调节心理落差,接受现实,设立合理目标,感恩生活,保持精神健康。她说:“健康和活着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逐步改善生活,避免过高期望,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责任编辑:陈玟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