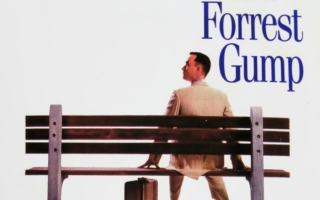自从开始透过做菜,讲述每道菜背后,属于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才发现味蕾与情感交织成一张充满酸、甜、苦、涩滋味的记忆网络,随着时间的流转,就像食物经过酿造、储藏展现的醍醐味,百感交集,令人在舌间心上低回不已。
我从小生长于东石一个不靠海的农村,每年雨季都因村后的朴子溪海水倒灌,淹没村里的几个窟仔(池塘)而成水乡泽国,和水里的鱼虾一样在深及膝腿的陆上潦行,成为最深刻有趣的记忆。
不淹水的时候,窟仔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游泳池,也是村里妇人的洗衣场所,更是阿公穿着一件四角内裤“摸蜊仔兼洗裤”的地方,鸭、鹅戏水,绿波荡漾。
池塘定期会涸窟,水抽掉一半时大人会先下去牵网围捕南洋代仔鱼,池水见底后,就到了各凭本事捉鳝鱼、胡溜(泥鳅)的时阵。雨天抾露螺,淹稻田时钓青蛙,去芦笋田灌肚扒仔(土黄色蟋蟀),冬天坐在大灶前炥番薯,年夜饭后厅堂里充斥着一股用围炉炭火烤鱿鱼的香气,伴随着家族所有叔、伯、姑姑们搦十八啦(掷骰子)的欢笑声,食物连结着情感,气味特别深刻浓烈。
国小四年级我们姊弟三人被带到高雄跟父母同住,从一个乡下野丫头逐渐转变为市场儿女,跟着父母在市场讨生活,和食物的关系更直接而密切。母亲因为忙于做生意,我也开始学习掌厨与分担家务。
夏天剖西瓜卖椰子水、甘蔗汁。端午卖菖蒲。中秋卖花生糖(因为习俗说要食土豆才会食佮老老老)。年节卖糖果饼干。能赚钱的母亲都会卖,只因嫁给一个赌鬼丈夫,让母亲操劳一世。
但我那赌鬼父亲除了不负责任外,真的很疼爱我们,冬令进补他会盛好一碗一碗乌漆抹黑的补汤,重金悬赏我们勉强吞下。
“冬至补会着,较赢九斗换一石。”
所以我用“八珍乌骨鸡汤”来形容他那“没有十全的爱”。
他喜欢吃满腹鱼卵的本地鲫仔,只用盐与姜丝咸凊,乌鱼季节他会买乌鱼壳(挖取鱼膘与鱼卵后的鱼身)和青蒜回家让我煮乌鱼米粉,或买些来自故乡东石的鲜蚵,教我煮姜丝咸菜汤一解乡愁。
为了追求从小立定的理想志向,高工毕业看见报纸求职栏里征求歌仔戏学员的广告,便不顾一切离家出走进戏班学戏,因为早就知道父母根本不可能同意,那是国中毕业闹过家庭革命失败的结果。
才跟着戏班流浪没多久,黄历七月半在台中就遇到韦恩台风,全班演员挤睡在水泥戏台后方的储藏室里,看着布景一块块飞走。
因为台风对电力、农渔养殖业带来重创,戏班无电可演戏酬神,大家终日无所事事,我在野外采集到一把乌甜仔菜(龙葵),配些虾米、香菇与五花肉丝,循着记忆中阿嬷的味道,煮出一锅乌甜仔糜让大家饱食一餐,赢得所有人的赞赏。
因为野台戏面临社会变迁的残酷考验,随着电子花车在庙口崛起,让录音班的少女歌剧团拼台跳起相思艳舞,戏子梦碎的我拾起小说创作的笔,记录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十万字长篇小说《失声画眉》获得自立报系百万小说奖,本该在文坛大放光彩的我,却悄无声息的走入婚姻家庭,于真实的人生唱起一出“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没有人知道我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什么?直到相隔十七年再以《竹鸡与阿秋》获得高雄打狗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才又开始在文坛露脸。
岁月嬗递,绝不是悄无声息,至少透过许多料理与食物,连结生命中的许多片段,或艰辛劳苦,或温暖关怀,或刻骨铭心,从读书时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艺少女,到饱尝人间冷暖的初老阿嬷,借着替媳妇做月子餐的饮食笔记,一路延伸至结合人生经历的饮食文学,蓦然回首,料理的滋味就是人生的滋味,酸甜苦涩尽在心头。◇
——节录自《舌尖上的人生厨房》(作者序)/ 联经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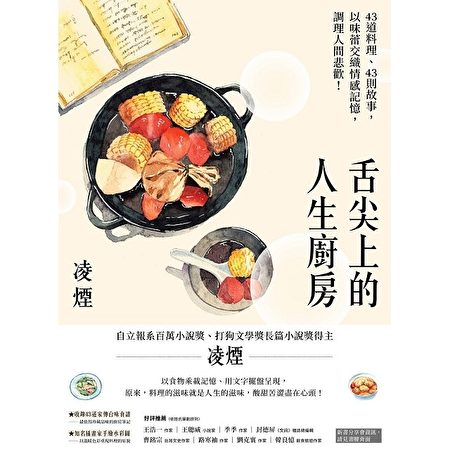
(〈文苑〉登稿)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