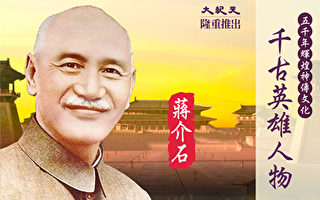树,记得自己的童年(3):共生

短命的香菇在地表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底下支撑它的网路在一个更阴暗、更富饶的世界存活很多年。(fotolia)
植物的敌人多到数不清。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把绿叶视为食物。当树木还是种子跟幼苗的时候,它可以整个被吃掉。植物无法逃离进攻不休的敌人大军和他们不间断的威胁。林地烂泥里住着伺机而动的生物,植物不论死活都是它们的养分。真菌大概是最厉害的角色。白腐菌跟黑腐菌随处可见,两者的化学物质都能做到其他东西做不到的事:腐蚀最坚硬的树心,所以才会叫做“腐”菌。除了少数植物化石之外,四亿年来树木的结局一直都是分解成最初的状态。这样的彻底破坏归因于一种真菌,它的生存方式令人毛骨悚然:腐蚀森林里的树枝与残干。但是这种真菌里也有树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
你或许以为香菇就是真菌。这就好像把阴茎跟男人划上等号一样。每一朵伞菌,无论是美味的或带有剧毒,都只不过是性器官;它连接着一个更完整、复杂和隐密的系统。每一朵香菇底下都有一张绵延数公里的菌丝网路,缠绕着无数土壤并维持地貌的完整。短命的香菇在地表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底下支撑它的网路在一个更阴暗、更富饶的世界存活很多年。只有非常少数的真菌(五千种)策略性地与植物建立起更深刻持久的和平关系。它们的菌丝网包覆和穿透树根,与树木共同分担把水抽进树干里的责任。
它们也会开采土壤里的稀有金属,例如锰、铜跟磷,然后把这些金属当成东方三博士的珍贵礼物。
森林边缘是恶劣的无人之境,树木不越过边界生长其来有自。跨出森林短短几公分的地方,对一棵树来说水太少、阳光太少、风太强或是太寒冷。不过,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森林会扩张并增加面积。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一株幼苗征服这个严苛的环境,熬过不得不面对的匮乏岁月。这样的幼苗总是带着共生的地底真菌并肩作战。这棵小树面临重重险阻,但是在真菌的协助下,它的根部功能也是一般小树的两倍。
它付出的代价是:最初几年幼苗的叶子制造的糖分大多直接送到在根部吸取养分的真菌。但是菌丝网只是围绕着奋力挣扎的树根,并不会穿透它们。这株植物与真菌的生理结构保持分离,仅靠双方的努力把彼此连在一起。它们紧紧相系。这场合作会持续到这棵树长得够高,可以在林冠争取阳光为止。
树和真菌为什么生活在一起?我们不知道。真菌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它放弃了更轻松也更独立的生活,选择跟树紧密结合。它让自己习惯吸收直接来自树根的纯糖,如此奇特又紧密的组合在森林里的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或许共生能让真菌感觉到,它并不孤单。
我的研究常被归类为“好奇导向研究”(curiosity-driven research)。也就是说,我的研究成果不会是有销路的产品、有用的机器、能上市的药丸、强大的武器,或是带来任何直接的有形利益。就算对上列的任何一样东西有间接助益,那也是很后来的事了,而且发现的人也不会是我。所以对国家预算来说,我的研究比较不那么重要。这种类型的研究只有一个重要的补助来源:国家科学基金会。
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美国政府机构,它提供的科学研究经费来自税金。国家科学基金会二○一三年的预算是七十三亿美元。联邦政府为农业部(负责监督食物进出口的人)编列的预算大概是这个数字的三倍。美国政府每年为太空计划编列的预算是其他科学项目加总的两倍:美国太空总署二○一三年的预算超过一百七十亿美元。但这种差别待遇远远比不上研究和军事花费之间的不平等。国土安全部是因应二○○一年911事件而成立的单位,年度预算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五倍之多,而国防部的“弹性”预算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六十倍以上。
好奇导向研究的其中一个副作用是启发年轻人。研究者总是过度热爱自己的天职,最令他们快乐的事莫过于让别人也爱上这份天职。就像每一种以爱为动力的生物,培育下一代是我们无法遏抑的渴望。你或许听说过现在美国的科学家不够多,因此有“落后”(无论意义为何)的危险。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位学术型科学家,他都会哈哈大笑。过去三十年来,美国政府为非国防相关的研究编列的预算没有增加。单纯从预算的角度来说,科学家不是太少而是过剩,而且每年都有更多科学家从学校毕业。美国或许可以宣称自己重视科学,但是政府确实不愿意为科学花钱,尤其是环境科学。
虽然七十三亿美元听起来是一大笔钱,但别忘了这笔钱要分给所有的好奇导向研究。不只是生物学,还有地质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更加深奥难懂的工程与电脑科学。因为我研究的是植物为什么能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所以被国家科学基金会归类为古生物学。二○一三年他们为古生物学提供的研究经费是六百万美元,这是全美国古生物学研究一整年的预算,而且挖掘恐龙化石一定会分到最多经费已是意料中之事。
尽管如此,六百万美元听起来依然不是小数目。或许我们可以假设每一州都应该有一位古生物学家得到补助,六百万美元除以五十,每一份合约的金额是十二万。这相当接近实际情况: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古生物学项目每年提供三十到四十份合约,平均每份合约价值十六万五千美元。因此无论何时,美国受到补助的古生物学家大约有一百人。就算古生物学家全体投入受欢迎的绝种生物研究,例如恐龙跟长毛象,这样的经费或许还是不足以回答大众对演化的诸多疑问。
请注意,美国的古生物学教授远远超过一百人,这表示大多数的古生物学教授无法从事相关研究。
尽管如此,十六万五千美元听起来仍是一大笔钱,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但这笔钱能撑多久呢?幸好大学会付我将近一年的薪水(教授没课的时候仍有薪水的情况非常少见,这意味着整个夏天都没收入),但是我必须帮比尔张罗薪水。如果我决定给他年薪两万五千美元(毕竟他有二十年的研究经验),就必须帮他多要求一万美元的福利,也就是每年三万五千美元。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大学可依据校内教授的研究向政府“收税”。因此除了刚才的三万五千美元,我还必须为大学的财库申请一万五千美元,这笔钱我一毛钱也看不到。这笔钱叫“经常开支”(有时也叫“间接成本”),我刚刚说这是“税”,税率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二。每间大学税率不同,有些声誉卓著的大学甚至高达百分之百,不过我从未看过低于百分之三十的税率。这笔钱显然是用来支付大学的冷气账单、修理饮水机、维持马桶顺畅等等。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设备在我的实验室所在的建筑里只有偶尔功能正常。
总之,在这种令人垂泪的情况下,雇用比尔三年的总开销是十五万美元,剩下一万五千美元购买三年高科技先进实验需要的化学药品与设备,或是雇用打工的学生,或是支付差旅费,或是参加座谈会跟研讨会。喔,别忘了,因为要缴税给大学,所以可支配预算只有一万美元。
下一次你碰到理工科教授时,可以问他是否担心过自己的发现可能有误。他是否担心自己选了不可能解开的问题来研究,或是忽略了重要的证据。
他是否担心自己错过了那条通往正确答案的路。如果你问理工科教授最担心什么事,他立刻就能看着你的眼睛说:“钱。”
──节录自《树,记得自己的童年》/ 商业周刊
【作者简介】
荷普.洁伦(Hope Jahren),1969年出生,植物学家、土壤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目前为夏威夷大学檀香山马诺亚校区的终身职教授。三度获颁傅尔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Awards),两度获得地球科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奖,只有四位科学家曾两度获奖,她是唯一的女性。2008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署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下,成立了稳定同位素土壤生物学实验室,是美国少数主持实验室的女性科学家。
责任编辑: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