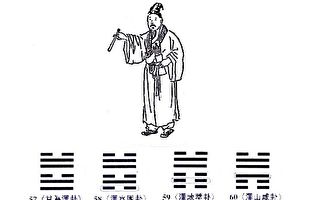亲爱的左手:
记得十年前,我是这么称呼你的。
当时我们喜欢晦涩,用一个全世界都不理解的代号,去定义一个人。我们组装密语,享受独一无二的小聪明,还有一边期待又一边害怕被拆解的砰砰然慌张。中文、英文、数字,或短或长,我们喜欢只有自己知道的特别。而似乎透过这个方式,就能牢牢地将对方锁在笔锋上,跟着每日每夜无尽无救的想念,一同落在孤单的纸面。
亲爱的左手,你给我的一串密码,代表我的密码,我至今仍留着。
那行最初用粉笔划在课桌上的数字,桃红色的痕迹,并没有被擦去。
是我的宝藏。
去年无名小站宣布关闭,好多人的青春一起尘封进黑洞里。你也知道这消息,在关闭之前,我们偶然在网路上有了久违的交集,发现原来各自都本着难改的念旧个性,去网志回顾了一同成长的花园。我说当年你锁起来的、写给我的文章,我还是进得去,所以又读了一遍。你口吻窃喜地回:“当然啊!还要把这些全都备份起来呢!”我笑了。想起自己也曾经是个认真的园丁,在明艳簇拥的园地里,虽数不清有几朵花是为了你种下,但十分确定,那时几乎用尽了青春最大的气力,奋不顾身、罔顾一切、不求成果地灌溉。每天都有说不完的关于你的事,每天都细心敏感得令人怀疑——脆弱的心,怎么会有那么坚定的勇气,耐着寂寞、距离、恼人的蒜皮小事,去爱一个人 ——明明我们那么遥远啊。
给曾经最爱的左手,很想问问,那时你写的文字、我写的文字,难道真的都有进到彼此心里吗?我真的知道你要什么,或是你希望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吗?爱好晦涩的年纪,渴望被了解却又不想坦率,这样焦躁自困的固执,让你与我都惹来了漫长煎熬。同时,也让我感到懊悔。若当年青涩的我们并没有成为恋人,会否今日仍是无话不说的知己?当年相互告白之后,碍于各种难以解释的害臊、羞赧,我们竟不交谈了。两年,还有那空窗后又延续的一年,我们面对面的真实对话、体肤接触,少至不堪计量;即使是在同间教室、同个城市、同片天空下,牵系你我的,居然剩下满坑满谷的纸条、信、卡片及简讯,再无其他。我们相爱,但总是看不见彼此的情表;尽管文字美丽又具备形体,但更多时候,我会因为这段需要仰赖不停歇的解读,才能靠近、依偎的恋情,感到可悲又可惜。
我们太爱晦涩了。两颗年轻的心,深深受到这无以名状的魅力影响,使得时光和笑和眼泪,非得都要蒙上一层薄纱,自觉更添气氛。十年流过,即便我仍可以在异乡街头上认出你的面孔,但其实早就不明白你了。我毫无自信、毫无把握,攸关你待人探挖的内心、你藏在角落锁死的盒子,无论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而这样的我——居然是一个你真心爱过的人?多么荒唐呢。给我曾经最爱的
你啊,如果有机会,好想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实实在在、确切的那种知道:音乐、生活,或者新的感情等等,你都还坚持吗?也想知道,在布满困惑的青春幕后,你可曾像我一样,尝试理解过那一个,总是希望得到答案、解释、分享,以贴近你灵魂的,小小的我吗?
十年后的夏天,我收到你的信。熟悉的字迹落在质朴内敛的牛皮信封外,里面装着一张精致的邀请卡:你的个人钢琴演奏会。我小心翼翼将它拿出、举高,摆在房间的白墙前,看上好一阵子,并用指腹缓缓摸过印刷于卡上的,你的脸。恭喜你啊,恭喜你。你终于完成了一件在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而我亦不自觉刹那想起,第一次看你弹琴的时候,自己在台下哭得一塌糊涂,吓傻了一票人。但那都是因为我明白啊。音乐之于你而言,永远就像海水之于鱼。你专注,且拥有浑然天成的气质;你的一辈子,都适合去创造独特的方式,演绎心所爱的曲子。你值得一切总和天赋与努力后的成果。你一直一直,这么前进着。
谢谢你。
纵使没能北上一趟参与你宝贵的演出,我仍有好好收着这封信。每看它一次,我就觉得,过去围绕着彼此的乌云,正逐渐散开。你不再突然消失了,我也不再固执于一个句号,自虐般等待。那个为了你跷课、坐着公车环绕整个市区、走逛每间你所爱的店,然后默默伤心的我,也长大了。火车站前一身匆匆逃走的背影,无数次难以割忘的六月 ——我皆无须害怕。我们终于可以好好说点什么了。
就要二十五岁,你会遵守十年前的约定,来见我吗?或者,我们其实还有好多个十年可以消磨。走到今天,写到这里,真觉得世界之大,远远超乎当时我们所想。面对说不完的傻事、度不完的年轻、伤不完的伤,都会慢慢习惯的吧。亲爱的左手,你就是我左边掌心上最大的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自今而后,把晦涩留在过去、把窗打开,允准洞悉灰暗的明朗流淌进来。是的,神秘之余,别再忘了给他人机会,透视自己。
我们都将有新的人。
我们都有新的人。
我们隐晦的秘密,在今天、在往后,在每一个相信人心的日子里,都有温柔的光亮将之瓦解。
──节录自【这里没有光】一书
作者简介:
1991年12月生,高雄人。毕业于高雄女中、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惯于往返南北,一枚双栖动物。熟稔于糟糕的生活、糟糕的文字。相信创作能够缓解苦痛,也能够加剧痛苦。相信所有人都是抱着痛苦活下去的生还者,也相信这样的生还,更有意义。
责任编辑: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