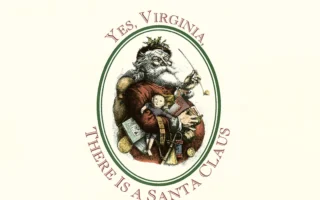一早起来,匆忙打发儿子上学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说是忘记拿月票,没法上车,所以只好回家。我说:“你天天坐这趟车,不能跟司机说一声,忘了带月票了吗?”儿子申辩道:“车上写着来着,上车必须出示月票,否则,就得买票……”唉,大早上起来,时间最紧张了,没办法,还得慌慌张张地开车送他去学校,早上堵车厉害,没准大家都得迟到……
仔细想想,儿子才十几岁,已经满脑子德国思维了。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付款台前有牌子写着,“请把您买的所有物品放到传送带上”,他就一丝不苟地把七八盒牛奶或大瓶饮料统统搬到传送带上。开车路上,看到路边的限速牌子也总是立刻提醒我,限速多少多少了,该减速了。
一位同胞曾开玩笑地说起他家的自制面包,他孩子用面包机烤的面包总是很成功,而太太动手时多半是未知数。因为孩子是严格按照菜谱放的料,太太呢,今天突发奇想放这个料,明天又心血来潮添那个料,而且比例也是中国人式的,这个少许,那个适量,所以烤出来的面包没有重样的,每次都是一个“惊喜”。
其实,不仅是儿子,我在德国时间长了,脑子也变得有点“木”了。有一回,儿子说足球没有气了,不能玩,我也只好望球兴叹,因为我的气筒口太大,没法打气。正好老爸在此探亲,搞清楚事情原委,老爷子拿出我们的打气筒,在前面包了点碎布条,把出气口变小,这样给儿子的足球打满了气。
记得很多年前回国时,等红绿灯过马路,被同学们当作笑谈。最近去美国开会,却也吃惊地发现,纽约人也是不等红绿灯的!而且美国人自有独特的美国式的创意,现在想起来依然忍俊不禁。
我们去的人多,主办单位准备的车子不够,我们那辆黄色的校车(跟陈旧的老式中国公共汽车类似)根本装不下。我们这一车大都是欧洲过去的,大家都很守规矩,一个座位一个人。眼看还有一大半人上不去,大家都不知所措。
这时上来一位高大魁梧穿着制服的黑女人,铿锵有力地对着人群大声说:“左边多挤一个人,右边多挤一个人,中间再加一排,快!”言毕,黑影一闪又下车了。这些装着西装革履、踩着高跟鞋的“欧洲绅士小姐” 们如梦方醒,乖乖地照办,很快都塞进车里了。甭管怎么不受用,反正车是开动了,最后大家都到达了目的地。
德国的机场,什么航空公司,哪班航班,哪个窗口都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凡是排一个队办手续的,都是要乘坐同一架飞机的。可是美国不同,那里好像是按照航空公司分配,不管是哪班航班,飞往哪里,何时起飞,只要是同一家航空公司,就都在一处办理手续。所以,当我按照在德国的经验赶到机场,看到满大厅拥挤的人群,连排队的队形都找不到,问讯处也没有,顿时傻了眼,心里真担心赶不上飞机了。排完了办理登机手续的队伍,交了行李,还有更长的入关的队伍要排……总之,当我一路奔到登机口的时候,那里已经空无一人,空姐只问了一句,“去法兰克福?”我连哧带喘只剩下点头的份,就被放行了。
其实在纽约最精彩的是那个夜晚。那天我们开完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一行十人,酒店在纽约郊外,坐地铁费时费事。我们打算打的走,因为美国有很多加长的、加宽的出租车,大家可以做一辆车,即快又省钱。不过,不巧的是,等了好半天也没有遇到一辆,我们又不想分头走,还想省钱。这时一辆比一般私家车稍大一点的出租车停下来,愿意拉我们。可是十口人怎么能挤进五人座的轿车?黑人司机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唰地把后备箱的门打开,示意后面可以坐人。大家都觉得又好玩又不可信,挤了又挤,尽量缩小自己,最后,副驾驶座位摞了两位,后排座挤了四位,后备箱里塞了四位,再加上几大袋资料……然后我们一边欣赏着曼哈顿美丽的夜景,一边开心地说笑着回到了郊外的酒店。
想来,这种历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得到的。先不提我们是否违规,也不讲那个司机是否明知故犯,反正对我们这些欧洲过去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