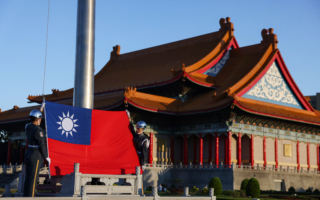【大紀元6月8日訊】談到今日中國鄉村交通的變化,最值得回味的是胡適先生寫在1927年的一段話,「今年三月裡我到費城(Philadelphia)演講,一個朋友請我到鄉間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車往鄉間去,到了一處,只見那邊停著一二百輛摩托車……這真是一個摩托車(註:胡適說的摩托車包括汽車)的國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車去做工,大學教員自己開著汽車去上課,鄉間兒童上學都有公共汽車接送,農家出的雞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車送上火車或直送進城。」(胡適,《漫遊的感想》)
上世紀初胡適在美國看到的情景,如今的中國鄉村已經隱約可見,儘管中國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輪子上的國家」,也沒有「輪子上的鄉村」。
先說說我過去的一點經驗與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發生一起嚴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於誤食了一種劇毒蘑菇,至少有十幾位農民中毒死亡。這是我第一次以記者的身份到永修採訪。在採訪過程中,我注意到縣城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有蹬著頂篷三輪車的車伕。在當地,人們把這些用盡腳力的「的士」稱作「蹬士」,也有人稱之為「肉的」,大概是笑話這種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車燒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關於蹬士,在一部描寫當地生活的長篇小說上我讀到這樣一段對白:「公司垮了,我倆的退休工資上哪兒拿?現今公司的好多職工日子過不下去了。只得下鄉割禾,上街騎蹬士,都走到人生盡頭啦。」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一些在公司裡做事的白領一旦走到了「窮途末路」,要麼下鄉種地當「無領農民」,要麼上街跑步前進賽駱駝祥子。對於這種邏輯,相信許多熟悉中國城鄉分治與隔離的人可能並不認同。因為對於許多進城務工的農民來說,為人力車出賣自己的「人力資源」,可能只是另一種新生活的開始。
趕巧,在那次採訪過程中我遇見了幾年前九江抗洪時的新聞人物楊平英,當時她正領著自己的兩個小孩為誤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鎔基把號稱「固若金湯」最終泡湯的九江長江大堤稱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楊平英因為懷抱兩個得了佝僂病的雙胞胎女嬰站在大堤上成了新聞媒體救助的對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復常態,楊平英把自己的家從鄉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縣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當「蹬士」。
一位車伕曾經和我談起,在這個小縣城裡有一兩千輛頂篷車。蹬車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鄉村的農民和本縣的下崗工人,他們早上6點鐘出門,一直蹬到晚上10點左右,平均一天能賺上十幾塊錢。老實說,對於人力車這種謀生方式,在感情與理智上我一直難以接受。霍布斯說人類為避免「人對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國家,在我看來,東方的「道德人力車」卻讓人進入了「人對人是牛馬」的時代。我雖然不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價值,但是其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遠坐在車上,有人只配當牛作馬往前跑麼?而以此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車政治」麼?
所以,2008年夏天,當我再次路過塗家埠時,首先想起的就是當地的人力車伕。和過去一樣,這裡依舊「蹬士」滿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車以外,現在還有不少摩托車和小汽車。在當地,靠「拼車」攬活的小汽車更像是小公交,它沿著縣城的主要道路來來往往,通票兩元,隨時有乘客上下。
面對如此人車混雜的場景,恍惚之間我彷彿走進了歷史。這是一種似曾相識的印象———就像胡適當年在哈爾濱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線」,那裡既有摩托車,又有人力車,「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製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以東方的人力車文明為參照,對美國的摩托車文明讚不絕口:「這種開車的訓練真是『勝讀十年書』!你開著汽車,兩手各有職務,兩腳也有職務,眼要觀四處,耳要聽八方,還要手足眼耳一時並用,同力合作……什麼書呆子,書踱頭,傻瓜,若受了這種訓練,都不會四體不勤,五官不靈了。」似乎在胡適看來,能夠和游泳一樣協調人體四肢的就只有開車了。
當然,「摩托車文明」並非十全十美。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美國的「摩托車文明」同樣可能導致「裝甲車不文明」———世界各國因為搶石油而單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麼秘密。顯而易見,胡適在這裡著力批評的是東方的「膝蓋上的文明」(人對人的下跪),其目的在於解放人。至於胡適在文中流露的純真情感與難以抑制的怦然心動,我想只有正在初戀的人才能真正體會。
整體而言,胡適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還是「慄慄危懼」、半盤接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所謂「半盤接受」,是因為只接受了「摩托車」)。古文字學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憶早年在北京時經常開摩托車在長安街與汽車競賽,熟人見了都為之擔心,說「你搞古文字學這行,應當坐牛車啊!」事實上,剛開始胡適也不太敢坐知識分子開的車,擔心他們像哈裏‧波特一樣天馬行空,在開車時思考哲學和天文學方面的問題。不過坐了幾次後胡適也就不害怕了———因為那些教授自從接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洗禮,不那麼「心不在焉」了。(ht
上世紀初的中國,汽車只是有錢有勢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車文明」在中國攻城掠地,城市被汽車佔領,而鄉村則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車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難行的街道和晚間擁堵不堪的小區見證汽車飛入尋常百姓家;後者,像印度、越南等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鄉村正在由「自行車王國」變成「摩托車王國」。由於許多大中城市都開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車不斷降價,摩托車開始上山下鄉,希望能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自從2001年南昌「限摩」以來,當地的摩托車經銷商們紛紛把「戰場」轉向鄉村。就這樣,鄉下孩子們過去只有在放露天電影時才能聞到的汽油味如今四處流溢,終年不絕,早已不復當年芬芳。
談到摩托車下鄉對生活的改變,有農民驕傲地說:「現在出門種田,只要一騎上摩托車,幾分鐘就到了地裡。真沒想到,我們當農民的也能享受到這份『瀟灑』。」儘管年輕人偶爾會騎摩托兜風,但在鄉下摩托被賦予一種「求真務實」的樸實性格。它沒有《摩托車日記》裡格瓦拉式理想主義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樣在美國成為彙集自由大道、原始動力和美好時光的象徵,成為時尚男人胯下兇猛的鋼鐵動物。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說,摩托車不過是種兼具助力與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幫手。2008年12月有則新聞說,重慶10位農民工因在東莞打工的工廠老闆跑了,沒有拿到工資,於是只好將廠裡已報廢的十輛三輪摩托車改裝成「大篷車」,帶著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帶走的財物踏上了返鄉之旅。由於車況不好,這群「中國吉蔔賽」從東莞到重慶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難理解,在交通閉塞、公共設施匱乏的鄉村,摩托車同樣是農民賴以自救的權宜之計。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農民的「賺錢機器」。就像縣城裡有人力車伕一樣,在一些通向五裏三鄉的關鍵路口常常會有摩托車在那裡守候行人。不過這一次,當我像往年一樣,在熟悉的三岔路口叫停巴士並且準備坐摩托回家時,發現自己徹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見有摩托車來,直到後來在路邊的村子裡發現泊著一輛破舊的桑塔那。事後知道,此時「摩的」稀少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現在不是年關,而且每家都買了摩托車,客源少;二是因為摩托不安全,在當地出了不少車禍,一些做載客生意的人要麼退出,要麼換了小型麵包車。
「西弗吉尼亞,大山媽媽,帶我回家,鄉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實的鄉村了。我坐的是輛黑色的桑塔那,據司機說是從上海買來的報廢出租車。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車內無所不在的泥土、穀粒和青草,更襯托出這車是可以暴走鄉下的「山寨」版坦克。由於連下了幾天雨,正在翻修的鄉村公路多有坑窪泥濘,最後司機在我的建議下走了山間另一條大路。不得不說,我又一次失算了。由於近年來鄉村荒蕪,草木茂盛,這條大路也像關天茶舍裡的好帖子一樣淪陷在枝條與茅草之中。好在司機沒有退縮,開著他的坦克繼續勇往直前,半壓著灌木前行。世界變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儸紀公園裡探險———雖然這裡沒有一隻恐龍。有趣的是司機,雖然手忙腳亂,仍不失時機地說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見過豹子下河喝水,嚇得沒命地跑了。在這寂靜的山林,儘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動物的。
穿出叢林,拐了幾道彎,坐著「山寨」版坦克,我終於回到了我的江南鄉下。願這裡永遠陽光明媚,空氣清新,萬物生長。
轉自《天益》(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