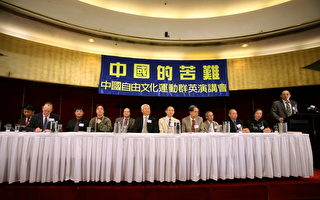【大紀元12月26日訊】十年前文章「我依然拒絕低頭進入那個知識界」發表按:
這篇寫於十年前,一九九六年二月的文章和信件,由於許良英先生的反對,一直壓到今天沒有發表。現在作為我為自由文化運動大會所寫的文章,《自由文化運動和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極權主義及其文化問題批判》的附錄說明發表。因為我認為這篇文章可以說明筆者的一個觀點,八十年代,寄生於極權主義社會的知識精英,甚至包括所謂「自由派」,對於任何異於他們—共產黨正統統治思想的傾向都是極為敏感的。他們對統治者溫文爾雅,對於一個年輕的異議者卻兇猛異常。很多時候,他們甚至可以說非常自覺地幫助政府禁錮圍剿異各種背離他們的傾向。
現在發表它,我還有另外一個目的,那就是希望我的經歷能夠給年輕一代的青年學生提供一點經驗,在他們被其「導師們」圍剿的時候,不要輕易否定自己。我自己在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反叛路上,經常遇到這類問題而彷徨徘徊,難以找到繼續走下去的支持。三十年來的經驗使我可以告訴你們,應該懷疑的是他們。
為此,我更希望在中國有思想的青年人、大學中的學生,能夠起來重新審視你們的導師、教科書,以及所謂學術刊物。我可以肯定地對你們說,他們教給你們的「知識」 ,不僅社會科學而且包括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的不一樣,和中國傳統的也不一樣。你們為什麼要單單要相信他們,而不是相信其他的知識傳統呢?
你當然也可以相信他們,但是,一定要在重新審查過他們的思想方法、道德規範後。這就是近代社會產生的基礎,一個社會不被專制者愚昧的基礎。由於我深受其害,先是受其影響、教育並且有所參與,後是受其封殺打擊,所以,我願為後來的思想問題研究者、青年人提供一個具體的案例,把這一切交給後來的人來審判前幾代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我希望以後青年人的成長能夠有一個正常的知識、人際和社會環境。
對於第二個附件,給戈革先生的信,筆者在此要補充說明的是,這封回信的背景是,戈革先生一方面在會上反對還學文和我參加翻譯愛因斯坦全集的工作,另外在會下同時給筆者來信,邀請筆者為上海的出版社全權自己負責選擇翻譯一本有關海森堡的傳記。筆者在收到戈革先生信的第二天,收到許良英先生告知會議情況的信件,為此,筆者寫下了下面這兩篇給戈革、梁存秀等諸位先生的公開信。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德國埃森
我依然拒絕低頭進入那個知識界
─關於自然辯證法問題爭論的繼續
─仲維光─
(一九九六年二月)
筆者按:
一九八六年年初,因為自然辯證法教授查汝強先生出來攻擊另外幾位自然辯證法界前輩和方勵之先生,為此幾位前輩決定寫文章反駁。那時候,我雖然正忙於論文寫作,但是感到批評自然辯證法,這是一個應該發言的機會,因此,也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和其他幾位同學的文章,在許良英先生家兩週一次的討論班上讀了。在場的范岱年先生同意並在當年第三期的《自然辯證法通訊》上得以發表。國內的理論信息及文摘報等都立即報導了這一對自然辯證法的發難。接著,《自然辯證法通訊》、《自然辯證法研究》等各個刊物都發表了查汝強反駁我的不同文章。九月號的《哲學研究》在登載查汝強攻擊我的文章前並加了一整頁的編者按語。九月底,《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也陸續開始設專欄討論這一問題。然而,在其後的討論中,雖然我被不斷地點名批評,卻遭到各方面的封殺,沒有答辯機會。
首先是《哲學研究》。我給《哲學研究》寄去第一篇答覆的文章,從一些物理學問題討論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問題,否定一分為二對物理學有任何積極作用。編輯部在拒絕發表該文的答覆信中說,你談的太專業化了,我們希望就一般的哲學和科學的關係討論。於是我又寄去第二篇文章,專門討論哲學和自然科學間的關係。當然是從科學史的角度論證自然科學和這種自然哲學式的自然辯證法沒有親緣關係,有的只是對抗。自然這次又遭到拒絕。編輯部在回信中說,我們發表文章是有學術考慮的。這引起了我的憤怒,我立即給該編輯部回了一封強硬的信。在此信中我說:談到學術考慮,那正是我們這次辯論的焦點。如果你們知道了什麼是學術研究,那麼這場討論就結束了,有了答案了。看看你們《哲學研究》過去三十年來發表過的文章,有哪一篇能留下來今天還能讓人看。你們發表過的文章可以為你們換職稱,提工資,但是唯獨對社會、對學術、對人民沒有任何益處。你們發表文章攻擊我,卻封鎖我的聲音。如果我的文章學術水平不夠,那不正是可以讓讀者更加同意你們的觀點嗎!
此信內容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傳回到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那些依靠這類雜誌生存的知識分子們感到了我對他們的蔑視。我同研究室的閻康年先生以規勸的方式恫嚇我,你難道不想提職稱、提工資了嗎?我對他說,我確實早就不想了。
與此同時《自然辯證法研究》也客氣地壓著我的文章不予發表。而我投給《自然辯證法通訊》的一篇答辯文章,在即將發表時被范岱年先生以資料陳舊拿下,並且幾乎作為那位責任編輯的事故來處理。該文是從科學史角度論述德國的自然科學的發展正是以洪堡為首的自然科學家和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鬥爭後,引入英法的經驗論和唯理論思想的結果。自然辯證法這種黑格爾式的自然哲學完全是對抗近代科學思想及其方法,對抗近代啟蒙思想。這篇文章當時也被選入一本準備出版的文集《自然辯證法向何處去?》,但是在我出國後,也立即被梁存秀先生拿了下來。當然即使如此,那本文集也還是被更正統的勢力封殺了。
在那幾年中,從知識框架到研究方法我都仍然處於不斷地反省自己,重新建構自己階段。我在黑暗中的摸索,知道的越多,也就愈加感到自己的幼稚與無知。我曾經不止一次引用赫爾曼在《量子力學初期史》中所說的一段話,那時你面前是一個大廈,稍微不留心你就會被說成是一個生手,而被排斥。我對此深有體會。所以,面臨一切打擊和排斥,我沒有說什麼。
當然我知道我和自然辯證法界的任何一派人都是不一樣的,我追求的知識框架和方法,即近代科學所帶來的認識問題的思想和方法,啟蒙思想,自由主義思想,從根本上是和自然辯證法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對立的。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要成長。既然國內不能讓我邊學習,邊寫作,沒有人能幫我進一步打開眼界,我只得在八八年決定暫時出國,以尋求新的幫助和發展空間。
在德國期間,一方面我得到德國「批判理性主義」的代表人,卡爾波普的學生和朋友哲學家漢斯.阿爾伯特的支持,通過閱讀文獻進一步打開了眼界,堅定了我的想法,另一方面在波鴻大學馬漢茂教授處做研究時,重新反省了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的各種思想傾向。我一直想寫一篇關於這場爭論的研究性文章,作為「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研究」研究系列之四,主要對自己進行批評和解剖,材料已經準備好,但是苦於涉及自己而不知怎樣下筆才更好,故一直拖延至今。然而,這場爭論,及這場爭論引起的心結感情,不僅我沒有忘,諸位自然辯證法界前輩也因為我在海外的對極權社會中的大陸知識分子的無情解剖而更加耿耿於懷。
去年年底,國內的老師因為知道我一直有志於國內的文化知識問題,因此來信問我是否願意參加中文愛因斯坦全集的翻譯工作。我在碩士期間研究的題目就是愛因斯坦的量子論思想。在出國前曾經翻譯發表過多篇關於愛因斯坦和其它物理學家的科學與思想問題的論文,並且八九年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翻譯出版過一本愛因斯坦傳,《愛因斯坦和他的生活》。這是國內出版的唯一一本愛因斯坦的生活性傳記。作者是一位和愛因斯坦一家交往多年,原來學藝術史的女作家。所以,雖然我明知這次翻譯愛因斯坦全集的報酬還不夠郵資,三十元一千字,我們在德國的生活也很困難,但是,為了能為中文世界多一些事情和感謝老師的關心,還是願意參加工作。然而,真沒有料到就是這樣一個翻譯工作,多年逃離出大陸知識界所編織的網的我,剛要上網,就又產生了一場風波。
從來沒有當面批評過我的文章,在一月十二日的信上還說我文章寫的不錯的戈革先生,二十日在北京向許良英先生突然發難,認為我不夠資格做這項工作,因為我的文體和金觀濤的一樣,都是「精英體」,對這種所謂「海外精英文體」,他非常不以為然。接著梁存秀先生在底下說同意戈革先生的意見,如果還學文和我要參加翻譯,必須先翻譯幾篇讓他審查一下,看能否合作。
任何聽說這件事情的人都很奇怪,「翻譯」一些文章竟然還會遇到這些問題。顯然這後面有其它問題。如果聯繫到前述心結,及近年來我繼續對封閉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的不恭,也就清楚了。哲學所的梁存秀先生這次情緒的發作和刁難是過去我與自然辯證法界和《哲學研究》雜誌對抗的繼續。過去表面上我雖然是和自然辯證法界的左派,查汝強和何祚庥等人對抗,但是骨子裡我卻是對整個自然辯證法界和科學史界的不敬。這就是今天自然辯證法界的所謂開明派要給我一點顏色看的原因。這甚至也是我對整個極權社會的知識界不買帳的結果。在思想上和學術上我對他們如此「放肆」,這次居然又往他們手心裡跳,他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收拾我的機會。只是我還是不買帳,要收拾,拿到桌面上來,讓世界,讓後人看看是怎麼回事。我是不怕丟醜的,因為我生在你們那裡,長在你們那裡,無論在學術規範和道德規範上都曾經夠丑了,現在無論怎樣都只會好起來。
事實上,這一對抗,早在八六年八七年他們對我的封殺中就開始了。無論自然辯證法的所謂開明派前輩們怎樣,在我來說,只有拋棄自然辯證法的問題,根本沒有《自然辯證法向何處去?》問題,因為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從恩格斯寫作它那一天起就沒有任何積極意義。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所以受到范岱年先生和梁存秀先生的排擠也是有道理的,我不認同他們的知識框架和文風,他們當然也不會認同我,這是毫不奇怪的。
「自然辯證法向何處去?」同樣也是雞蛋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爭論,我不屑一顧,所以爭論雙方就自然把所有的「臭雞蛋」都拋向我。然而,如果所有的臭雞蛋都為此扔掉,不能再進行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爭論了,我還是感到欣慰,總算是轉向一些有意義的問題了。為此,我希望能把我和這些前輩的爭論公諸於社會。只是,這不僅是文風問題、自然辯證法的知識框架問題,而是極權社會的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我認為,意識形態依附於極權社會的「開明」「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會帶來新的價值和方法,不會吹來清新的風。
距第一次批評自然辯證法(八六年)界的極左派整整十年,現在,終於開明的自然辯證法界前輩給於我不得不講幾句話的契機。我把給前輩的信公開如下,這應該才是真正的涇渭分明的辯論和反思。不是自然辯證法向何處去,社會主義向何處去,而是要不要自然辯證法,要不要否定極權社會的文化,知識分子要不要反省自己?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德國,埃森。
戈革先生並轉梁志學等自然辯證法界前輩
戈先生:您好!
去年年底,劉遼老師來信徵詢還學文和我是否願意參加愛因斯坦全集的翻譯工作。我原無意參加此事。因為我手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時間和精力。但是想到劉老師的好意,想到我們對愛因斯坦思想和人品的喜愛,並且今後我們還想做這方面的工作,就對劉老師說願意做一點。但是,沒有料到就是這樣一件小事,「翻譯」而還不是寫作,竟然會引起戲劇性的反應,有人認為我「文風」不好,而不願我參加,甚至把我和金觀濤相比。這真讓我羞慚汗顏,我一直把這些人看作老師,覺得即便過去他們曾經參與了共產黨文化的創建,但總還是和共產黨文化有些距離,對我多年來的努力應該能看到。沒想到我錯了。不少人說,我寫文章總是把話說的牙青口白,甚至點名。但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我對我談的問題和批評負責,二希望所提的問題能夠得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這一次不幸又是如此。
現在恰好您來信也談到我的文風,我願意把我對自己文章的反省,把當年關於自然辯證法辯論的一些事情的反思和想法拿到桌面上來和諸位老師交換看法。
一.關於我批評查汝強的文章第一篇文章
─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對自然辯證法的批評
我在寫作關於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的系列文章中,本來準備把那次批評自然辯證法事件作為一個案例來剖析一下。在寫作這個系列的文章的時候,尤其是有關這個案例,我多次強調想以自我批評,自我解剖為主。這篇文章由於涉及到「自己」,所以究竟如何處理我始終沒有想好,因此一拖再拖,至今沒有動筆。但是我自九○年後就不止一次地在研討會、會議報告中坦承,對曾經寫過那樣的,儘管是批評馬克思主義、抨擊自然辯證法的文章,感到臉紅。我認為那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對抗式的文章。我再也不會用那樣的語言和方法去寫作了。
我曾經多次以我自己的例子向與會者說,我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背叛馬克思主義,從認識論、科學思想開始反思,但是時過十五年,到八五年,我的文風還是沒有完全變過來,八八年我在自然科學史所做的報告中也說過,我做的首先是擦黑板,但是怎麼擦還是有很多痕跡。我這樣自覺的去努力尚且如此,那些沒有意識到這點的人,只會比我更糟糕。我這樣說,是以期引起人們對共產黨文化的反省。這也是我一直想把八十年代中期有關自然辯證法爭論事件,作為一個思想史案例,重新記述呈現給讀者的目的。我願意讓後來的年輕人看到,到八五年,我作為一個反叛馬克思主義十五年的人,卻依然寫出那麼醜的東西。
雖然如此,在何祚庥所編輯的查汝強文集中,他的後記卻還是給了我一定的安慰,那就是他說,仲維光提出要取消自然辯證法。這使我很高興,因為這是我當時所有所做的唯一一點有價值的工作。我和那些要修補自然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同,而是要否定它、拋棄它。
其二就是我的文章無論就問題的提出,還是論述的角度,還是遠比所有參加辯論的其他人的文章要好,因為只有我不是從自然辯證法的角度論述問題,而是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否定它。
二.關於梁存秀先生和范岱年先生扣押我的批評自然辯證法的那篇文章
─從科學史的角度提出要根本否定這種自然哲學
我給梁存秀先生的那篇文章,是從自然科學史的角度,就我能得到的資料,來闡述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科學史的發展毫無作用,而且這種黑格爾式的自然哲學在德國的嚴密科學史上是被趕出去的對象。為那篇東西還學文在德國的一些期刊上幫助我查找了很多資料,那時我還不懂德文。這些資料都是在國內上沒有出現過的。但是這篇文章被范岱年先生以資料「陳舊」為由在即將登載時拿了下去,在我離開大陸後也被梁存秀先生從文集中拿了下去。
先說范先生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為無論怎麼說這篇文章的資料都比《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登載過的金觀濤、樊洪業等人的文章資料不但新,而且多。這篇文章寫的並不好,不成熟,但是不比金觀濤及雜誌上的其它文章更差。並且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重要的。即自然辯證法與自然科學毫無關係,而且這種自然哲學曾經阻礙過德國自然科學的發展。
我到德國後,曾經請德國的卡爾.波普的批評的理性主義哲學代表哲學家漢斯.阿爾伯特先生就我想要從事的關於自然哲學的研究寫一封推薦信。他推薦信的第一句話就是,「自然辯證法式的自然哲學過去和現在從來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毫無影響,這個問題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對於來自馬克思主義國家的人卻是值得弄清楚的。」
說實在的,當我提出這種問題時,我感到羞愧。這種無意義的,毫無學術價值的問題,而我卻提出來研究。像下文提到的實在論和唯物論區別這樣的問題也是這樣的毫無學術價值的問題,但是在我們中國的「科學哲學權威」們那裡,卻居然成了一個學術「發現」。即就這一點而言,我永遠也不能原諒范先生、梁先生對這篇文章的扼殺。這個問題早就應該由他們提出來,他們沒有提出來,我提了,他們還壓制我。由於他們的壓制,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提出來。而且他們只會打擊封鎖像我這樣的人,而對金觀濤以及類似的人,很遺憾,他們從沒有做過什麼以盡學術界權威和前輩職責的事情。當然他們不可能做什麼,因為金觀濤們是他們培養的產物,是沿著他們所走的道路走下來的,在「學術」基礎上,他們對金觀濤們沒有反感。他們對我極為敏感當然也有道理,因為我是要反叛他們,對他們的思想不屑一顧,要把這些理論送進墳墓。
再說梁先生那本文集中的其它一些文章,就討論的方法和使用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來說,沒有任何學術價值,例如吳國盛的文章,典型地是在自然辯證法中,在馬克思主義中討論自然辯證法。這種文章從所用的概念到論述方式,語言都是純粹自然辯證法式的,所不同不過不是查汝強的結論而已。實際上這種自然哲學從根本上就是和自然科學格格不入的,它的認識論基礎完全是專斷的。
自然辯證法向何處去?根本就是一個無意義的問題。整個文集除了有一點社會意義外,毫無學術價值可談,可談的就是如何把這種哲學扔到紙簍中去。由於我正處於轉型時期,我的文章有不少毛病,甚至很嚴重的毛病,但是我提出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這是那些文章遠遠不及的。
梁先生拿掉我的文章,只是說明梁先生仍然維護自己的知識框架,看不到外面的東西。對梁先生來說,這無非意味著共產黨不對,查汝強不對,但是梁先生們是對的。而我要批評的主要是思想和知識框架,而不只是批評查汝強個人,這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當然包括梁存秀、許良英老師和您們這些曾經很深地參與自然辯證法工作、討伐過西方科學家及其思想的前輩。
諸位自然辯證法界前輩,你們那個人沒有從事過這種鞭撻工作呢?可是你們哪個人對自己的以往有進行過徹底的反省和自我批評呢?看看你們以往和現在的文章吧?那才是真正的極權社會的學院精英體鼻祖,我不過是受了你們一點影響,而且在不斷地擦拭還是擦不盡而已。
雖然如此,儘管我認為極權社會的學院精英群體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是我還是願意和你們坐在一起,就你們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逐字逐句地分析,如果你們現在有了能力,可以幫助我排除那些尚留在身上的痕跡,我還是感激不盡,因為,我早對自己身上怎麼也擦不盡的你們對我們這一代的這些影響深惡痛絕了!
我今天之所以重提這些問題,正是要表明梁存秀先生和查汝強等人一樣不僅是共產黨文化的產物,而且是這種文化的維護者,梁存秀先生和查汝強等人的區別不過是性格,一些觀點,一些做人方式不同而已。這也是梁存秀先生先天就感到和我格格不入的原因,因為在學術上如果真是如我所說的那樣,如我的看法,他們這一生就全被否定了,全完了,什麼也沒有了。
今天重提這一問題也使我進一步清楚,我們所說的自然辯證法界其實就是梁存秀先生和諸位前輩,所謂於光遠的一圈人,近半個世紀在中國所經營的事業。這當然包括何祚庥,這位於光遠當年的跟包,後被送到蘇聯學習物理的「紅小兵」。我和諸位前輩的分歧正是過去和查汝強爭論的繼續,這場自然辯證法問題的爭論遠沒有結束。我是誤入雞群的一個異類,諸位沒有進行過反省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界前輩,當然不會容忍我不斷地對此發生異聲。范岱年先生和梁存秀先生扼殺我所利用的正如阿明.赫爾曼在《量子力學初期史》中所說的:那時你面前是一個大廈,稍微不留心你就會被說成是一個生手,而被排斥。
最後,就是梁先生在八八年我離開大陸之前就此文集問題和見過很多次面,直到我離開大陸前兩天還和他通過電話。但是,梁先生從沒有向我說過一個「不」字,讓我修改,而在我離開大陸後就拿下我的文章,這就是你們的道德嗎!這樣做人未免太沒有品質了罷!
三.再談極權社會的文風和極權社會的文化知識問題
如上所述,當我自省我的這篇文章時,並不意味著梁存秀等人的文風就好,我的文風是受這些前輩的文風影響而來的。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對許先生說,我們這一代如此就是受你們那一代的影響所至。你們在過去自然辯證法雜誌上寫的文章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文章,並且你們的寫作比那些共產黨中宣部中專門從事宣傳的人還有迷惑性。
我曾就扣押我的文章給《哲學研究》編輯部寫過一封信,信的原文留在北京家中了,在信中,我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你們懂得什麼叫學術水平嗎?看看幾十年來的《哲學研究》,哪篇文章能夠留下來。如果你們知道什麼叫學術,那麼這場辯論也就有結果了。
本來我的反省是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反省自己。但是並沒有達到這一效果,好像受過前輩影響的我不對,而在主流文化中您們這些老前輩是永遠正確的。
對梁先生和范先生扣押我那篇文章,我沒有說什麼,因為,那時我在另一方面也自知文章還有很多缺陷,但是,絕對不是他們說的那種不行。現在。梁先生又來批評我的文風,我想,如果他從來沒有反省過自己,那麼他批評我的「角度」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不僅如此,我認為,他沒有資格批評我。他不放心我,我還不放心他那種知識框架和語言方法呢。坦率說,他寫的那些東西和四九年以後的在各類所謂學術刊物上的那些狗屁文章有什麼區別。
我自從七十年代初期反叛後,就不再看那些共產黨文人寫的東西。意識形態有了一個變化。自從我進入自然科學史研究以後,逐漸接觸到真正的學術研究是什麼,研究方法有了一個變化。自從我到了海外在海外寫東西,語言逐漸有了變化,現在,我還在緩慢地變化。我一個四十多歲的人,還要在知識和語言上補課,其中除了政治原因外,完全就是因為上一代知識分子太不行了,如果上一代稍微行一點,我們就會少走很多彎路。如對自然辯證法的看法問題,以及很多研究方法和資料問題。我的導師們居然沒有一個人有能力能夠指導我。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上一代人在《自然辯證法通訊》和《哲學研究》等等刊物上發表的東西不是沒有罪責的。白紙黑字影響了多少人!時值近日,戴念祖和沈惠川等人不都是老一代人影響下的產物嗎。你們反省過自己嗎!
這就是我在「我們的精神究竟在什麼地方病了」一文結尾引述哈威爾的話所強調的,問題不只是共產黨,束星北、王福山,而是我們每個人。「當我們提到道德敗壞的環境時。我並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從不往窗外望的特權人物,我指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早已習慣於極權統治制度,接受它作為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並允許這事實一直運作下去,我們不只是它的受害者,我們也是它的創造者。
如果我們把過去四十年來的悲傷情況看成是某位遠親送給我們的一件東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我們必須要求自己對這個情況負責。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我們才能明白,我們是可以改變這個情況的。我們不能把過錯全部推到以前統治過我們的人身上。不僅因為這是不正確的,而且這麼做會使我們低估自己應負的責任,以致我們不能主動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擇。」
四.寄生在極權社會的政治文化上,還是反叛極權社會的政治文化
─關於我的文章和金觀濤的文章的區別
在我從裡面向外走的時候,我的文章當然仍然存在著很多受梁存秀這些前輩文人影響的痕跡,這是我和金觀濤文章相同的地方。但是我的文章和金觀濤的文章還是有根本的區別。
這些區別表現在:
1.對我來說,首先要解決的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即知識框架問題,反省自己,重新審視基本概念,要求自己言之有物,有據,力戒說假話空話,力戒談自己不瞭解的東西。雖然我談的也許仍然不精確。
2.在語言上追求清楚、明白、直接、樸素。
3.我的文章談具體問題,不要建立體系,不聲稱探索歷史規律和為現實政治服務。
4.我不利用文章和前輩們拉拉扯扯搞關係,獵取社會和政治效應,向上爬。這種傾向在諸位和姚文元戚本禹同時代的前輩身上也曾有過不同的反映。
5.范先生一手提拔的金觀濤惹諸位前輩不快,是因為搶了風頭,佔了諸位前輩的位置,不把諸位放在眼裡。而梁先生等諸位前輩不肯見容於我,則是因為我對這樣的權威和地位不屑一顧,對諸位前輩的知識框架和文風不屑一顧。雖然都是不屑一顧,但不是一回事。
凡是對共產黨文風和文化有一定認識和看法的人,有一點真正哲學知識,不是共產黨教科書上那樣教條概念,把一切哲學都歸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人,必然會看到我的文章和金觀濤的區別。
至於諸位自然辯證法界前輩是寄生在極權主義的文化上,還是在追求另一種文化和學術?你們的過去乾淨嗎?你們的學術研究乾淨嗎?你們的目的乾淨嗎?那需要每個人自己反省,不用我來說。我指的當然不僅是政治,而且包括學術研究方法、語言、概念上,與最根本的對哲學等思想問題的理解。
五.極權文化中蛻變出來的艱難
─我現在對自己文章的反思。
我深知,一個在那個文化環境中長大的人,在二十歲以後改變自己,重新建立另一種精神和思想,重新用另一種方法研究寫作的困難。這種改變也許確實如毛澤東所說的是脫胎換骨的改造,因為我們已經被毛澤東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這個改變中,我沒有能得到諸位前輩的任何幫助和點撥。
我的文章的毛病現在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對問題的把握和認識問題。另一方面是文字問題。
在前者,由於我雖然早已拒絕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但是要真的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方法是一十分艱難的過程,對很多概念的重新把握要比從無知接受它困難的多。例如夏天的時候,您曾經對我說范岱年先生到丹麥研究實在論和唯物論的區別。我大吃一驚,沒有敢繼續問您,如果真是這個題目,是十分可笑的。對正常的學術界來說根本不存在這種問題。不瞭解這個區別怎麼進入學術研究,但是,這卻的確是我們的「導師們」要弄懂的問題。由於這種問題的存在,給愛因斯坦思想貼上唯物主義標籤,對西方學術界來說也是莫名其妙的。再例如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各種左派思潮、非理性思想,在九○年前我都不敢批評,只是覺得不對勁,九○年後開始逐漸看到,但是一摸到門,還沒有能夠更深刻地把握,就不得不寫文章涉及,因為除了仍然跟著共產黨文化走,否則,只要涉及根本性的問題,就必然涉及這些問題,迴避不了。
這也是最近我寫了一些雜文的原因,因為可以迴避一些嚴謹的討論,而繞道把問題先提出來。例如第四篇文章中的理想主義問題,兩種文化(極權主義文化)問題,第三篇文章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結構問題,從三十年代以來語言的蛻化問題。知道五分卻要把五分全寫出來,無法厚積薄發,怎麼可能把文章寫好!所以我常常有趕著鴨子硬上架的感覺。
這些問題本應該由老一輩人指導來做。但是,前輩們連提出這種問題的能力都沒有,只好由我們這些在共產黨的封閉社會中受到殘缺不全,甚至被扭曲的教育的人來做。我雖然做的不好,但是做了。總比你們的後代金觀濤要強。知恥近乎勇,前輩難道不應為此知恥嗎?
關於文字問題,我自己當然知道要不斷提高自己。這也是出國後我經常對別人說,思想進步了,文章乾淨了,但是中文的文字卻失去了進步的環境和可能。我請朋友給我郵寄一些古典散文來,希望能得到比《古文觀止》更多的古文文本。洗煉文字之間的聯繫和張力,是我要不斷努力的。但是我也知道,三四十歲的人中很少有人有我這種認識,並且省察自己的不足。無論誰能在文字上指出我的不足,我都是仔細思索,不會作為耳旁風。
每年過去,我都會回顧過去一年看自己有無進步。我雖然已經四十多歲,但是,我感到每年還在進步,這是我欣慰的。我相信,再過幾年,在思想上和文字上,我還能更上一層樓。
現在我要說的是,在背後向我射暗箭的是射不到我的。因為我已經不認同那個極權主義文化世界,我自己如何已經和那個共產黨知識界無關,問題是我自己究竟是怎樣。
六.究竟是誰不夠資格
要我翻譯幾篇給梁存秀先生看?這是一種故意刁難。就德語,就對德國哲學、文化背景的瞭解,就對科學和愛因斯坦的瞭解,翻譯愛因斯坦的文章,梁存秀先生有什麼資格對還學文和我審查。共產黨的哲學教授頭銜並不說明什麼問題,我們能不能合作,如果只是一方面的適應另一方面,我不會參加。
梁存秀先生這一代人用馬克思主義狹隘的教條框架把中國知識界引入了一個歧途。他們對德國哲學的理解和介紹完全和世界其它地區的不同。我想被梁存秀先生們派出國留學的學生一定會對此有所理解。他們在國內學到的那套方法,到國外來完全不能用,要重新來。他們每個人都會感到,並且痛恨共產黨的哲學教授們浪費掉他們的寶貴青春。
具備什麼樣的資格才能夠較為準確地重現愛因斯坦的文章呢?
首先,且不談梁存秀先生從馬克思主義主義教條對費希特謝林等德國哲學家的詮釋和批評的錯誤,但只就研究愛因斯坦來說,馬克思主義加上費希特謝林的哲學背景,只會離愛因斯坦越來越遠。二次大戰時,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經想請愛因斯坦為他想美國的大學寫一封推薦信,以使他能到美國去。但是愛因斯坦終究沒有給他寫,因為他的哲學傾向正是愛因斯坦最厭惡的。但是這裡我必須加一句解釋,雅斯貝爾斯應該說那一哲學傾向中最為簡潔清楚的。
其二,梁存秀先生對科學及其思想有什麼瞭解。愛因斯坦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事情。理性和科學啟蒙思想的發展,不僅是和馬克思主義,而且和梁存秀先生研究的德國思想是不同的兩條道路。以梁存秀先生那樣的思想框架和背景,只適合在極權國家內部搞馬克思主義宣傳,甚至都不能到任何非極權國家搞馬克思主義研究,更何談愛因斯坦研究、翻譯。
其三,愛因斯坦是反叛的,愛因斯坦喜愛音樂、文學,熱愛生活,具有豐富的人性。梁存秀先生這樣的極權文化的信徒,共產黨員,能理解愛因斯坦的愛、恨,愛因斯坦的人格嗎?愛因斯坦一生最痛恨的不正是梁存秀先生的這種思想傾向,這樣的人格嗎?梁存秀先生翻譯愛因斯坦,敢於把這一切翻譯出來嗎?
其四,愛因斯坦的母語是德語,文化背景是德國施瓦比地區的文化,但是愛因斯坦又痛恨某些典型的德國傳統。梁存秀先生知道愛因斯坦痛恨的是什麼嗎?比如說,愛因斯坦曾經說,他居然在受過十幾年的德國教育後,還能保持一點想像力,這是一個奇跡。梁存秀先生瞭解德國的教育制度,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發自肺腑地說出這句話嗎。愛因斯坦痛恨的正是梁存秀先生「研究」的那種費希特以來的德國的思辨傳統,梁存秀先生能理解這一切,把這一切如實地再現出來嗎?
急於去當祖師爺,不加分析地去排斥別人,這是共產黨文化的特色。其實在研究這些大科學家時,我們每個人都是學生。如真的全面研究玻爾,不懂丹麥文行嗎,不懂克爾凱戈爾及宗教哲學,不懂得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思想基礎近代經驗主義和唯理論(決非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所說的那樣)行嗎?!。而只就這三點談何容易。我雖然早就覺悟,一直在黑暗中靠自己摸索補課,並「有幸」(直到)四十歲時出國,然而,現在我在搞真正的研究時只能是誠惶誠恐。我唯一能做的只是指出,極權社會是一個荒謬的社會。我可以確切地說的只是,像梁存秀先生這樣的哲學教授,完全是在誤人子弟,我們可能要化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全清除這幾十年所造成的精神和知識障礙。
我要研究愛因斯坦也正是這一原因。梁存秀先生這樣哲學背景,這樣人格的人翻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地下有知,也會苦笑!而像還學文和我這樣的人,愛因斯坦只會鼓勵我們不要怕犯錯誤。
我對愛因斯坦的喜愛使我以後會繼續從事愛因斯坦研究。研究是個人的事情,參加翻譯一個東西竟然要由誰來批准,不過是那個社會對文化壟斷的結果。詩人多多兩周前在我這裡說,我們這些人的特點就是不怕共產黨。過去共產黨沒有壟斷住我,在海外洋人教授也沒有壟斷住我,現在雖然在中國仍然是由共產黨及依附於他們的幾個知識精英壟斷,但是我相信很快會改變。所以我沒必要屈服於中國的壟斷,參加這樣一個小組。這樣做,也免得這些餘年可數的老先生將自己寶貴的精力花費在這些問題上。我總是覺得,與其如此去弄得別彆扭扭,不如深夜捫心自問,反省自己的一生。至於我們,只要有精力,肯定不會放棄對愛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紹的。
此致!
維光
1996,2,11(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