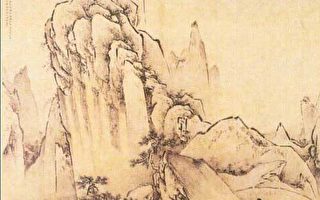【大紀元8月5日訊】“密友資本主義”背景下的社會衝突:當今中國的貧困和暴力
一、“密友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兩極分化及其政治後果
二、制度型貧富差別的非正義性及其成因
三、對貧困者的結構性暴力和貧困者的暴力
四、通過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來化解社會衝突
********************
四、通過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來化解社會衝突
無論是在一國範圍內,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以消除貧困爲正義目標的經濟發展才能成爲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也只有這樣的經濟發展才能營造社會的融洽和長遠安定。任何有道義價值的經濟發展都不允許以産生和擴大貧困爲其代價。正如《聯合國發展計劃》所說的那樣:“爲了增強人的安全,需要一種新型的發展,需要把人放在發展的中心位置,把經濟增長當作手段而非目的,需要保護這代人和後代的生命機會,尊重所有生命都賴以存在的自然世界”,“說到底,可持續的人類發展是爲個人、爲工作和爲自然的。它的最首要任務是減少貧困,增加生産性就業,增進社會融洽和改善環境。”總之,可持續的人類發展是爲了讓所有的人都“變得更有力量”,更能有效地“參與到他們生活的過程和事件中去”[15]。可持續的發展必須是一種同時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在內的新型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公正合理的經濟分配與自由平等的社會、政治參與相輔相成。二者皆缺的社會雖不一定立即就會發生動亂,但二者皆備的社會卻一定能夠長治久安。
在中國,雖然憲政民主對絕大多數國民來說仍然十分陌生,但貧困者對富人的仇恨和暴力卻早已構成了社會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遠的如梁山泊好漢劫富濟貧,近的如打土豪分田地或者造反鬧革命。這種暴力有許多非理性因素,它可以用來反抗官商勾結和權勢者欺壓百姓,但也可以用來集體懲罰普通的有産者,更可以被用作隨意占取他人財物的藉口。如果我們把反對一切暴力當作一種基本的社會正義和民主價值,那麽我們就應當既反對造成貧困的結構暴力和文化暴力,也反對任何以貧者反抗爲名的個人暴力。即使貧困者的暴力找准了它的仇恨物件,它仍然不能代表所謂的“報復的正義”。
真正的正義只能産生於公共政治,因爲正義是一種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決。個人的暴力行爲畢竟不能主導一個社會的公共政治。在民主社會中,只有法律才能申張正義,也才具有正義權威。在非民主的社會中,貧困者運用暴力,並不是因爲不懂或不想通過法律來申張正義,而是因爲現有的法律並不申張他們心中的正義。貧困者的鋌而走險,與其說是他們對法制無知,還不如說是社會公共政治失敗的結果。個人暴力的流行往往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提醒我們:公共政治消失之日,必然就是各種暴力開始之時。從邏輯上看,個人的暴力行爲不是公共政治失敗的原因,而是公共政治失敗的産物。
公共政治的根本特徵是說理,而暴力的根本特徵則是沈默。阿倫特曾指出,在言論說理的公共政治中,人們彼此以明理之人相待;相反,在單憑強制的暴力中,人們彼此視對方爲武力壓制的物件。因此,“暴力只是政治領域的邊緣現象,……由於戰爭和革命都以暴力爲主,它們都是嚴格意義政治領域之外的行爲[16]。”同樣,任何暴力型“申張正義”也都是嚴格意義的公共政治領域之外的行爲,都不值得贊許和提倡。
沒有公民文化作爲堅實基礎的民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政治,它必然會淪落爲民粹政治或者群氓政治。蔡美兒在一些動亂地區觀察到的正是這種民粹民主。從民粹政治或者群氓政治的危害來看,在貧富懸殊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制度,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甚至誘發社會衝突。依據這種看法,似乎中國就應該慶倖過去25年來實行了拒絕政治民主化的經濟市場化;沿著這一邏輯進一步推論,甚至可得出政治專制對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更有利的結論。中國官方關於這一問題的說法其實就是這種邏輯。然而,把自由市場和政治民主分割開來,試圖以取消或拖延民主來應付自由市場帶來的巨大貧富差別、糜散性結構腐敗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多數人的憤懣不平,這樣的策略真的能使中國躲過一場社會衝突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先得瞭解什麽是民主。“民主”並不是什麽一成不變的概念,在不同情況下,民主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實質意義。民主可以是一種自發或奉旨的民粹式民主(如“文革”中的“大民主”),體現的是多數人的暴政。這種民主極易淪落爲無政府主義和受個別人蠱惑操縱的政治專制。民主也可以是一種既體現多數人意志又保護少數人權利的民主憲政秩序,它旨在保障不同階級和利益群體的和平共處;其合法性來自憲政法制,而不是直接來自多數人的意志;它貫徹理性協商的原則,擯棄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以民主名義施行的暴力。用後一種民主的標準來看,無論是造成貧困的經濟暴力,還是報復經濟暴力的民粹式或個人暴力,或者甚至以維持穩定爲名義所施行的國家暴力,都是應當譴責的暴力形式。後一種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在當今的中國,國家政治權力所取消或拖延的恰恰正是這樣一種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必須建立在公民政治的基礎之上的。畏懼公民政治的政權必定仇視真正的民主,但卻能容忍和利用市場。但問題是,沒有公民政治的限制和規範,市場則必然成爲腐敗的滋生之地,而公民政治民主拖延得越久,民粹民主也就越有可乘之機。現代公民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倫理規範之所以代表社會正義,是因爲這種倫理規範來自公共群體本身。這和前現代社會群體道德規範主要來自宗教、行會、合作夥伴或熟人顧客關係等等是不同的。現代社會的公共倫理規範不是一套一成不變的道德原則,而是一個形成價值共識的機制和過程。社會正義的“社會”不只是指一個人群,而更是指一個維護價值共識的輿論人際關係,也就是公民社會。
比較健全的市場和民主都是存在于相對發達的公民社會之中的。蔡美兒所說的那種“密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票箱民主之所以不健全,乃是因爲它們沒有好的公民社會基礎。市場和民主都必須有所限制,這種限制只能來自公民的共同有效參與和體現這種參與結果的政府法令和政策措施。在公民社會中,放任式自由市場必須接受有效的財富再分配、社會福利保障、公共資源政策、透明資訊和競爭程式的限制。多數人意志民主則必須接受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法制秩序、公正程式和憲法絕對權威的限制。當市場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作爲一種應付執政合法性危機的措施匆匆引入後“文革”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經遭受過了“文革”時期的致命摧殘。由於市場和民主被強行隔離,市場被當作一條與公民群體的共好價值觀全然無關的發財致富之路,公民社會建設問題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只有在加強公民社會,健全公民政治的前提下,才能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民主體制運作(如實施民主憲法、透明立法、獨立司法、限制官員權力、自由輿論的監督、自由言論和自由結社下的公民參與等)來有效地避免暴力的激化,消除暴力的危害。中國要長治久安,要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防止突發的暴力衝突,就必須實行這樣的民主。唯有如此,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注釋】
[1] Amy Chua,World on Fire: How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p.263.
[2] 斯蒂格裏茲曾在克林頓政府任職,也在世界銀行擔任過重要職務,他是原教旨自由市場論的強烈批評者。
[3] 轉引自Greg Grandin, “What’s a Neoliberal to Do?”Nation, March 10, 2003, v276, i9, p.25.
[4] Amy Chua, pp. 6-7.
[5] Amy Chua, p. 147.
[6] 劉海英、楊靜,“十年不變:市場經濟、精英聯盟、權威政治-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訪談錄”,http://www.cc.org.cn/newscc/browwenzhang.php (2004/2/13)。
[7] 馬修,“中國已進入恐怖時代”,http://www.cc.org.cn/luntan/China (2004/2/7)。
[8] Steve Lee, “Poverty and Violence,”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22, No.1 (Spring 1991): 67-81, p.69.
[9] Amy Chua, pp. 4-5.
[10] 2003年1月22日,山西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海倉在其辦公室裏被槍殺;緊接著第二天,南方的福建輪船總公司總經理劉啓閩被員工連刺四刀身亡;半個月後,北京的富豪周祖豹返鄉過年,在自家門口遭歹徒連刺14刀,當場死亡。8月,蘭州富豪劉恩謙意外地遭槍殺;9月,10億富豪喬金嶺莫名地自殺。
[11] 蜀帖龍,“‘雙搶’分子應向李小平學習”,http://www.wforum.com/wef/posts/58916.shtml(2004/1/31)。
[12] Johan Galtung, “Peace Problem: Some Case Studies,”Essays in Peace Research, Vol. V (Copenhagen: Christian Ejlers, 1980), p.407;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 No.3 (1990), pp. 291-2.
[13] 出處同上。
[14] James C. Scott,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社會斷裂”,http://www.lctz.com (2004/2/29)。
[1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4.
[16]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1977, c1965), p. 19.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