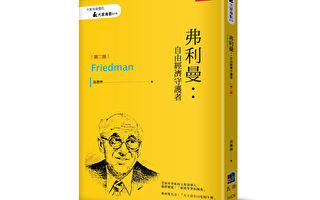【大紀元2025年01月21日訊】
一、東歐移民家庭
1911年1月17日,喬治·史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 1911~1991)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郊區小鎮欒棟(Renton)出生,是家中獨子,一直到二十歲大學畢業,都住在西雅圖,之後才動身到美國東部念研究所。史蒂格勒的父親喬瑟夫(Joseph)在二十世紀初就從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移居到美國,在美國認識了伊莉莎白·杭格勒(Elizabeth Hungler),兩人結了婚並生下了史蒂格勒。伊莉莎白在十多歲時就由匈牙利(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移居到美國,夫妻倆的家族都是務農的。
在禁止私自釀酒的法律出現之前,史蒂格勒的父親喬瑟夫曾以釀酒維生,但禁止私釀酒法令出現後,就嘗試做過多種工作。喬瑟夫是個強壯者,曾當過一段時間的碼頭裝卸工。史蒂格勒回憶說,他的母親會哭著送攜帶短棍的喬瑟夫去參加碼頭裝卸工人工會的聚會。不久之後,喬瑟夫轉進房地產市場,因為那時正值經濟大恐慌,西雅圖也遭到重創,造船廠被迫關閉,而波音飛機製造廠的規模仍小。喬瑟夫和伊莉莎白是以買下破落的房子,再重新整修並予以出售謀生。在史蒂格勒十六歲之前,已在西雅圖十六個不同的地方住過,但他的家庭在遷移當中仍維持著舒適,而且喬瑟夫也吸收到房地產的豐富知識。
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移入者通常是從低工資的工作做起;他們可能年紀輕且不具有任何職業所需的技能﹐史蒂格勒的母親就是如此,或者根本不會說英語,史蒂格勒的父母剛到美國時就是這樣。不過,移民者是具有活力、身體健康者,而且富有冒險精神。以史蒂格勒的母親伊莉莎白來說,一個只有十八歲的女孩子,隻身到美國,又不懂當地語言,要自己養活自己,這是多麼大的挑戰?還好的是,伊莉莎白是落腳在一個只講德語的社區。
研究發現,經過一、二十年後,從歐洲移到美國者,會比同年紀、同教育水準和相同資歷的在地美國人,賺更多的錢,喬瑟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史蒂格勒本身也是種族熔爐的典型產物。他在三歲以前只會說德語,但在跟不同背景的小孩玩在一起之後,就拒絕再講德語,直到上大學修習德文之前,對德文可說一竅不通,而其父親到後來,在德語中夾雜的英文字詞比重愈來愈大,相對地,講英語時夾雜的德文字詞比重愈來愈少。
史蒂格勒覺得他和其他移民者的子女有著一項差異,那就是他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利用時間。直到十二歲進初中之前,他的父母親都工作得很辛苦,而且都工作得很晚,根本無暇管他;即使上了初中,史蒂格勒也大都和自己所拼裝的東西相處,例如他和朋友們會從湖底拖出一艘棄置的小舟,將舟底塗上焦油,之後就在湖面划著玩,而那個時候他們還都不會游泳呢!史蒂格勒曾參加第四十四隊童子軍,那是一個極富冒險心的童子軍團隊。該團獲得許可,在當時隸屬海軍的一個狹小航空基地「沙點」(Sand Point)的一處森林區建造一座小木屋。
在1920年代中期,飛行是不拘形式的。史蒂格勒的童軍團和那裏的飛行員玩「膽小鬼」(chicken)的遊戲。他們會從華盛頓湖上的木筏下來游泳,那些飛行員就駕駛飛機掠過木筏,逼嚇他們跳下木筏,結果是飛行員贏了。當沙點基地擴張時,史蒂格勒他們的童子軍營地就被收回,但他們很快找到新家。1928年,巨北鐵路完成了北美最長的隧道,在泰鎮(Tye)的舊隧道就被棄置,童軍團要求巨北鐵路把泰鎮送給他們,對方竟然答應了。
泰鎮曾經叫做威靈頓(Wellington),1910年發生一場雪崩,停在威靈頓的一輛火車掉到山谷下,造成96人死亡。巨北鐵路後來就加建了擋雪板,但人們仍可在白天的山谷裡看到該場意外事故留下的扭曲鋼鐵。在史蒂格勒的童軍團擁有泰鎮之前,該鎮曾遭焚毀,但他們卻是得到一個完好的火車站。相對於沙點,泰鎮的交通並不便利,搭街上的電車就幾乎可到沙點,但泰鎮距西雅圖五十英哩。不過,史蒂格勒和朋友們在數年間仍相當規律地利用泰鎮,那時史蒂格勒擔任的是童軍團助理團長,是協助而非聽命於團長。每到夏天,童軍團都會攀爬奧林匹克山(Olympic Mountains),再進入凱斯凱山(Cascade Mountains)到東部。在那四、五天的遠足結束時,史蒂格勒通常都疲倦而腳痛,且全身溼淋淋的,並對所吃的食物非常厭煩。因此,每次史蒂格勒都會發誓那是最後一次,但來年夏天一到,他們又會再上山。
由這些活動可知,史蒂格勒在暑假是不工作的,只偶爾打打小零工。當他十六歲左右時,曾到威納奇山谷(Wenatchee Valley)從事梳弄蘋果樹的工作。蘋果是整叢生長的,必須適當地予以稀疏,才可使每粒蘋果順利生長。史蒂格勒的工資是每小時四角、供膳宿。他工作了三個禮拜,是他一生中唯一用體力賺錢的經驗。史蒂格勒的一生從來沒遊手好閒,在十多歲時,一半時日的暑假都在打網球,終其一生,史蒂格勒都是自己油漆房子,而且做一些手工製品。不過這些藍領工作生涯是很短的。
史蒂格勒舉他父親為例,證明巴伐利亞人非常不同於典型的普魯士人,非常地個人主義,而且完全不排斥冒險。1932年,美國的政治生態起了大變動,長期以來屬於共和黨重要據點之一的華盛頓州,就處在政治風暴中心。民選的州政府職位中,只有教育督察沒有民主黨候選人,史蒂格勒的父親想要登記參選。但在史蒂格勒的勸阻下放棄了,而競選連任的教育督察,是在那次州政府職位選舉時,民主黨大勝中唯一獲勝的共和黨員。
事後回想,史蒂格勒認為其勸阻父親參選是對的。雖然其父是個聰明人,但對政治、官僚體系和教育行政卻一竅不通。是有很多成功的商人進入政府擔任全國性的行政職位,但大部分人在政治界都沒成功。他們被消息靈通和自我保護的部屬環繞和控制,必須和冷酷需索的立法議員周旋,而且他們所任職的單位必須改變的部分幾乎都動不得,而教育行政人員通常還有偽裝虔誠的需要。史蒂格勒慶幸他的父親沒去當官,否則他往後就得採取支持官員的立場,也就無法有往後的成就了。
多年之後,史蒂格勒的父親參加了西雅圖市民代表委員會的選舉,約三十位候選人角逐數個席位。他的競選費用僅2.75美元,用來印製一些宣布參選的卡片,由於他的德文名字,獲得數千張選票,但落選了。
二、求學生涯點滴
在進入華盛頓大學之前,史蒂格勒對書籍是貪得無厭而不加以選擇的,也是個沒什麼規劃的學生。他在華盛頓大學的成績相當優異,大都是企業管理的課程,本來是想用來做事業生涯準備。但1931年大學畢業時,企管方面的工作不太好找,於是史蒂格勒接受了西北大學的免服務獎學金,一年之後就獲得碩士學位。
當史蒂格勒離開西雅圖到芝加哥西北大學就學時,並沒有考慮到要發展學術生涯,當時的史蒂格勒對他的生涯沒有什麼概念。他的父母都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的大學修習課程都是自己選擇的,而且都沒受到家庭文化的影響,不像他自己的兒子就不可避免地沉浸於他所受的教育中。就因為沒有這種影響,史蒂格勒才讀了許多愚蠢的書,也修習了太多類似房地產原理的「實用」課程,並且沒有去修數學。
在西北大學那一年,史蒂格勒遇到一個對他影響很大的老師伍德貝瑞(Coleman Woodbury),是頭一個激發他對學術生涯感興趣的人。漸漸地,經濟學使史蒂格勒覺得是他值得全力去研究的一門智識學問,而非作為企業經營的導讀工具而已。當史蒂格勒從西北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又回華盛頓大學念了一年,這時的史蒂格勒,其興趣和目標的轉移已很明顯,於是他又收拾行囊往東部走,再也不回西雅圖了。這次往東的目的地是芝加哥大學,而那時的史蒂格勒並不知道芝加哥大學是經濟學界的主流。
史蒂格勒之所以會選擇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完全是他在華盛頓大學的老師告訴他的,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老師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和范納(Jacob Viner, 1892~1970)都是優秀的經濟學家。史蒂格勒也認為芝大將會比哥倫比亞大學或哈佛大學給予個別學生更多的關注,哥倫比亞大學只寄一本印刷的小冊子給申請入學者,裡邊與申請者有關的段落打了勾,譬如「我們將在五月十五日以前,必須收到你的成績單」以及「你必須在六月十五日以前寄來二十五美元」。史蒂格勒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了十一年的教授,對於該校經濟學系一貫的高品質深感尊崇和喜愛,但在1933年時,該單位卻顯示出人際關係淡泊且不太有人性化。哈佛大學是由經濟學系系主任的秘書寄了一封回應申請人的入學申請,而芝大則是由經濟學系系主任米立斯(Harry Millis, 1873~1948)親自回信給申請人。史蒂格勒就由人際關注這個面向,選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就讀博士班。
1933至1936年三年間,史蒂格勒在芝大就學,確實發現芝大經濟學系提供了一種熱烈的智識生活。影響史蒂格勒最深的老師是奈特,他時常不客氣地批評學者和體制,對於所有權威都抱持懷疑態度,這也顯示出奈特的智識精力。有時奈特會無法閱讀他手中拿著的重要書本,因為書中寫滿了他的看法,即使是兩行字之間的空白處也是一樣,於是原書文字就難以辨識。那時的奈特已從經濟學轉入哲學和宗教的研究,在宗教上表現得有如學識淵博的不可知論者。經濟學裡有一個著名的虛擬人物「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是個完全理性的人,能準確計算每項行動的成本和利益(或效益),並採行利益大於成本的行動。奈特曾經在芝大神學院的一次演講說:「經濟人和完美的基督徒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會有朋友。」
史蒂格勒將奈特比喻為摩西(Moses),奈特會在教室裡批評該週《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的新且荒謬的錯誤,而有經驗的學生會帶著不懷好意的神情,看著新來的學生想努力地記下極無秩序的筆記。史蒂格勒說他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上課中,奈特告訴他們,如果不懂得即將討論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地租理論,那就可以別唸經濟學了。但在十五分鐘過後,奈特卻說他自己直到兩年前才了解那個理論。有時候,奈特會出現在其他老師的課堂上,提出某些大家公認是沒有意義的爭論。
史蒂格勒認為奈特是一個值得敬愛、不屈不撓、不可思議的人。奈特對學生的重大影響力並非靠怪癖和魅力,而是他追求知識的專注。奈特表現出毫無保留地崇尚「真理」的態度,其崇尚的程度鮮有人能及。追求真理是危險或痛苦的,但又是必要的。沒有一個權威會因為太威嚴而不能加以挑戰,沒有一個當代的學者會因為太有影響力而免於批判性的檢視,而且通常會被公開抨擊。權宜性的妥協根本不在奈特的思維之內,因此,若問他屬於哪個政黨,是很荒謬的問題,因為兩大政黨均未絲毫擁有他。不過,奈特支持朋友和門生時,卻是毫無保留的。
奈特執意支持賽蒙斯
當時的芝加哥大學,有兩大著名經濟學家在爭吵,一位是奈特,他出身自伊利諾州貧家且子女眾多的農家,性格頗為奇特。由於家境清寒,奈特經歷奇異的教育過程後,到30歲才從康乃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後在愛荷華大學待了將近十年,才在1927年來到芝加哥大學任教。當時他已因一本探討經濟學理論的名著《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s, 1921),以及一些相當具煽動性的哲學論文(集結於《競爭的倫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1935)這本書中)而聲名大噪。奈特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高度獨立思考的人,他懷疑很多經濟理論的正確性,也懷疑對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所有公開討論之完整性品質。
另一位當事人是道格拉斯(Paul Douglas, 1892~1976),他和奈特的出身類似,也是在貧窮環境中長大,而且還有個破碎的家庭。道格拉斯和奈特各以不同的方式,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奈特是心思細膩的理論家,不斷深入探討經濟分析和社會哲理;道格拉斯則是想像力豐富的實證工作者,而且是個積極而快樂的自由派改革者。在其自傳《豐盛的年代》(In the Fullness of Time, 1972)中,他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只是一筆帶過,而在參議院的十八年是他人生的巔峰期。在他很不情願地離開參議院後,史蒂格勒邀請他到芝大演講。當人們告訴他氣色很好、精神飽滿時,他回答說他寧願是個疲累的參議員。
奈特和道格拉斯這兩個人性格南轅北轍,一個是胸懷開闊的自由主義者,一個是在知識上反對崇拜偶像主義者,只因同在一個小系裡(只約十位教授),才勉強使兩人湊在一起。奈特在1927年到芝大後的最初幾年,與道格拉斯的接觸只是斷斷續續,因為道格拉斯在1930年暫離芝大六個月,到史瓦斯摩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研究失業方面的問題,不久之後又參與多個公共委員會。不過,這兩人的對立還是形成了,而最後主要的是以書信往返交鋒。
在史蒂格勒1933年進入芝大就讀之前,奈特和道格拉斯早就爭論不休,兩人關係冷淡,很少有同學同時修他們兩人的課。1934年秋,由於賽蒙斯(Henry Simons, 1899~1946)面臨拿不拿得到永久教職的事情,兩個人槓上了。賽蒙斯是奈特的愛徒,隨著奈特由愛荷華大學來到芝大任教。道格拉斯反對給賽蒙斯永久教職,甚至反對繼續聘任,因為賽蒙斯只寫了《自由放任的實是計畫》(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這本好書,沒有其他的作品,而且又是不太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奈特極力袒護賽蒙斯,甚至以相當感情化的字眼為其辯護,他是這樣說的:「說到感覺,我必須承認我的弱點。我不認為我能夠以抽象的優點和弱點的冷靜語氣來談論此事。我『覺得』排斥賽蒙斯就等於在排斥我。如果他真的被排擠掉,我就會在道德和感情上對這個團體『絕望』。但這絕不是衝著任何人而來,只是事情的本質確是如此。當然,這種感覺和我體認自己在這情境下乃屬多餘有關。在我擅長的領域中,我們不是站得很穩,而特別是我在其他方面又不是很有分量。此外,就『品質』來說,如果這些人不屬於這個團體,那我也不屬於此。」
這個爭議事件最後以所羅門王式的聰明,很有技巧地解決:留用賽蒙斯,但讓另一位奈特的門生捲舖蓋走路。
史蒂格勒在其1988年出版的自傳中評論此事件,說:「奈特是我論文的指導教授,終其一生都對我很好。可是,讀到這些信件,發現他以自己的飯碗和尊嚴力保賽蒙斯,心感悲痛。這是不能常用的險招,否則會使系上很難做決定。當然,教授們還是會強力『促銷』他們的指導學生,但正確的態度對成熟的學門是重要、甚至可說是關鍵的一環。」
史蒂格勒同意道格拉斯所指稱的,賽蒙斯的資格在1935年時是不符合要求的。不過,賽蒙斯從那時起就開始寫論文,在他後來僅活的十年中,發表了許多關於貨幣政策、公會,以及反托拉斯政策的重要文獻,以及一本討論個人所得稅的必讀書籍。這位英年早逝的賽蒙斯,之後在芝大法律學院開始教經濟學時,又為法律教育開創了一個重大的發展方向,也在法律學院先拿到永久教職,後來才獲經濟學系的永久教職。
這個事件顯示奈特比道格拉斯對於賽蒙斯的前景看得更清楚,也顯示奈特慧眼識英雄,並對其得意的門生之支持是毫無保留的。
道格拉斯在1939年當選芝加哥市議員,離開了學術界,不久之後進入海軍陸戰隊任職,爾後又成為美國參議院參議員。
早年芝加哥大學的重要人物
奈特無疑是早年芝加哥大學的最主要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可證明其對知識的專注。奈特不當人家的顧問,不論是大小人物或企業,也不論是公開或私下。奈特也不到處演講,他沒在廣受歡迎的傳播媒體尋找立足點。奈特的行事風格顯現出「追求學術知識,是值得第一流的心靈、全心全力投入的事業生涯」。即使是在奈特給予學生這種好印象的那個年代,該種行為在經濟學界都不常見,而史蒂格勒認為,該種學者風範是偉大教師的主要修養。奈特的學者風範衍生出「不斷地懷疑權威」,他只服從道理,絕不向權威低頭,形成一種「反權威」的特殊形式:奈特跟學生相處完全沒有一絲優越感。他在聆聽任一學生的建言時,與聆聽著名學者的建言都一樣的認真。史蒂格勒感嘆道:「他那麼專心地注意聽我們不夠深入的觀點,有時候真讓我們備感尷尬!」
史蒂格勒在奈特的指導下,完成了「關於十九世紀末尾三分之一年代的經濟理論的歷史」博士論文。史蒂格勒感到很納悶的是,奈特對學生那麼好且幫助大,為什麼找他指導的學生卻是那麼的少。就史蒂格勒記憶所及,他是奈特在芝大那些年指導過的三、四位學生之一。在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瓊斯(Homer Jones, 1906~1986)、瓦利斯(Allen Wallis, 1912~1998)、羅賓斯(Lionel Robbins, 1898~1984),以及史蒂格勒合力下,在1935年奈特五十歲生日時,將奈特的極佳論文集結出版,那就是《競爭的倫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這一本書。
芝大第二位重要人物──范納
奈特是當時芝大第一號人物,范納(Jacob Viner)則是第二位重要人物。他是國際貿易專才的第一把交椅,對於經濟史更有驚人的學問。有這樣一則流傳的故事:一位年輕學者急促地跑去找范納,說:「我剛發現美國第一位數理學家!」范納回說:「你是指伊雷(Charles Ellet, 1810~1862)?」這位學者驚道:「你怎麼知道?」范納說:「他是唯一沒被發現的美國早期數理經濟學家。」
這則故事顯示出范納的豐富經濟史學識。范納在課堂上是個相當嚴厲執行紀律的老師,他的身教和言教,形塑出芝大小心運用價格理論的傳統。1934年時,范納在他著名的經濟理論課程「經濟學301」剛開始教課時,詢問一位同學:「哪些因素決定產品的需求彈性?」那位學生先回答說:「要視替代品多寡而定。」隨後又補充說:「以及供給情況」。范納臉色一沉說:「X先生,你可以不用上這門課了。」
史蒂格勒當時也修這門課,霎時和大部分同學的脊椎都感到刺痛。之後,史蒂格勒又修了范納的國際貿易理論課,范納強迫學生們要打分數。這是史蒂格勒在芝大修過的課中唯一有分數的課,通常選課的學生是拿”R”而不打分數。數年之後,史蒂格勒才體認到范納偉大情操的一部份。范納的武斷遠不如奈特或賽蒙斯,而且認為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和效果都在於那時或現在的知識不足,因而公共政策的唯一作用只是增進知識。范納對智識歷史的研究很廣泛,比奈特還有過之。奈特闖出名號的文章是研究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理論,該文列出七項李嘉圖作品的缺失,而范納分析李嘉圖時則是融入感知與同情。因此,讀范納的文章可以「聽到」李嘉圖的聲音。
上文提到的賽蒙斯是芝大的另一位名家,他是公眾和大多數經濟學家公認的芝加哥學派核心理論大師。他致力於鼓吹「以私有(競爭的)市場來主導財貨的生產和消費」,而「政府只扮演有限的經濟性功能」。他在1934年出版的《自由放任的一項實是規劃》讓許多人著迷,因其文筆犀利而且有許多大膽的新經濟政策建議。該書是在現代最蕭條時期的谷底時寫出的,傳達了賽蒙斯的一項理念:西方社會正接近無法回頭的關鍵時刻。
史蒂格勒自認對賽蒙斯的了解程度勝過對奈特和范納,他還將賽蒙斯介紹給包爾小姐(Marjorie Powell),兩人最終修成正果,結為夫妻。史蒂格勒也和內夫(John V. Neff)這位經濟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交往,但和經濟計量學家休茲(Henry Schultz, 1893~1938)和道格拉斯這兩位著名的教授則較少接觸。
教授間爭論不休
史蒂格勒在芝大求學的當時,教授之間激烈的爭論,顯示芝大經濟學系沒有主導性的思想學派。范納和奈特兩人一直在爭論的是:生產財貨和服務的成本到底是心理上的成本(像是令人厭煩的勞動),或者只是不將這些資源用於別處所損失的利益(如休閒的快樂)。
史蒂格勒說他無法理解,為何兩個那麼傑出的人會持續在字詞上進行激烈爭論。他倆利用學生傳達爭論的內容,使爭論從一個教室蔓延到另一個教室。據說有位參加博士學科考「經濟理論」的學生,在回答某個問題時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奈特教授請閱此;第二部分:范納教授請閱此。」據說芝大沒有鼓勵這位學生繼續唸下去。賽蒙斯雖是奈特的愛徒,但兩人也會為相左的見解爭論得不可開交。
史蒂格勒的傑出同學們
在芝大求學時,史蒂格勒遇到多位傑出的同學,他形容說有如教授群那樣重要的同學。第一位是瓦列斯(W. Allen Wallis, 1912~1998),他和史蒂格勒同一年來到芝大,兩人從此開始了一輩子的友誼。他們挪用了一間空的研究室,搬來一些桌椅,並對每位老師的表現進行嚴格的檢視。研究室張貼著一些標語,其中一張標語是這樣寫著:「數學裡沒有表達混淆概念的符號」。那是一句荒謬的句子。瓦列斯有著批判性、探索性心靈,很明顯和史蒂格勒相同。瓦列斯在1962到1970年擔任羅徹斯特大學(Univ. of Rochester)校長,也當過美國經濟部次長。1958年時,瓦列斯協助史蒂格勒回到芝大當教授。
第二位是弗利曼,他早就在1932年到芝大求學,當時已經是一個可敬畏的智識人物。弗利曼不只可以非常嚴謹地、富有創意的思考,而且過程非常快速。多年之後,曾是弗利曼學生的凱塞爾(Reuben A. Kessel, 1923~1975)告訴史蒂格勒,有一段長時間每當他拿問題去請教弗利曼,總是搞不懂弗利曼的回答,因為弗利曼與他的討論很快就跳到其他課題,弗利曼已快速地進入那個問題之分析,而且進到更多層次的探討了。史蒂格勒提到可以顯示弗利曼早熟的事件,當弗利曼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研究生時,曾因感冒臥病兩天,但當他返校上課時,已經寫好了一篇新論文。該篇論文指出,世上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對於應用家庭收支資料估計需求彈性所建設的方法之錯誤所在,但庇古並未看到該篇登在《經濟學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論文,因而也未承認錯誤。由於此一事件,史蒂格勒也就時常揶揄弗利曼,說如果他在滑雪時跌斷腿,一定會有新的作品出現。
第三位是包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他是從英國來到芝大的,拿的是大英國協研究員(Commonwealth Fellow)獎學金,既聰明又勇敢,敢於跟奈特爭論資本的本質。
第四位是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 1915~2009,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當時選修經濟學研究所的課程,他曾說是瓦列斯和史蒂格勒勸說他去修高等數學,使他成為數理經濟學家。不過,史蒂格勒並不認為有這麼回事。
芝大經濟學系的學習活動
當時芝大經濟學系的學生們和資淺教授,規劃了一系列的學術研討會,而且邀請一群客座教授(包括藍格(Oskar Lange, 1904~1965)、瑪哈祿普(Fritz Machlup, 1902~1983)等人)演講,帶動了很棒的討論。但當系主任問學生們是否想將研討會列為一個課程時,卻被拒絕了,因為他們擔心教授們會對運作有意見。這也顯示芝大年輕研究生的自信、傲慢、頑皮,而史蒂格勒是其中佼佼者。
有這麼一段小插曲可證明。萊特(Chester Wright, 1879~1966)教美國經濟史,上課時間是下午四點到六點,在五點休息時有十分鐘喝所謂的「社會科學茶」時間。雖然這堂課的內容還不錯,但萊特的上課方式不夠吸引人,所以史蒂德勒往往只上半堂。有一天萊特宣布說,有人寫了一張匿名便條,警告他不要超過六點才下課。課堂中所有的學生都轉頭看史蒂格勒,就是都認為是他寫的。這讓史蒂格勒很懊惱的想:「為何我沒寫那張便條!」萊特老師其實是很溫和的,在史蒂格勒後來考經濟史的學科考試時,還特地出了一題有關美國太平洋岸西北部的經濟發展問題,那是史蒂格勒的家鄉,應對史蒂格勒有利,可惜的是史蒂格勒不會這一題。
史蒂格勒認為,一個人在學校或大學所獲得的知識,至少有一半是跟同學學習的,畢竟同學們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間無所顧忌的交流、論辯,而師生之間就不可能如此。不過,學校若能聘請到眾多好的教授,是能夠吸引好學生就讀的,芝加哥大學就是個好例子。
芝大對史蒂格勒的影響非常大,他學到重要的一課是:對於公認的信仰和權威的聲望予以質疑。他確信:廣為人接受的概念,很少有支持其正當性的證據。不過,史蒂格勒認為,芝大未能讓學生往應用統計資料估計經濟關係,以及檢定經濟理論,是一大遺憾。因為這一門成為往後的一股熱潮。其實,當時芝大有兩位老師在鼓吹這種潮流,一位是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另一位是休茲(Henry Schultz)。
道格拉斯是勞動市場統計研究的先驅者,更重要的是,開啟了生產理論的統計研究,亦即研究生產商品或服務的過程或數量時,勞動和資本使用量之間的關係。
休茲開了一門數理經濟學的課,課名是「相關和曲線配置」(Correlation and Curve Fitting),是個很愛引經據典的學者。休茲雖無太多自己的深入創見,卻有刻苦耐勞、窮追本源的特質,精研的是個很狹隘領域,那是統計上的需求曲線,多年來都在撰寫其畢生巨著《需求的理論和測量》(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他聘請當時就讀研究所一年級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助理,幫助他從事此工作。弗利曼雖然認為休茲的學術才智有限,對純粹分析不專長,但不偏不倚追求真理,堅持在一個狹窄的範疇內深耕的態度,使休茲在經濟學上的貢獻遠勝於其他更能幹,但治學較不嚴謹較不心胸寬闊的學者。不幸的是,休茲在他的專書出版前,開車載著妻子和兩個女兒赴加州度假,車子在公路上墜崖,全家喪生,年僅四十五歲。
史蒂格勒日後覺得當年忽略現今稱作「計量經濟學」的內容,是自己造成的錯誤。他從未修道格拉斯的課,因為道格拉斯和史蒂格勒的指導教授奈特不和。而史蒂格勒對休茲的教學方式則不感興趣,因而錯過修習計量經濟學。不過,日後史蒂格勒卻以「實證研究」得到尊崇,這是管制經濟學中檢視政府的管制政策主要成分,需要應用計量技巧,而且只要中等程度的技巧就夠了。如果當初史蒂格勒能上休茲的課,就不需要大費周章向弗利曼、瓦列斯、伯恩斯(Arthur F. Burns, 1904~1987)、費布利肯(Solomon Fabricant, 1906~1989)和摩爾(Geoffrey H. Moore, 1914~2000)等同窗好友以及老闆學習了。
在芝大求學時,史蒂格勒對歷史深感興趣,由他的博士論文是探討經濟理論的歷史,就可得到印證。其實,終其一生,史蒂格勒對歷史都抱持著濃烈的興趣,即便經濟史在學術界早就不受重視,甚至已被邊緣化了。不過,史蒂格勒對自己選走經濟史這條路,還是耿耿於懷,自覺當初沒預測到四十年後的經濟研究之方向,也就是數理化和計量經濟的走紅,他對自己當年求學時沒選讀計量經濟,以致在數學和統計技巧方面沒能得到很好的訓練深感遺憾,尤其因為對數理化不夠專精而錯過1946年被聘為芝加哥大學教授,最關鍵的因素就在於此,更讓他至死都無法釋懷。
史蒂格勒對大學學費的明顯改變有深刻感受。當他在1933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每年的學費是三百美元,相當於1988年的兩千八百美元,非常便宜,而兩個時代的生活水準差異也很大。他舉實例說,1930年代的學生都沒汽車,而十年後,弗利曼曾因為主動提議要載幾個學生去西北大學參加一場學術研討會遭到拒絕,而吃了一驚。那些學生每個人都說要自行開車去。史蒂格勒回憶說,那個時候的獎學金也很少,而他是在研究所裡打零工賺取學費的。不過,他覺得不同時代的本質並沒改變,也就是說,研究生就好像生活在一個緊密結合的小型社會,整天都沉浸在經濟學中,基本上是一個競爭的智識中心。
1936年,史蒂格勒接獲埃姆斯(Ames)的愛荷華州立學院(Iowa State College,之後升格為大學)助理教授聘書。也就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和美可小姐結婚,他們是在芝加哥的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認識的,而大家都暱稱美可為「小寶寶」(Chick)。美可生長於賓州的印地安納市,其父是當地律師。她從郝約克山學院(Mt. Holyoke College)畢業後,教了一段時間的書,之後才到芝加哥大學深造。在他們結婚的前一晚,美可的父親將她叫到一旁,警告她說,匈牙利人有打老婆的習慣。其實,這位岳父大人是多慮了,因為史蒂格勒只有四分之一的匈牙利人的血統。
史蒂格勒夫婦共生養了三個兒子,大兒子史蒂芬(Stephen)是統計學家,次子大衛(David)是康乃迪克州的律師,小兒子喬瑟夫(Joseph)是加拿大多倫多市的企業家。史蒂格勒的夫人小寶寶於1970年8月,在加拿大馬斯科卡湖(Muskoka Lakes)邊的農舍過世,那是史蒂格勒一家人過暑假生活的地方。直至1991年史蒂格勒去世,他從未再婚。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