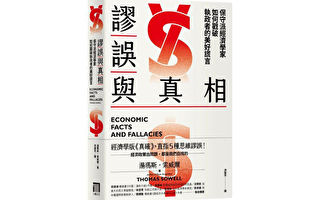【大紀元2022年04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林宜君紐約報導)近半世紀以來,美國高等教育界出現挑戰「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的訴訟、爭論與反思。專家或民間組織質疑,高等教育以多元化與彌補少數族裔為名,讓非裔或西語裔學生獲得優先入學門票,相對剝奪了白人與亞裔學生的教育權益,是否真的有效?
近年,美國最知名的反對教育平權運動的訴訟案,莫過於由民間組織「學生公平錄取」(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以下簡稱SFFA)在2014年發起的對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學錄取排亞訴訟案。
儘管SFFA一路與哈佛大學纏訟至美國上訴法院,最後在2021年12月8日,被美國總統拜登向最高法院要求駁回上訴。但是這起訴訟案讓許多美國的亞裔家長與學生更加關注在高等教育上的求學權益。
4月21日,紐約市知名保守派智庫「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在總部舉辦座談會,現場邀請SFFA主席布倫姆(Edward Blum)、紐約同源會創會會長陳慧華(Wai-Wah Chin)分享各自在反擊平權運動方面的經驗之談;紐約上訴律師賽富阮(Dennis J. Saffran)則從法律角度分析哈佛錄取排亞訴訟案。

哈佛訴訟案對美國大學生的影響
SFFA主席布倫姆在受訪時表示:「如果最高法院能停止大學在招生中考量種族和民族,長期的影響是減少我們今天在大學校園中看到的那種憤怒和兩極分化。」
「無論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任何學院或大學(的學生),都會知道他或她被錄取,是基於他們的成績,而不是基於他們的種族。」布倫姆說。
「沒有誰是『太多代表』的,用族裔或個人沒法控制的事來當標準,這是真的在仇亞,有系統地這麼做。」紐約同源會創會會長陳慧華說,她指用族裔來判斷人是否合格,是「有偏見的偏見」(prejudiced bias)。
律師賽富阮指出,哈佛訴訟案之所以關鍵,「是因為校方針對亞裔學生而非白人」,這可以給挑戰種族偏見的人,「一件能說服人的工具」。
賽富阮認為,哈佛大學招生時歧視亞裔美國人的政策,在「巴基案」大法官鮑威爾(Lewis F. Powell Jr.)眼中是平權行動的楷模,但「這實際上在一百年前是用來排擠猶太人」。
「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是美國學生挑戰高等教育平權政策最著名的判例之一。
1978年,美國退伍軍人巴基(Allan P. Bakke)以優異成績申請加州大學,卻被校方以年齡太大而拒絕,他因此在美國最高法院起訴加大,法官最後判學校政策侵犯白人申請者的權利,宣布巴基勝訴。
大法官鮑威爾在此案中表現出搖擺態度,他的判詞中採用了哈佛大學以族裔作為錄取標準的含糊說詞,並認為合乎《憲法》。
以種族作為錄取標準的成效
《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與「曼哈頓學院」資深研究員萊利(Jason L. Riley)21日也現身哈佛訴訟案講座。
萊利著有《請停止幫助我們:自由主義者如何讓黑人更難成功》(Please Stop Helping Us: How Liberals Make It Harder for Blacks to Succeed ),探討美國政策對於非裔底層的影響。
此外,萊利也是知名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首本自傳的作者,兩人都對美國高等教育界流行的平權政策抱持批判的觀點。

哈佛訴訟案有何重要性?萊利受訪時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討論,因為(美國)最高法院長期以來一直在迴避這個問題」,「如果美國《憲法》就這麼說,如果我們關於民權法的聯邦法規就這麼說」,「這(哈佛訴訟案)只是個簡單的訴求」。
「這些學校存在歧視,他們應該停止歧視。」萊利說,「這是一個日益多樣化的社會,而這種種族分贓制度,根據膚色或種族挑選贏家和輸家,是國家的錯誤,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平權行動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我們有一些證據證明它是否有效。我們所掌握的證據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不通的。它不僅不起作用,在某些情況下,它還會適得其反。」他說。
萊利表示,「我們在加州大學看到,當他們結束平權行動後,非裔和西語裔大學生的畢業率上升了。」
「坦率地說,我認為這麼做是很受歡迎的,因為現在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絕大多數美國人,包括大多數黑人、白人、亞裔和西班牙裔,都反對大學招生有種族偏好。所以法院原則上應該這樣做,我認為這也是流行的觀點。」他說。

探討高等教育執行平權政策的聲音
美國亞裔家長與學生或許仍對「平權運動」感到陌生,但就連哈佛大學最著名的「正義」課教授沈岱爾(Michael Sandel),都讓學生公開檢驗與辯論這項議題。
2009年,沈岱爾在課堂中以哈佛大學強調錄取標準「多元化」為例,認為校方的說詞巧妙地既避開了歷史問題,又獲得大法官鮑威爾的認同。
但是當學生在申請入學時,遇上像哈佛大學「尊重多元化」、「分數不是唯一的錄取標準」和「種族也起作用」的標準時,個人的學術表現就被抹殺。
「難道我們不值得因為個人的優秀、成績、成就與努力被考慮嗎?這樣不是對的嗎?」沈岱爾在數百位哈佛學生面前提出質疑。

兩年前的11月2日,沈岱爾再次就「平權運動」為題,專訪布朗大學的非裔經濟學教授洛瑞(Glenn Loury)。
訪談一開始時,沈岱爾好奇為何洛瑞曾說「平權運動」無關乎種族平等,而是「掩飾錯誤」(covering ass)時,洛瑞給了以下耐人尋味的回答:
「我的觀點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平等,這與名義的平等不同。如果您想要實質的平等,這與光學般的平等不同。如果你想要尊重、榮譽、地位、尊嚴、成就和可控的平等,那麼你可能需要慎重考慮執行基於種族的人口選擇系統。」
美國大學的平權政策訴訟與爭論,多圍繞在「多元化」(diversity)、「共同利益」(common good)、彌補曾經的「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受害者等主題。
「平權運動」除了直接影響學生能否入學、美國《憲法》的解讀,還涉及人性的尊嚴。時至今日,高等教育是否應該將平權政策作為錄取學生的首要標準,社會上仍是議論紛紛。
責任編輯:陳玟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