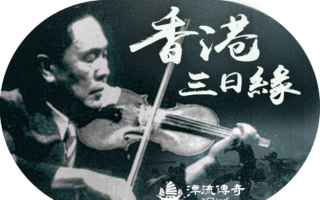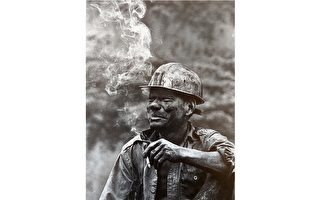【大纪元9月20日讯】“骂我最容易了,我从来没作过交响乐。”终身致力于民族乐曲的黄友棣教授如此调侃自己。这位小学音乐课本就出现的作曲者,您一定不陌生。您会唱“杜鹃花”吗?“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对了,就是这一首歌的作曲者。
豁达开朗大师风
“黄友棣教授”在音乐界是个响当当又受敬重的名号,认识的人大凡听到他的名字会出现一种共同的表情:眼睛一亮接着微笑点头,如沐春风。
与教授初见面是在八十四年,我参加高雄市汉声合唱团时,一场以他的曲子为演出主题的演唱会前的一两个月。黄教授几次翩然而来,细细聆听,然后整曲讲评。在课堂中,他还亲自为我们伴奏“杜鹃花”。专注的指导,并配合我们的指挥,在其后把乐曲气氛适时加强、抑低,没有藏私、没有疲劳、更没有架子。何谓大师?就在这简单的举手投足中,不言可喻。另外,经常有人登门求助编曲、请教问题,教授总不会让人空手而回。他为各学校做的校歌,据说有上千首,无私之心益显大师风范。
乐天知命享余年
事隔多年,这次采访我再度握到黄教授的手,十分的柔软温暖。他给我看他的牙说:“不整齐但全都是真的。”“大概是我小时候家穷,没钱买糖吃。”人们一直对他的养生之道充满好奇。他的说法是:“我吃得很简单,别人的一顿我分三顿吃,别人活五十年我可以活一百五十年。哈哈!”每天上菜场买菜走一走,是他最大的运动。活到这把年纪,老友一个个走了,他依然生活自理。想当年:“好多算命的朋友都说,我是个‘捧着寿桃吃不到的人’。”别人是过一天感觉少了一天,他则是抱着每过一天就多赚一天的想法。还笑说自己到了59岁时就抱定:“天天等着‘它’来,天天不见‘它’来。照样有一天,做一天,决不放弃!”看来这些“铁口直断”是踢到铁板了。
黄教授年近九旬,我们还以为才60多岁。一个私心越少的人,无形中似乎就越应合宇宙的理,时间对他的制约力相对减少很多。
音乐教育全方位
黄友棣教授认为音乐训练并非只是磨练唱奏技术。例如他有机会做乐曲讲评时,总会先介绍作曲背景,因为歌词涵意一旦弄错,则乐曲的表达及风格走向会偏离,甚至荒腔走板,贻笑大方。他说要小心中国歌曲的“声韵”变化,每个字会代表不同的涵意,如果作者或演唱者不注意,则经常会犯以下的错误:
“蝴蝶飞飞”唱成“蝴蝶肥肥” “飞机”唱成“肥鸡” “大道之行也”变成“大刀之行也” “长相思”变成“长想死”…… 这样子不就差很远了。
淡泊名利心境宽
因为对民族音乐的卓越贡献,先后获得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以及行政院文化奖。怀着感恩的心,黄教授也不禁感慨,他曾经因为获奖而负债、甚至获奖而得罪人于无形。黄友棣教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诠释了心中的无奈:
“听到群鸟歌唱,不妨欣赏片刻,却不必大喜欲狂,因为,一下子就过去了!遇到鸟粪脏臭,难免烦恼些时,却不必终宵不寐,因为,一下子就过去了!”“只知尽责无轻重,最耻言酬计短长。”(梁寒操先生的驴德颂)黄友棣教授的一生还在进行着,名利虽看淡,人情仍往来。只是不陷在烦恼中,“说我好坏,很少动心。”问他完稿后要不要过目,他摇摇手说不用了,豁达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一生,我的笔触,各自负责罢了!
这位与中华民国同龄的长者,一生精研中国风格的作曲与对位,并有深厚文学造诣,但没有文人相轻的狭隘心理。其思想及人生哲理,实为一代典范。
乐坛奇葩的诞生
黄教授民国元年在广东高要出生,排行老六。两岁时父亲早逝,留下不善理财的母亲跟七个兄弟姐妹,田产给人占了,生活十分刻苦。由于自幼孱弱多病,许多长辈都断言他活不到十六岁(弱冠)。但他自小学、初中连续三年即以严格的身心磨练,学习游泳、马术、武艺等技术来冲破自己体能的限制。
“我从小没过过生日,我母亲在我生日前,别人要问起就说还没到,隔几天人家又问,她就说已经过了,不劳费心。现在想起来,应是我母亲怕别人破费。”大概受他母亲的影响,这次的午餐约会,他早就安排好了进退,我连账单都没摸到。
音乐生命的启蒙
由于家贫,黄教授初中时期除膳食费外,没有零用钱。先是帮同学学医的哥哥绘制生理插图赚零用钱,其后受派当小学军训老师。后来校长看他工作负责,又请他任教国文及英文课。在那时因三哥是国乐团的台柱,唱奏的地点就在三哥的住室,所以经常有机会接触乐器,举凡扬琴、月琴、胡琴他都能奏。
1928 年考上大学预科,除课程繁重外,还要在市立小学任教,赚生活费。在这青年阶段,有位好心的同学借他一把没有琴盒的小提琴,像青菜一样地用纸包了起来。尽管“无师自通”的演奏方法并不正确,但也能奏出流畅的外国小曲、圣诗。同学的哥哥一听,深觉提琴的声音优美可爱,立刻又要了回去。因为无琴可用,遂央求二姐设法标会筹得六十元(小洋银元),购得一具差强人意的琴。就这样从此挑起了天生对音乐的热情,也让他走向音乐教育的路越形清晰。
在强烈学习音乐的渴望下,利用帮别人合奏的机会,趁机学习一些技巧。另外在大学学钢琴时,与几位女同学合租一架琴,安置在职教员联谊会中的贮物室。这地方靠近校园水池,黄昏蚊蝇多,谁也不愿那时练,他穿起特厚长裤、手脸擦上药油避蚊虫,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练足四小时。由于租琴的女同学们乐于教他,又遇明师李玉叶收为徒弟,才正式学习钢琴。
乐教生涯的转折
大学毕业后,要想将所学贡献在音乐教育上,除必须考取英国的音乐学位外,还要能演奏、能作曲、能指挥合唱团演出,并具有足够说服力。为此,每周一天要搭车至广东,随李玉叶教授学钢琴。隔一周再随俄国提琴名师多诺夫(Tonoff)学提琴。至于和声对位则全凭自己自修。几位好同学听说他要登台演奏,一齐集资买一把好提琴送他,令他感动流泪。后来他如愿在香港以高分考取英国“王家圣三一音乐院”提琴学位。
问世间情是何物
背负偿债的宿命
小时候黄友棣兄弟姐妹们最爱听母亲讲鬼故事,有一次母亲讲了讨债鬼投胎,讨完了就离开人世的故事。哥哥忍不住问:“不晓得我们要讨多少债才肯走呢?”母亲很生气地说:“你们是来还债的!”
从此以后“只为偿债而来”的观念,深刻在他心中,使他甘于贫贱,逆来顺受。家中的债大部分落在他当音乐教员到教授的薪俸上,所有的债,包括举债出国进修,一直到六十岁才全部还清。
即使还清了债,他悟到人生还是一连串债务的连锁,不是人欠我,就是我欠人。他讲个故事:一位无子嗣的孤零人向高僧诉苦,他一生清白,不曾亏欠他人,也不让他人亏欠,为何上天不赐他有儿女?高僧答曰:“生佳儿所以报我之缘,生顽儿所以讨我之债,汝不欠人,人不欠汝,如何会有儿女?”
不受拘束的独行客
身材颀长,浓眉大眼,琴艺超群加之彬彬有礼的黄友棣,自年轻便有许多学妹、女孩常来找他。“烦都烦死了!”当时又穷又好学,一心只想好好研究作曲理论的他,遇到一些来势汹汹的女朋友,总有特殊方法逃之夭夭。例如告诉她:“我所投身去做的事绝无赚钱可能,其次家中尚有大笔待我去还的债项,而且命相家早有定论,我必死于非命。若想做个穷寡妇,乃可决心嫁我。”
后来同学告诉他真正避开这些纠缠,唯有结婚,“死会了”就清净了。并推荐了一名很喜欢他的女子。结婚后一个礼拜他就感到婚姻生活更麻烦。“我天生是个孤独鬼。”音乐的创作与研究永远比婚姻有趣。他们聚少离多,这一场婚姻,结束在他的前妻带着三个女儿赴美移民而他决心去罗马深造之际。
民族音乐的推手
1937 年日军侵华,县立中学随县政府迁入乡间。在撤退时,广东行政训练团需要一名能作曲的音乐教官,他受聘后为筹办的艺术馆负责音乐工作,并为儿童教育院编音乐教材。在艰苦的环境中,迫使黄友棣教授不断地成长,并形成独特的作曲风格,此时期作品多为无伴奏的歌曲,他运用趣味的方法来编作无伴奏合唱曲。著名歌曲杜鹃花、月光曲、归不得故乡等,便是该期间的代表作。由于战局随时有变化,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办音乐讲座或演奏,多以提琴为主,并教众人唱抗战歌曲。也将各地的民歌选编一、二首为提琴变奏曲,用来提升当地艺术水准及发扬民族精神。
舍我其谁的情怀
46 岁时黄友棣教授带薪出国留学罗马,主要修习中国的风格和声技术。许多人不明白为何要去意大利学?因为二千年前的汉代就有直通意大利的“丝绸之路”,我国的曲调由此经中亚传到土耳其,米兰主教安希洛兹(Ambrose)在第四世纪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圣歌,用和声把他们加以发展,也是留传流至今的格利果圣歌的前身。
在罗马六年中,他认为当前中国需要的并非交响乐及歌剧,而是培养作曲人才的资料,于是着手编出一套中国风格的和声作曲法。不只谈理论,同时创作实际的乐曲,这期间传颂一时的代表作有:大合唱部分-金门颂、中华大合唱、琵琶行;艺术歌曲则有:燕诗、陌上花等。
若非经历一番民间疾苦就出国进修,终不切实际。环观留学回来的音乐界人士,回来后只是把西方的一套搬过来表演几回,或随潮流教书以终,甚至也有人愚昧地想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摧毁另寻出路。莫怪他要大声疾呼:“泰山应及早醒悟!”森林里的泰山给母猿养大,凭其天赋智慧方才醒悟过来,了解自己是人而不是猿,不再跟猿猴乱闯。中国音乐的发展谁来做?何时才能醒悟?想与世界潮流合一前,应先确立自己的民族音乐的定位。
虚怀若谷乐开心
1987 年7月黄友棣教授由香港移居到高雄,为文化沙漠注入了水及养份。当年就与萧飒先生合作写了“诗画港都”及“木棉花”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黄教授创作源源不绝,为儿童、为合唱团、为佛教界、为经国先生、为六四天安门的同胞们不停地写。他谦虚地说:“一个人一生做一件事,无论笨得如何,都可以成功。”
而如此专注忙碌的他,作何消遣?“其实我工作充满趣味,不必向外求。我为众人作成歌曲,使他们奏得开心、唱得开心、听得开心,各个人的开心合起来,就是我的开心。”
“先天下之曲而曲,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黄友棣一生为众人写曲而忙碌,依然为自己赚得无限的喜悦。◇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