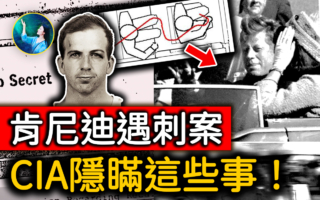【大纪元1月7日讯】在德国罗滕堡(Rottenburg)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二层楼上高墙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出版社老板兼作家韦尔弗里德‧克利泽(Wilfried Kriese)指着靠墙摆着的四个木质书架说:“这些书我都读过,我读了几千本书。”对于一个出版商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但对于一个语言书写障碍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奇迹。九年正常学制教育和三年职业培训,克利泽都是在特殊学校度过。
幼时受打击 语法拼写成灾难
克利泽的语言和读写障碍并不是天生的。两岁时,父亲的去世不仅使他的母亲成为有四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而且给他带来巨大打击,一直和正常儿童没有区别的他从此失语,等他重新说话时,人们发现他发音不清,并且有读写障碍,“直到七年级时,我才能较顺利的阅读。”他回忆道。
上学时,克利泽的梦想是当动物饲养员,因为他对动物有着特殊的喜爱,但最终他还是上了三年的木匠职业培训,至于当作家和出版商是当时的他想都不敢想的。“我那时的语法只能用灾难来形容,拼写也是。”他形容二十年前的自己。
二十岁时,为了能够正确填写木工的单据,他参加了跨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个业余高校德语班。为了不让同事发现他的拼写问题,工作时,克利泽一直在兜里揣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诸如抽屉之类的词,填写单据时,他就悄悄拿出纸条,看一眼这些词怎么写。
面对社会排斥 寻求沟通对话
“在特殊学校里,我们感觉很舒服,因为我们都是有着不同程度语言读写问题的孩子。但出了校门就不一样了。”克利泽在自传中写道。他的很多同学在校外经常对别的孩子使用暴力,因为他们几乎被所有的社交圈子排斥,加上一些孩子本身就是来自经常使用暴力的家庭,于是这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变成了对社会的仇恨,一些孩子就通过使用暴力来发泄。
生性温和的克利泽来自一个虽然不富有,但没有暴力的家庭,母亲为他能够学习付出巨大的努力,用本来就不多的收入,支付克利泽的补习费。克利泽面对社会的排斥,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摆脱仇恨,寻求沟通和对话。
著书二十余 关心边缘人团体
廿五岁时,克利泽突然有了想把他身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写下来的愿望。他没有敢告诉任何人他的打算,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人会认为他能成功,会支援他。两年后,他的自传,也是他的第一本书终于出版了,当然有人帮他修改了语法和拼写。当时还没有他能买得起的电脑,也没有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德文正确书写软体。一个一直因为读写障碍而不得不上特殊学校的人出了本书,这让克利泽高兴得甚至晚上抱着他的第一本书上床入睡。
从二十岁开始,克利泽不断的参加不同的德语班、函授写作班、新闻写作班,和语法班。与此同时,他也陆续写了廿五本书,主要涉及社会和边缘人团体问题,还有一些人物传记、专访。媒体也逐渐注意到这个作者特殊的人生经历,当地的报纸、电视台都来报导他,甚至几家全国性的媒体也采访了他。他以前上的特殊学校请他回去讲演。他的风格被媒体称为很自然,怎么说的、想的,就怎么写。
摧毁一堵墙 人生中充满惊奇
对克利泽来说,人生中充满了惊奇,“喏,您看,一年前,当我刚把出版社从我家搬到这个办公室来的时候,我怎么能想到今天我和一位中国女士,还有一位印度女士坐在一间屋子里呢?”他的助手科奈尔回过头微笑着看了我们一眼。祖籍印度的科奈尔今年廿四岁,有着印度人的深色皮肤,她从小被一德国人家收养。五年前,她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在高墙出版社打工。
当然最大的惊奇就是克利泽的高墙出版社。出版社的座右铭是:“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想摧毁一堵墙。”在克利泽自己的人生中,从记事起,就是在面对和破除一堵又一堵的墙,不解、孤独、愤怒、仇恨、失望,觉得被遗弃……四十二年走过来,现在的他在墙外见到了另一番风景,不只是他自己的廿五本书,还有一百多个作者委托高墙出版社出的书。
他邀请作者参与出书的过程,让作者亲眼看到如何从一个电脑文件做出一本书,分享个中喜悦。而他,一个专家认为不能正常学习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而且还激励了很多像他这样的边缘人,鼓起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和社会。
享受写作乐趣 获奖不是目的
在外人看来,这一切风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温莎大学授予当时四十岁的克利泽的荣誉博士头衔,对于一个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人来说,这样的荣誉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克利泽对得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我从中得到了乐趣。我不喜欢工作这个词,出版社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为了竞选一个奖项而写,那么就得写得符合一定的条件,写作就不再是我想要的写作了。如果写完了别人给我一个奖,我当然很高兴,但得奖不是目的,而是写作带来的结果。” ──转自《新纪元周刊》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