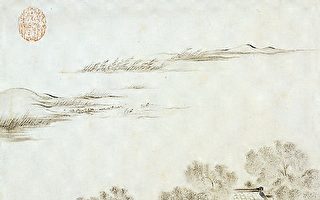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十六》)
【注释】
攻:《论语》中孔子说过“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此两处“攻”都做“攻击”解。但“攻”也有攻治、学习之义,如,攻金攻木,攻读等。
异端:一说指杂学、邪说;但如杨伯峻所说,孔子之时,还没有诸子百家,也没有佛教,而且儒道还未完全两分,不过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一说指事物的两个极端,如“过”与“不及”等。
也已:句末助词,无义。《论语》中有多处。也有人将“已”看为动词,作“停止”、“消灭”义。
【讨论】
本章历来争论纷纭。先简单罗列一些白话翻译:
“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钱穆)
“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杨伯峻)
“一个人于修业时而分心于外务,那是有害的。”(毛子水)
“批判其他不同立场的说法,难免带来后遗症。(傅佩荣)
“攻治杂学邪说,这是祸害啊。”(孙钦善)
“只钻研不同的一端,那就有害了。”(《论语今译时析》增订版)
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对歪理邪说要坚决批判;(二)治学不能走极端;(三)学问要兼容并蓄,攻击异端学说有害。
那么,我们如何尽可能地靠近孔子原意?还是用孟子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以孔子出生之年(公元前551年)为线,可分为上2500和下2500年。上2500年,从伏羲八卦到黄帝飞天,从周文王演易到老子五千言,道家为中华文化之根脉。孔子处春秋晚期,问道于老子,始创儒家,儒源于道,儒道并非完全两分。后数十、百年,有百家争鸣;再后,佛教传入,道家中之一部分演变为道教,儒家中之一部分演变为儒教,乃为三教。至赵宋,理学家们将杨墨等百家之言、道教、佛教等都称为异端邪说。至于西方历史,其从宗教教派出发,对于异端——通常指违反一个宗教的重要教义的教派及其学说——极为严苛、残酷。因此,孔子之世异端一词,不能以后世异端一词之通常含义来理解。
或有人举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来注解本章。据传,“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连子贡都不解,孔子说:少正卯有“心逆而险(通达事理却又心存险恶)、行辟而坚(行为怪僻而又坚定固执)、言伪而辩(言语虚伪却又能言善辩)、记丑而博(对非义的事知道很多)、顺非而泽(言论错误还要为之润色)”之“五恶”,人只要有这“五恶”中的一种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诛”, 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恶”的“小人之桀雄”,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他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孔子家语‧始诛第二》)
本文以为,即使有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但少正卯是否就一定是本章所指的“异端”呢?目前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以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来注解本章,显得牵强。
大家知道,孔子强调“中庸”,过犹不及。钱穆认为: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孔子曾说:“我有知吗?我实是无知呀!有鄙夫来问于我,他心空空,一无所知,只诚悫地来问,我亦只就他所问,从他所疑的两端反过来叩问他,一步步问到穷竭处,就是了。”(子罕篇)
再说,孔子本人是宽容、平和的,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不搞强制,不强求一致。还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篇),也并没把“道不同”的人视为敌人,仅仅“不相为谋”罢了,并没有排斥异己。
综合这些来看,本文倾向于钱穆的观点。
主要参考资料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语集注》(朱熹,载入《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直解》(张居正,九州出版社)
《论语新解》(钱穆着,三联书店)
《论语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
《论语今注今译》(毛子水注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论语三百讲》(傅佩荣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论语译注》(金良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论语本解(修订版)》(孙钦善著,三联书店)
毕宝魁、卞地诗:《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本义考辨
看更多【《论语》说】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