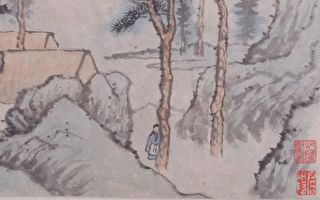走过旧时的蹊径——代序
我是个不积极又不果断的人。生活散漫离乱,得过且过。自己这些年的研究,亦复如此。其实也说不上什么研究,只是课余之暇,独坐书房,闭门造车,东拼西凑,了无章法可言。
至于如何选择历史这个营生,说来也很偶然。只缘高中毕业那年,终于留级,但功课未见起色,只有历史科较出色,但也不过七十来分,其他各科可想而知。不过,我想读的是新闻,那时台湾还没有新闻系。心想没有新闻,不如读旧闻。因为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但不论新与旧都是一样,我都是妄想,肯定考不取,只借此台北一游。但却意外侥幸考上了,真是意外的意外。
当年台大历史系,在傅斯年先生的调理下,是台湾大学的第一系。名师如云,南北混同。但我却漫步椰林大道,不知历史为何物,于国计民生何补。不过,后来问题终于来了,因为毕业时要写篇论文。论文是什么?怎么写?我完全不知道。但不论怎么说,总得先选个题目。虽然,当年劳干先生没有开魏晋南北朝史,但我们班上包括何启民、孙同勋、金发根和我,却都选了这个范围。后来大家都没脱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范围。所以,我们可说是台湾培植的第一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工作者。
我的题目是〈北魏与西域的关系〉,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也许是因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吧。关于阳关,四年级时劳先生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讲的就是阳关,一年的时间徘徊大小方盘城之间。不过,这门课选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两三个旁听的,使我那一年再也无法逃课。不过,这个问题对我的论文有些帮助,我的论文大概写得还算不错,劳先生给了九十六分。毕业后报考研究所,劳先生为我写推荐信,说我对白鸟、羽田、箭内的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可继黄文弼楼兰未竟之业,期许颇高。其实我当时对这些日本学者的著作,略有接触,但却不尽了解。而且对于“西征楼兰”,那是条茫茫的天涯路,实非我能力所及。而且班上同学高手不少,衡量再三,我拿了推荐信,却没有报考。
不过,“西域”,对我以后申请香港新亚研究所,有很大的帮助。我申请新亚研究所,也是非常偶然的。那是退役之后,在历史博物馆研究组工作,负责的业务是国际交换,因和单位主管相处不洽,递了个“请辞,乞准”四字的呈文,就下乡教书,开当铺去了。在乡下一年,教书尚可,当铺却开垮了,又回台北在个书店当门市。那时我刚结婚,居于陋巷违建之中,生活非常艰苦。一天看到报上一则广告,香港新亚研究所在台招生。我妻见我整日沉湎“一剑光寒十四州”中,并非长策,总该混个功名,远了去不起,这里倒合适。所以,劝我报考,但我兴趣缺缺。倒是我的朋友万家茂非常热心。那时他正读台大医学院生理研究所,做完实验,就来窝居,两人各据一椅,追读金庸的《萍踪侠影录》,即《射雕》。他为我到学校申请成绩单,为研究计划找打字行,并且在申请截止前一天晚上,陪我到邮政总局投递。
申请研究所,研究计划是必须的。但我却不知怎么写,用些什么参考书。好在自己在书店门市工作,架上还有几本通俗可用的书。于是,就以自己的论文为基础,再以读过一些汤恩比文化的挑战与回应模糊的概念贯穿,写成〈西域‧文明的驿站〉的研究计划。认为西域环绕沙漠的绿洲地理环境,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早期处于农业与草原文化之间,随双方的政治势力而沉浮。其后界于东西文化交汇之处,由于本身无独特的文化基础,因此,东西文明传递至此,皆能保持其原有文化的风貌,以待另一种文化的吸取。西域居于其间,缓和了两种文化接触与挑战的冲击力。计划寄去四五个月,如石沉大海,我早已忘记这件事。一日突然接到通知录取了。后来知道这次招生只有一个名额,是亚洲基金会给的。包括台湾、日本、东南亚各地十九人申请,我竟又侥幸录取了。据说当时校外委员罗香林先生非常欣赏这个研究计划。
进了新亚研究所,拜在牟润孙先生门下。不过,这个研究计划只是进阶之用,如要再进一步探讨,就非能力所及了。那么,从何处切入,颇费思量。后来想到初入台大历史系时,因鲁实先先生之嘱,读了一部黄善夫刊本的《史记》,接着又读了半部《汉书》。于是便从《史记》所载高祖“平城之围”入手,讨论汉匈的和战关系。写成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稿子,注了三四万字。这篇稿子是自习之作,目的在学习材料的运用与掌握,从来不敢示人。不过,后来研究所月会报告〈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以及对长城问题的探讨,和现在写司马迁《史记》关于对汉匈问题的解释,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所谓研究所月会,由钱穆先生亲自主持。每次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与学生各一,提出报告。然后由各导师提出评论,最后钱穆先生作总结,气氛颇为肃穆。轮到我报告,提出的报告是〈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文章以文言写成,两周前已分送诸导师与同学。不过,想想有所不妥。因为和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有相左之处。钱先生对瓯脱的解释,取其原始义,即韦昭所谓“界上守屯处”,与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所云:“境上候望之处”。我则取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的引申义,即“瓯脱,闲地也”。扩大为“农业与草原民族间的缓冲地”。因此,我请示师父牟润孙先生,是否要删去与钱先生抵触之处。牟先生说钱先生不一定会记得。但钱先生不仅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并且很坚持。对我作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最后还是郑骞先生以辛弃疾的一句词:“瓯脱纵横”,为我解围。
这次月会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多,是新亚研究所月会空前绝后的一次。老夫子真的生气了。以后在新亚研究所的几年,我不敢再见钱先生。直到他定居外双溪素书楼,才再亲近钱先生,多所请益。月会的第二天,一位没有参加月会的学长,走进我研究室,他光光的脑门上冒着汗珠,瞪着眼,怒冲冲地指着我说,我不该冒犯钱先生。他说昨天他没有来,如果来了,我早就躺下了!我说:“瓯脱,只是偶尔一脱,昨天已经被脱得光光,以后在新亚一天,决不再脱。离开新亚,我一定还脱。”的确,后来以长城为基线,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拓跋氏从平城到洛阳文化转变的历程,就是以瓯脱为基点出发的。(待续)(本文限网站刊登)
内容简介
只有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权威之时,史学才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空间,魏晋正是这样的时代。魏晋不仅是个离乱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文化蜕变的时期,更是中国史学黄金时代。书中一系列魏晋史学的讨论,虽然是作者研究魏晋史学的拾遗,却也道出对这个时期史学探索的某些观念。此外,关于魏晋时代的散论,以及对长城文化的探讨,也是作者曾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些以文学笔触写成的历史文章,常带感情,读来倍添温情。
──节录自《魏晋史学及其他》/东大图书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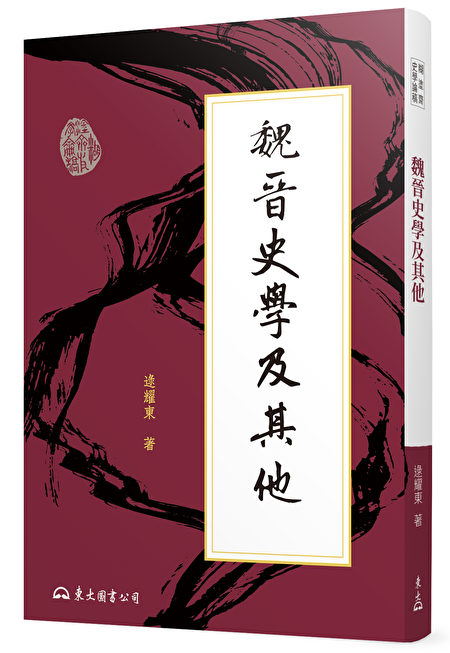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