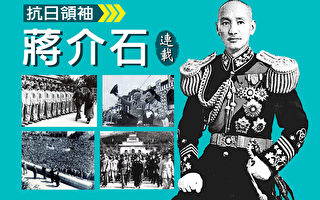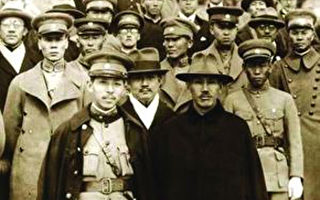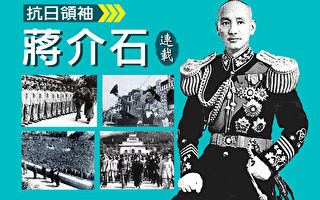第二节 战略物资大转移
日本侵华,处心积虑,蓄谋日久。由丰臣秀吉始,历三百年时光,而明治维新,而昭和新政,而田中奏折,一本侵略扩张的欲望,一步一步形成了一条顽固的军国主义路线,把贪婪的目光,始终盯在大和民族的文化母国——中国的身上。为了满足大和民族的利益,实现侵略扩张的目标,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努力发展经济,发展各类适用工业,不断提高国力。从明代的纵倭为寇,到清代的甲午海战,日本当局一次次在检验着自己的实力。
中华民族辈出英才,当年极具政治远见的蒋中正对于日本的阴谋、野心,在其青年时代已经洞察于胸,还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曾预言,日后中日两国必有一战。
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开始行动,把一举吞并中国的强烈欲望付诸行动,首先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时的日本可以说是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空军,不仅在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在人员素质和武器质量上更是大大优于中国。
而这时的中华民国,虽说已开国二十年,但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南北分治等一系列挫折,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在蒋介石的率领下,才完成北伐,实现全国统一。统一甫定,在召开编遣会议的时候,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认为“编遣方案”损伤自身实力而联手发动中原大战,历时半年有余。战火刚刚平息,日寇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寇开始侵华行动后还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策动下,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民国的江西省瑞金县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然分疆裂土,目的就是要推翻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与日后日寇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遥相对应。苍天无眼,国民政府腹背受敌!
因此,开国二十年来,中华民国无法有系统地进行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民生建设。清末以来积贫积弱的国力,无法有效改善,无法立即奋起与军力雄厚的日寇相抗衡。然而,就当时的局势而论,已不是中日两国必有一战的问题,而是两军对垒,何时开战的时候了。如何决策,如何运筹,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的肩头。
蒋介石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防形势,筹之再三,向全国军民发出“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战略主张,用以充分表示中华民族对于和平的爱护。一旦和平根本绝望,牺牲成为必然,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后关头。当最后关头压向中华民族之时,我们将毫不犹豫的奋起应战。蒋介石告诉国人:我们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虽然条件未备,时机未到,暂时不能应战,但必须要积极备战。其实,对于军事训练方面,早在四年之前,即1927年,蒋介石就已聘请德国顾问团,开始了军事筹备。当然这只是备战的一个方面,要抗击日寇并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统筹规划,及早着手进行全面备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将重庆定为战时陪都,以四川重庆为核心,形成西南大后方。将沿海地区的相关企业及时迁至四川,形成战时国民经济体系,作为支撑持久抗战的人力物资根据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曾向全国军民发出号召: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祗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国民政府在准备应战的同时,重要战略物资,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的相关企业和技术人员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及时转移到重庆,转移到四川后方去,这诸多事项摆进了统筹抗战的议事日程。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寇三月亡华的狂言,为大转移换取了三百多天的时间,就这样,战略物资和人员的大转移,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全面展开。
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工厂总数1255家, 占全国工厂总数近三分之一。为使民族工业免遭厄运,不少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纷纷计议,举厂内迁。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毛纺行会、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工商界行会组织,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呼吁,“誓不以厂资敌”,要求政府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给予迁移帮助。局势严峻,舆论强烈,国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下设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委派资源委员会林继庸等赴沪调查上海各厂现有设备及内迁可能。
接到任务后,林继庸即于1937年7月28日召集会议,研究如何有效开展工作问题。
“我为了要了解全国工厂分布的概况、制造能力及所拥有的人才,以便从事全盘性规划,乃先从全国工业普查着手。我找了三十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编成若干组,先加以训练。我恳切对他们说:“调查工作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要把调查工作做好,必须任劳任怨,态度要虚心诚恳,要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人民福利打动他们,使他们知道其从事之事业与国家戚戚相关,不可分离,期被调查的工厂与你密切合作。”……我总认为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动物,祗要你待人好,所谓以诚待人,人必以诚待之,这些人员训练完成后,即分派到全国各地从事调查工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02•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电子版P37-38)
时任职实业部的顾毓瑔先生是调查组的成员之一,调查结果由顾先生执笔形成文字报告。为了尽快做好迁厂事宜,资源委员会工业联络组下又成立了一个迁川工厂联合会,联合会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会同上海的一些爱国厂主、商人们一起,立即将工作全面展开。
上海本是个龙蛇杂处,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开工厂,目的只是为了赚钞票,对于一部分厂家来说,要说服他们远离纸醉金迷的安乐窝,扛着大机器到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另起炉灶,确实是个十分艰钜的工作。再加上,沪宁失陷之后,敌人及伪组织想用一种怀柔政策先固定沦陷区一带的经济基础,然后实行其以华制华的诡计,用我们的资源及金钱来供给他们的军用,向我进攻。敌伪对于苏、锡、常、沪一带的工业尤深注意。当时上海租界内英美当局尚能保其主权,留在上海的工业界人士,尤其是一般自称工业界绅士的人们,不察情势,以为租界仍可持作护身符,始终不肯离开上海。有些人竟以爱国为口头禅,创造“孤岛上工业孤军为国奋斗”的美名。假借八百壮士坚守四行的悲壮事实以为掩饰,而进行其投机事业。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在上海站不住脚了,又无跑进后方来奋斗的勇气,于是麇集香港做买卖。这些人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没有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精神,说什么搬迁时,困难重重,政府无法也无力解决,视重庆四川为畏途,种种说法,似是而非,足以动摇人心。林继庸先生说:“这些人依赖外国人的心理太重,把本国政府的力量估计太低,他们费尽苦心,出些钱联络几位外国朋友,写了些假字据,在外国领事馆转理登记的假手续,在工厂门前挂上外国旗子,自欺欺人地以为是万全之策,同时他们又要学时髦,因为到后方兴办实业是时髦的口号,便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于是把工厂的招牌挂在重庆,自己仍旧在上海或香港逗留。”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02•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电子版P134)
这种空气异常恶劣,若不尽快纠正,必将对持久抗战的国策,产生极其不良的后果。针对这一现状,林继庸先生立即写成《敬告逗留港沪的实业界诸君子书》一文,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九日,在《时事新报》发表。书曰:‘余每常询问仍在港沪逗留的实业家,为何不内迁共同在艰难困苦中奋斗,在兴建史上留些纪念品?总括起来,他们的答复约有五端:
(一)在港从事实业较为方便,且仍可作救国工作;
(二)在沪租界内复工,不致为敌人操纵,且可救济失业工人;
(三)产业为敌人挟持,无力摆脱,亦犹“身居魏阙,心在汉室”;
(四)军运至忙,虽窗门木板亦满载无遗,至于民间机件则虽极重要者,亦难得吨位,欲行不得;
(五)产业已为敌人毁坏,不易恢复,且落得休息休息待天下太平再想办法。
这几个道理,骤看起来颇有道理,但细心加以考察,实在是词诡、志馁,不可不解释。其与历尽艰辛内迁复工,共肩国难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尤不可不加以分判。
从前海岸线上,津、沽、青、沪等处工业之发达已经是大错误。现在由沪迁港,便是一错再错。吾人勿以为在港可以苟安。国际战机一触即发,香港一隅小岛,到时恐如瓮中之鳖,欲逃无路!且由港购进货物须用港币,甚至在港诸实业家之衣、食、住、行、娱乐等等,与及厂中职员工人及其眷属日中所需,均无一而非外汇。当此政府厉行统制资金外流之时,吾人不能协助政府以谋国内资金安定,反而极力诱使资金外流,循至财源枯竭,国势愈危,诸君子虽可多发其财,良心何忍?且吾人做事需有意义,在港生产而谓能供内地军需之用,实在是难能之事,至于内地原料供给问题,大可乘此时机利用国产品以为代替,其不能代替者,已由政府统筹供给,虽稍有困难,然亦不是无办法,若必欲事事顾虑万分周到而进行,则国难时期断无此事。今国难当严重关头,吾人更当以光明磊落之胸襟慨然赴难,不可假爱国之名躲在金迷纸醉场中说风凉话:“吾爱国,吾爱国。”拿出些微数目的救国公债来示人,实在是不能掩盖其诱致资金外流,减低内地生产能力的罪过。
在沪租界内复工,其祸国程度与上述者比是半斤八两。当老板的固可在租界内安居,然厂中一般小职员,工人及其家属,能不能亦在租界内居住?如不能,则必住在敌人控制之内,一般靠以谋生产之人们亦必环绕不去,遂致被侵占区市面逐渐繁荣,秩序逐渐安定,前次逃出战区之民众亦必闻风返沪寻求工作,市面凄凉之景象逐渐改观,我英勇国殇之血迹逐渐洗净!居其中者,不久则忘却国耻。诸君子于无意中为虎作伥,诱使许多清白良民侪身汉奸,清夜扪心,何以自解?沪海关已在敌人监视之下,敌舰走私漏税,已成天经地义,且敌币低落,诸君子厂中能否拒绝购用敌国原料?能否拒绝购用改头换面之敌国原料?胼手胝足制成之物品,能否拒绝敌人购用以供给其军需?不肖者更效法诸君子,挂牌设厂,变本加厉,购买敌国成品,冒充国货,以骗国人。敌人得诸君子之努力经营,其经济力量自然巩固,闻敌军二十余万人之供养已取诸沪津,近且决计以用诸我国之敌军悉数须有侵占地供应。敌我实力消长,系于诸君子一念,一念之差,即成大错!
其产业已被敌人挟持者,亦不是没有摆脱办法,乃是没有焦土抗战的决心。寇来时当然想利用现有产业,寇行时则必放一把火烧个干净,产业同是一样不保。假借外人保护,事实上告诉我们,其力量亦等于零。试看英国大使的被击,美国军舰的炸沉,便可了然于外人保护之不可恃。诸君子产业,与其资敌或被敌人毁坏,何如索性放把火自己毁了?若其无力烧毁,也应当加以破坏,或把机器的重要零件带走,带同技术员工到内地来努力。我们抗战成功以后,敌人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处的机器,折合赔款,拿到手来,不怕不赔回给你们。若必与敌人周旋,自己不出头,暗中派人代替,还想分得些少利益,以为虽行汉奸之实而可不居汉奸之名,世人耳目可一手掩盖,国法对于这一笔账是终要清算的。问一声“卿本佳人,奈何从贼?”那时羞答答的如何答复?且天道自在人心,国法虽可瞒过,恐怕家庭父子兄弟间也要兴起革命波澜。说什么“身在魏阙,心在汉室”?恐怕是“类我,类我!久则消之矣!”
…………
厂为敌人毁坏,虽是不能移,但是那些企业及技术人才是国内人才的精华,国家对于他们希望甚大,万不让他们随意“休息”,政府亦须帮助他们复兴,抗战之后,种种建设,亦须早日筹备。只要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政府再给于方便,当然可逐渐恢复起来,否则他们“休息”了之后,失望的失望,改行的改行,将来再谋恢复市场已为捷足者所得,也就要大费气力了。据调查,工矿调整处最近对民营工矿之协助已达资金一千三百余万元,计经汉及由汉迁出之工厂二百五十余家,平日视为荒凉之川、滇、湘、桂、陕诸省区,一旦已建立多个工业区基础。
我们试行游江畔,便觉烟突骤增,机声聒耳,看见他们数十家内迁工厂正在平地建筑,或在置机正轴,或在日夜开工制造犹恐不足。虽然是短屋茅棚,各位热心技术家正在那里绞脑汁,挥血汗,其发奋努力一如前方战士之亲临战场。他们是值得人们钦佩!在兴建史上必有他们的位置。吾人深望现在逗留在港沪的诸位实业家,不要再打万分稳当的算盘,早日入来,与他们共同奋斗,共同在抗建时期中分享荣誉!’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02•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电子版P134-138)
林继庸的《敬告逗留港沪的实业界诸君子书》,辞藻并不雕琢华丽,文字并不激昂慷慨,而是在平实无华中从如何抗战建国的民族大义立论,向实业界诸君子阐述了国难当头,应该如何把握时机,处理好德、义、利、害的得失关系,做一个爱国的实业家,切莫错过青史留名的难得机遇。此文阅读时并不令人荡气回肠,然而,那拳拳爱国之心,殷殷规劝之意,却能打动每一位读者由衷的情怀。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曾经港沪多家报纸转载,当时不少徘徊犹豫中的实业界人士读后顿然觉悟,深切认识到,在上海办工业只能直接或间接的为敌人帮凶,惟到西南大后方去才是发展我国工业建设的前途,于是纷纷相约,迁厂重庆。
顾毓瑔先生感慨万端的回忆说:令人遗憾的是,由他执笔写成的那份调查报告的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时抄走了!不过有一个数字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要迁往四川的各家工厂的机器设备总量是32万吨。在那战火横飞的岁月,要把32万吨的机器设备尽快运到重庆是谈何容易!
把战略物资运往四川,大致说来有三条路线可走,以长江为界,江北江南多取道陆路,但大部分还是靠水路,溯长江逆流西上。陆路方面:南线走赣南、湘南跨过粤汉路,穿过桂北入贵州,在贵阳右转北上,经遵义进入四川。北线:就是沿陇海线西行,过西安到宝鸡,左转南下,走川陕大道,穿越大散岭入川。
对于当年陆路运输战略物资入川的困苦状况,让我们仅以北路运输的一个实例,来窥视一下当年的艰辛。
当时负责把山东连云港电厂走北路西撤的年轻工程师孙运璿回忆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政府决定将连云港电厂运到内陆去,我…连云港我做过,所以要我负责运输。非常困难,宝鸡再往里头走都是高山,我们想的办法,没办法运。后来我一个工头,河北人,他给我建议:我们家乡里有搭车方法,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我说怎么样搭车啊,他说,首先做个拖车,我再训练一批骡子来拉这拖车。我说,你有把握?他说,我有把握。他要我试试看。我就给他说,好!我做拖车,你训练骡子,我们俩试试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这个办法。我这个工头很有办法,他训练了18匹骡子,他用鞭子训练骡子一起用力。就这样,我做拖车,他训练骡子。结果,就从宝鸡出来,爬高山,爬到四川。我还编个歌给大家加油:爬啊爬啊,要穿过秦岭之险,翻越大巴之巅,伙计们,加油吧!前面是五丁关,过个五丁关,就是广元。现在想起,非常兴奋,好苦啊!好险啊!”(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五集•大迁徙)
孙运璿先生回忆的是他七十年前的一段亲身经历,他用“非常兴奋,好苦啊!好险啊!”十个字作为他回忆这段经历的结束语,后人听起来,可能颇觉轻松,但是,“好苦啊!好险啊!”的个中滋味谁能体味!
由宝鸡翻越秦岭,把大型机器运往四川,究竟有多难?我们后人无法想像。不过,诗人李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给出了回答:“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孙运璿先生所说的“苦”“险”二字,全在李白所说“蜀道难”的一个“难”字之中。
连云港电厂从东海之滨,搬运到四川,只是战略物资大转移中的千百件实例之一,将32万吨机器设备搬运到四川,不论是走陆路,还是水路,都全在李白所说的一个“难”字之中。但是,当日寇侵略者的铁蹄踏向中华大地,国难来临之际,中华儿女们以共赴国难的坚强意志,用人力、畜力、力拔山兮气盖世之毅力,终于战胜了诗人李白所告诉后人“蜀道难”中的那个“难”字!
孙运璿,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后来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上了蒋经国时代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晚期,原本打算推荐他为下届总统的继任者,遗憾的是,就在准备推荐他的前不久,孙运璿先生因患中风而退出政坛。
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最为优秀之处在于,对于凡是对于民族大业作出有益贡献的人,永远不会被炎黄子孙所忘记,就是在民间都会有以不同的形式予以纪念和褒奖。
林继庸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遵照国民政府安排,为保存国家工业命脉,动员组织沿海厂矿企业迁往重庆四川大后方,建立战时国民经济体系,为持久抗战奠定国力基础。林继庸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推动东南各省工厂大举西迁,确实保存了长期抗战的生产力,那是一幕动人而可歌可泣的工业史迹!当初迁厂之时,厂家也曾遇到种种困难挫折,无不埋怨林继庸。林继庸任劳任怨,一力为厂家排难解忧。等到工厂迁到后方去,渐渐地赚了钱,发了财,大家又都无不感激林继庸!实业界诸多朋友非常怀念这位林先生。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七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将迁川大厦礼堂改为“继庸堂”。用以纪念林继庸的迁厂功绩,成为当时重庆的三大堂之一,另外两个是“中正堂”、“沧白堂”,而“继庸堂”是三堂中比较新的一个。
有段轶闻,不妨在此一述:据说重庆有一次举行集会,“中正堂”、“沧白堂”容纳不下,借“继庸堂”开会。典礼进行时,当司仪喊“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时,抬头一看,堂中赫然挂住林继庸的巨幅照片,司仪喊道“向国父遗像行……”,就没有再喊下去,工作人员赶紧去张罗一张国父遗像盖在林继庸的照片上,才行三鞠躬礼。在重庆除了有“继庸堂”外,在李家沱工业区内,还有一条“继庸路”。可见大家是非常怀念林继庸先生的。
林继庸先生听到这些事情后谦虚而平淡地说:“我本人数十年来立身处世,均循着正道前进,随遇而安,不以个人得失为念,我以为一个人不一定要做大官,但是要为国家做些有贡献的事,这也就是国父所说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02•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电子版P207)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