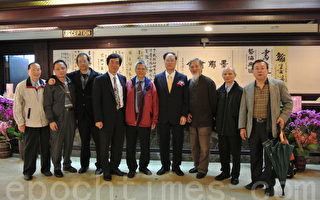【大纪元2013年01月19日讯】前言
三国演义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卷头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翁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卷头词倒不是罗贯中自己写的,是清初的毛宗岗在重编三国演义时,把明正德年间的一位博学多才的状元杨慎的一阙词,巧妙而合题的放在卷首,这首词所引发的“震撼效应”,直让后世读者对世间俗事的风云莫测,百年政局的千变万化感叹不已。
我这篇“卫国街演义”当然没有三国演义那么富戏剧性,有些故事中的人物虽然事业有成,却也还没有到名垂不朽的地步。这只是一篇当我自己也成为“白发渔翁”一族之后,“笑谈”当年求学时,那段年轻岁月的短文而已。也许哪一天与老友“喜相逢”时,也能煮“浊酒一壶”,把杯欢谈其他的“古今多少事”。
———–
台南市崇诲新村内的卫国街,是当年眷村里的一条没有铺上水泥或柏油的小泥路。也许是与眷村有特别的缘分,我在台湾的日子,算起来几乎都是在眷村渡过的。从早年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到后来台北大直的东园新村,因为父亲是军人,我们是军眷,住在什么地方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大学时期在台南的成功大学四年,我可是有选择权的,我最后还是选了卫国街的崇诲新村,一个以纪念抗战时期壮烈殉国的飞行员沈崇诲烈士而命名的空军眷村。或许是被村里那伴着我长大,熟悉而亲切的四川话吸引来的吧!我的青春时代,曾在台南市的崇诲新村渡过了近三年的时光。
记得卫国街的东边是块杂作农地,由卫国街南行,接上东宁路,再穿出大学路的一条巷弄,在巷口那间附设有冰店的“大千弹子房”左转后,就可以直达成功大学正门口的校本部大楼。卫国街的眷村住户好像都在眷舍里加盖了一、两间房,出租给成大学生赚外快。也都在竹篱笆上开了个后门,供我们这些学生房客进出。
那时我们成大学生几乎都是以脚踏车代步,由崇诲新村的租屋处骑车到我们电机工程系馆,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记得大学的最后一年,是住在卫国街三十号,一间独立的,约有十坪大小,被隔成两间的小屋中之一间。房里有一张双层铁架床。书桌两张与木椅两把则是我们房客自备的。
我们班上住过卫国街的除我之外,至少还有老周、老李与我同房的老张。在成大的四年中,有三年的时间我是与老张同住的。我俩同系、同年级,但不同组,自大一以后,就好像没有几门课是在一起上的。他的死党是他从师大附中开始就同班的五位同学,其中有四个居然在成大是同系,剩下一个在机械系。三年下来,我与他们这群死党都混熟了,班上有些同学还以为我也是附中毕业的。老张是个极具毅力与恒心的人,每晚风雨无阻的上图书馆K书,就像他现在一样,六十好几的人了,一年四季,每天还必定要晨泳。我则很少上图书馆,K书时喜欢轻声的听古典音乐,有这怪癖,每晚当然是只有躲在自己租屋里K书的份。无独有偶,班上一位绰号叫“郭盖”的同学,有一次到我房里来讨论功课,居然喜爱上了我的独特K书环境。此后郭盖就经常来我房里一面听古典音乐一面K书,我俩也就此成为这一辈子的总角之交。每晚十点,老张准时由图书馆回来,我们都得禁声,郭盖也就只好打道回府。不过我们三人在三年级时,曾远离卫国街一年,在台南市区里合租了一间民房,老张是台北长大的,完全不通台语,与本省籍的房东多少产生了一点误会。我还好是南部长大的,与房东可以沟通。高雄凤山的民风强悍,小孩子若是完全不通台语,出门迟早是要挨揍的。我那半调子台语可说是被揍出来的。
从大一的下学期算来,我前后有过三位卫国街的房东,都在同一条卫国街上,房租也都没变过,每个学生每月得付房东一百五十元。在新台币还算值钱的年代,黄金一两才不过两千元。算起来我们四个学生每一学年得付给房东近三两黄金。难怪这几位房东都阔气得很,家中也都有当年的奢侈品,一台黑白的大同电视。当年台湾的电视只有台视一个频道,电视节目内容也与现在相去甚远,播出时间好像只有晚上六小时。每天开播时,算是眷村盛事一桩,房东也会欢迎我们几个房客挤进他的小客厅去一起看电视。
在成大做工学院的学生真的很辛苦,台湾南部的风气又极端保守、没趣。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怀念的还是在台北建国中学念书时的自由又快乐日子。当年,成大工学院学生四年得修满至少一百七十个学分才能毕业,我们平常是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的。大四那年,功课终于比较轻松一些,我们才比较活得像个“大学生”。“看电视”的频率也比较高。但是民国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实在乏善可陈。娱乐性节目较受欢迎的是“群星会”的歌唱节目。黄蜀娟的“东山飘雨西山晴”,迄今还余音绕梁。电视偶尔也会播出剧情精彩的英语连续剧。记得每星期四晚上九点正,有一个小时的英语战争连续剧“战斗”(Combat!),是Vic Morrow 与Rick Jason主演的。剧情是以二次大战的欧洲战场为背景,每一集都有一段不同的故事,前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连贯性。其实剧情现在看来还是颇为幼稚的,千篇一律的总是“愚蠢”的德军腹背受敌,被“聪明” 的美军从背后丢了个手榴弹,杀得灰头土脸。同房的老张也是军眷出身,对军事片兴趣之浓厚,绝对不亚于我。他每星期四晚上九点正,必破例由图书馆提早一小时赶回,正襟危坐的在那台十四吋大同电视前报到,比上“电子学”课时还要认真。邻居的两位机械系同学也不会缺席。剧中的道具,包括三零步枪、卡宾枪、自动步枪与吉普车等,都是我们受军训时使用的美军军援品。凭良心说,这个电视剧虽然剧情太夸大,当年却是颇受全台观众喜爱的,这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在真实生活里,Vic Morrow与Rick Jason都是纽约市出身的美裔犹太人, 所以才会在“Combat”剧中把德国人拍得那么不堪。Vic Morrow在1982 年拍越战片Twilight Zone的外景时,手抱两位稚龄的华裔女孩,三人竟同被头顶上二十呎处失控墬落的直升机桨片打得身首异处,死得惨不忍睹。Rick Jason则于2000年时举枪自尽。两人的下场都很惨。
在卫国街的日子里,我们是与一位精神失常的独居灰发老妇为邻的。大一的下学期,我甚至还做了她的紧邻,每天得忍受她不时胡言乱语的喊叫声,即使紧闭房门,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有时得用棉花球塞耳熬过。全台的眷村里都流行四川话,而她却是操着北方口音。终年一袭粗布大挂,就像我们有时在电影里看到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陆农村妇女穿着。据我的第一位房东告知,因为她是“烈属”,村民们多多少少会照应她一点。但最后一位房东又说她是因为丈夫弃她而去,深受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她有个已出嫁的女儿,偶尔在周末时会过来照应一下。而且她也不是一直疯疯癫癫的,精神稍微正常时,在她后院门口见到我们,还会主动与我们这群学生打招呼。在她口里,我们这群学生都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叫做“小悲(白)脸”。“你好啊!小悲脸。”是她见面的口头禅。精神不正常的时候,我们若骑脚踏车经过她家后门,会被她抡起扫帚追着打,嘴里还嚷着:“打死你这小悲脸!”
她还能字正腔圆的唱平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唱的那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这“空城计”的调子,因为自小就常被喜爱平剧的父亲带去看平剧,所以我还满熟悉的。可是她就只会唱这两句而已,每隔几分钟就重复的唱这两句,唱得我也都快疯啦!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隔着竹篱笆教她下面那一段“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没想到她还真的跟着我哼了起来,连房东都看傻了眼。可是第二天她就又忘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那头两句啦,白教她了!
老周与我同为摄影学会的会员。有一天两人在学生活动中心的暗房里洗照片,正苦没有摄影题材,突然想到卫国街的老疯妇。两人带着相机,原本想偷拍她抡起扫帚追打“小悲脸”的照片。不料那天她老人家竟然和蔼可亲,笑容可掬。赶紧把老张抓出来替我们三人合照了一张。过了几乎半个世纪,这张照片我还好好地保藏着呢!
台湾南部民风比较朴实,再加上工学院的功课紧,我们前三年的大学生活委实是乏善可陈,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应付各种大、小考试。相对于那前三年,大四的工学院学生是“解放”了的。迷上麻将的不在少数,去“台大”的也大有人在。
哦,“台大”是我们给“台南大舞厅”取的谑称。我们几个住在卫国街的,喜欢上了桥牌。其实我们早先就会找机会打桥牌,有些短暂的,没有军训的寒暑假日子,回到台北时,我们也会聚在各人家中打桥牌。只是大四那年更疯一些。
我的固定桥牌搭挡是班上的老朱,我同房的老张与郭盖则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四人只要是凑好时间,就会挤在我们那狭小的卫国街租屋里,捉对厮杀得天昏地暗。有的时候,老张的死党也会来卫国街打桥牌,小小的屋子里居然会摆上两桌桥牌。我们的老规矩是,晚上的宵夜是由输家买单,因此大家打得还颇认真的。崇诲新村就像全台各地的眷村一样,有军眷开小吃店或是摆个小吃摊赚外快。一人一碗干拌面,再加两个卤鸭头之类的便宜卤味就解决啦!每个人花不到三、四块钱,经济又实惠。
后来发现数条街外,有个摊子卖“猪杂汤”,一块钱可买到热腾腾的一大碗,碗中全是煮得稀烂的“猪杂”。所谓的“猪杂汤”,就是你平常在菜市场里买不到的猪“零件”,被混在一起煮成一大锅。若是在美国,这些“猪杂”肯定是制造宠物饲料的主要成分。但是对我们这群平日油水不足的穷学生来说,这是补充蛋白质的大好机会,大伙儿趋之若骛,打完桥牌就去吃“猪杂汤”。囫囵吞枣的吃过几次以后,我开始用这几年来在工学院做高材生被训练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起“猪杂汤”的成分来。
“头家,这系啥米款ㄟ肉?”我挟起一块看起来有点儿“透明”的肉,用那半生不熟的台语问道。“嘴齿肉!”老板嘴角叼着一根“新乐园”,喵了那块肉一眼,轻描淡写的回道。哦,是牙龈肉,觉得有点儿恶心,但还是勉强吞了下去。不久,我又发现一块肉,正面看来有点儿像小时候在地板下捡到的日本铜板,就是那种中间有个小圆洞的日本倭皇菊标的铜钱。我们那时戏称之“屁眼钱”,因为那菊标配上中间的小圆洞,就活像个“屁眼”!我左思右想,心里愈来愈不是滋味,转头把那块肉挟给郭盖看,郭盖眼都没眨一下,“我知道,不就是猪屁眼嘛!”他毫不在乎的说。不过老张和我都在乎!我俩从此没再去吃过那一元一碗的“猪杂汤”。
桥牌玩家的通病,就是自命不凡,都自认为自己是高手,直到有一天真正的高手现身啦!他就是老黄,一个行事脱俗的人。有一次大概是考“电子电路”,我就坐在他旁边。考卷上有五道计算题,只见他疾笔应答,二十分钟后就缴卷离开,把老师都吓了一跳。次日下午在系馆见到他,他睡眼惺忪的又坐在我旁边。其他的课不常见到他,但这一节课他是非来不可,因为这位老师可是要点名的。我悄悄的问他:“你昨天这么早缴卷,考得如何?”“及格啦!六十分!”“还没发回考卷,你怎么知道?”“五题我答对三题,就是六十分呀!”“万一有一题答错的话呢?”“怎么会!那三题是考古题,答案我可是倒背如流的。”“再多花半小时多做一、两题不是把分数拉高一些吗?”“唉呀!我们的毕业证书都是同一张纸,填上不同的名字而已,没排名次的,你干嘛这么认真?”“我…”“好啦,老实告诉你,我前晚打了通宵麻将,昨天昏昏沉沉的能答对三题,已经是心满意足,不想多“虚耗功力”,得回去补一觉。昨晚又打了一夜麻将,现在想先打个盹,点名的时候拜托把我摇醒。”
这就是行事潇洒的老黄,桥牌桌上也很“惊世骇俗”的。他是众所周知的桥牌校队,在全省大专桥牌比赛中代成大出征,拿过奖牌的,不仅如此,他还曾被选为桥牌国手的预备队员,就是后来由沈君山领队连夺两届世界桥牌大赛百慕达杯亚军的中华队,我们念大学时中华队参加的是远东区桥赛,拿到远东区冠军才能有百慕达杯的参赛权。和老黄打桥牌,我们就都像是些有几分三脚猫功夫的镖客,自鸣得意的与修练过“达摩易筋经”的徐元平(就是武侠小说“玉钗盟”里的主角)对着干,当然是毫无招架之力。再加上我们出牌时还要思考一番,老黄就直在旁边拼命催促:“快一点!快一点!”催得人心慌意乱。
有一局牌,大概出牌已出了一半,我正在犹豫该打那一张牌时,老黄等不及地开口啦:“就打那张红心8吧!”我吓了一跳:“嘎!你还会认牌?”赶紧翻过牌看看红心8的背面是否作了暗记,“唉,拜托,牌都出了一半了,我怎会算不出你手上还有什么料。”老黄只是摇头叹息,而我也只有心服口服的份。常打桥牌的人都大致能算出外面的人头牌(也就是face card 如AKQJ等),但是要能准确算出人头以下的牌,那就得靠功力啦!
由于郭盖与老朱两人经常来卫国街混,在此双双被我封为崇诲新村的荣誉村民。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的阴历生日与老张的阳历生日正好是同一天。伙同这两位荣誉村民,我们打了一整个下午的桥牌。晚餐时间,由老张与我做东,四人骑着脚踏车到“沙加里巴”夜市去吃晚饭。在一个小摊位上点了“棺材板”与火锅,开了几瓶台湾啤酒,就在摊位前的小方桌子上吃喝起来。几杯啤酒下肚,我大概是蛮兴奋的,就开始讲起我自以为好笑的“笑话”来,这“笑话”是我父亲在总统府任参军时真实发生的。父亲讲给我听的时候,还真把我给笑翻了椅子。这“笑话”是与老总统的宁波乡音有关的。
话说老总统在总 统府里日理万机,通常是不会有闲情逸致找人聊天的。但他是军人出身,偶尔也会抽闲开个临时召集的检讨会,检讨在大陆那几场关键战役失败的原因。这时就会招在同一楼层,那些在参军室里值班的参军们来讨论。参军们都是当年曾任师、军长,甚或是军团司令的将军,带兵作战的经验非常丰富。有些战役还是他们亲身经历的,讨论起来就免不了会忘形的“据理力争”。在某一次的讨论中,某参军大概是那场战役的指挥官之一,与老总统意见相左,大声坚持他自己的主张,真的把老总统给惹火了,盛怒之下,老总统拍桌大喝一声:“强辩!”立刻镇摄住了全体在场人员。宁波话这“强辩”二字听起来还真像是“枪毙”,吓得那位参军脸色苍白的站起来,口中嚅嚅的说:“报告总统!我上有高堂老母,下有未成年子女,请不要‘枪毙’我。”把一屋子人,包括老总统在内,全都给笑倒了。
现在听起来,这绝对算是个“笑话”,不是吗?可是,当时大家只笑了几秒钟而已就笑不出来啦!只见邻座的一个中年男子,突然站起,朝我们走过来,在我面前晃了一下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一张不知是啥名堂的证件,声色俱厉的质问我:“你是那个‘单位’的?胆敢在公共场所‘诋毁’总统!”吓得我们四个人不知所措。还好,他只再撂下一句:“下回给我小心点!”后,就转身回到他自己的座位去了。说不定他心里在想∶“这小子居然有总统府里的‘内幕消息’,八成来头不小,少惹为妙。”
可是我们四个天真的大学生那还有心情继续吃喝,两分钟不到,就留下还没吃完的火锅,夹着尾巴骑着脚踏车飞快的飙回卫国街。我俩的庆生宴居然发生这么扫兴的事,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儿别扭。那个年头,“狐假虎威”的人还真不少,就像是几粒老鼠屎,把一锅应该是香气扑鼻,引人垂涎的腊八粥给糟蹋掉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如老黄的预言,我们都拿到了那张没有排名次的毕业证书。还没来得及效法徐志摩,潇洒的“挥挥衣袖”与卫国街道别,这就匆匆忙忙的收拾行囊到服役通知上的军营报到去了。大概就是因为忘了“挥挥衣袖”,这片“卫国街的云彩”就被我给带走了,它就这样天涯海角、如影随形的罩着我,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一年后,约一半的同窗又都负笈美国的各大学研究所。毕业证书没有排的名次,这会儿可管用啦!第一名毕业的老周夺得美人归(娶得我们的班宝,也就是班上的两位女生之一),去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在某大企业做研发主管。老朱也是在拿到博士学位后,投身电子业做研发主管。同房的老张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回台湾打拼,凭他那每天晨泳的坚毅性格,做到台湾两大微电子工业之一的执行长,是两岸三地电子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票附中死党也个个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大放异彩。老李任教美国某大学多年,最近更是凭他的独步科研成就,于2012年被票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新科工程院士。抖吧!?
我这都还只是报导与卫国街崇诲新村有一点儿关系的“村民”而已。至于班上其他的佼佼者,则有跨国大企业的董事长,有电脑公会的理事长,有美国名校的大牌教授,还有一大堆数都数不清的中、小企业创办人。看来,我们成功大学电机系五十七级毕业生里,还真的是卧虎藏龙呢!
老黄于十年前走啦。这么聪明的一个人,竟然是得脑癌去世的,让人不胜唏嘘。郭盖最惨,大约八年前第三度中风,导致全身瘫痪,躺在台北石牌荣总附近的安养院里,我每次因公返台,再忙也必定抽空去探望他。他虽已不能言语,但意识还是清楚的,见到我的时候情绪都会十分激动。郭盖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弟弟,是台湾医社的社长,也是荣总的医生,就近照应他的余生。每每想到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困境,心里还是蛮难受的。
至于我呢,半退休啦!在含饴弄孙之年,做我自青少年时期就爱做的工作─爬格子,心满意足矣!
2012年11月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