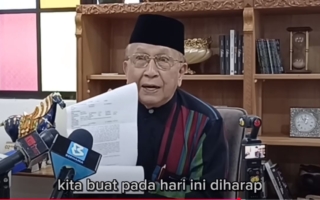启程
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份看起来阴郁又累人的职业。“你怎么会选这份工作?”“不是很令人沮丧吗?”事实上,这份工作带给我们巨大的满足和成就感,甚至是快乐。
怎么可能? 部分原因是,我们看到了出生和死亡(降临人世和离开人世)之间,有着非常类似之处。而这份理解,让我们认定了自己的使命和报酬。
身为安宁护士,我们认为自己的角色与助产士或接生婆恰恰相反,他们协助一个新生命从子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则是在人生的另一端,协助病患安稳地从活着步入死亡,去到死后存在的某个地方。
我们会对病患和家属这么说:“让我把我所知这个过程的一切告诉你们。让我们善用这些资讯,并针对你们个别的特质、需求和人际关系,一起让它成为你和亲友最美好的经验。”
你读到的某些案例是我们在医院或居家照护体系中遇见的病患,也有些是别人的经验。但是大部分的资讯来自于我们多年来担任安宁护士、照护临终病患的临床经历。
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分娩与临终方式曾有一段时期,人们普遍在自己家中迎接出生和送别死亡,很多国家到现在依然如此。
到了二十世纪,一些工业化国家,分娩和死亡的场景被人们从家里移到医院,成为一种医疗过程,必须经由医院的专业人员依程序进行。
分娩时,准妈妈必须完全遵照指示,只能用医生允许的麻醉剂和止痛方法。准爸爸不能进入产房,其他家人则被当成外人,甚至是骚扰者,资讯的接收很不透明。
安宁病患遭遇的情况与这些限制相似,甚至还受到多一层的羞辱:被当成医学上的失败品。
医护人员经常不自觉地,把临终病患移到离护理站较远的房间,对于病患的按铃求助也迟于照料。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最近几年,对父母和宝宝本身的重视已超越制度政策和技术层面。分娩,再一次变成生命经验的一部分,而非仅是医疗程序。
现代孕妇受到有求必应的待遇,能获得所有想要(或需要)的怀孕或分娩资讯。他们可以选择在哪里生产、由谁接生,若有必要,使用哪一种方式止痛。
准爸爸和较大的孩子也是生产教育的一部分,且通常会参与分娩过程,而这当中不一定要有医院或医生。
如今,许多妇女透过助产士或接生婆的协助,选择在家生产。即使真的在医院生产,通常是在布置得比过去惯用的无菌产房更舒适、更像个家的分娩套房里。
这种更能掌控情况且容易取得资讯的做法,让整个生产经验变得更舒适。在场的家庭成员与母婴共享了一种特别的连结,且因共享了那撼动人心的一刻而使彼此更加紧密。他们参与愈多、了解愈多,便能得到愈多的体会和成长。
于是,面对死亡也重新回归“老派”的做法。感谢安宁疗护运动的兴起,把疗护重点从专业医疗人员和他们的机具,转移到最核心的人身上──即病患和他的非专业照护者(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就像分娩一样,照护临终病患的方式已尽可能由核心人士主导,且他们亦能取得所有必要的资讯。临终者不再只能被动地接受检验和止痛剂,而是能主动控制他们的生命和死亡。
投身安宁疗护如果能选择,多数人宁愿在家度过最后时光,且多数家属也希望得到病患情况的真实报告。
尽管在家照顾安宁病患,实在很艰难且令人恐惧,但多数家属还是撑得过去。有了适当的训练与支援,家属也能学会如何让病患感到舒服,特别在疼痛控制这部分;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学会如何以药物让病患减轻痛楚,又不至因用药过量而导致不省人事。
而且,到最后,病患比较不会觉得孤立和恐惧,照护者也能较感宽慰,知道自己已经尽全力陪伴关爱的人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尽管死亡是件充满悲伤痛苦的事,却能带来完满终结。用这种方式面对死亡之后,很多人说:“这可能是我遇过最困难的事,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或是“现在她走了,唯一让我宽慰的是,她和我一样明白,为了她,我已经尽全力了。”
安宁院是照护临终病患的主要机构,其疗护计划是顺应自然、以病患为中心,最重要的两个原则是:
第一、病患有权选择自己要如何度过最后余生;
第二、他们的最后余生应该尽可能安宁舒适。
安宁院也协助家属以正面的态度通过这项难熬的生命试炼。现代社会中有许多非传统的关系却能相惜相挺的人,这证明了血亲或姻亲不必然对每个人都是最强的支持。本书从头到尾所说的家属(亲友),都包括了病患自己认可为家人的人。
多数病患选择在家度过最后的日子,而不是在医疗院所(安宁组织、医院、安养中心),不过后者能提供必要时的住院照护服务。
无论大小、型态或相关组织,安宁疗护不只是一个地方或一群人,而是一种关怀的理念。
我们在安宁体系服务的人,不啻把它当成一份职业,更看成一套人生哲学,它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同时影响了我们所照护的那些人。
抚慰心灵的疗护体系
安宁疗护运动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活动,以前是要让旅途劳顿的人感到安适,而今演化为关怀照护的哲学,让人安宁地走完自生至死的最后一程。
远自中古世纪,安宁院是让旅客或朝圣者稍作停留的地方,以便他们休息、补充食物、得到庇护,或者在他们疲劳、生病、等待死亡的时候,获得帮助。
当时的欧洲有好几百个安宁院,遍布在朝圣的路径上。十九世纪初,爱尔兰慈惠姊妹团(Irish Sisters ofCharity)在爱尔兰和英格兰成立了数间安宁院,其一是位于伦敦的圣若瑟(St. Joseph’sHospice)。
英国医师桑德丝(Dame Cicely Saunders),就是在那里开始了她的研究,为她日后的现代安宁疗护运动奠定基础。
一九六○年,桑德丝医师提出照顾病患的新做法:设立类似中古世纪的安宁院,建构成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来“照护临终者,让他们在形而上的旅程中,从这个世界,度向另一个世界”。
她的做法是以爱与慈悲的关怀,结合偏重缓和疗护(缓解、减轻症状)、而非治愈疗护(企图防止病情恶化、让病体复原)的精密医疗技术,来照护临终者。
一九六七年,桑德丝医师在伦敦郊区创立了圣克里斯多福安宁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于是现代安宁疗护运动自此诞生,尔后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你很重要是因为你是你。”桑德丝医师这样告诉临终病患。“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很重要,而我们会尽可能帮助你,不只安详地走向死亡,还要好好地活着,直到最后一刻。”
在此同时,美国精神科医师伊莉莎白.库伯勒. 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研究和著作,开始影响人们对于生和死的看法,让安宁疗护运动更加落实而茁壮。
一九五九年,库伯勒. 罗斯医师在耶鲁大学的研讨会上发表一篇论文,描述临终病患所受的苦,即便住在最好的医疗院所里,他们通常被隔离安置,时常被施以高剂量的镇静剂(但还是痛),而且极少有机会自行选择别人对他采用什么疗法。
没完没了的检验,就为了监测他的病况和治疗效果。他们总是被视为一连串的生理症状,或者干脆当成医疗体系的失败。然而,在这些“专业疗法”下,丧失的是一个有着恐惧、疑惑、欲望、需求与人权的人类生命。
库伯勒. 罗斯医师在她一九六一年的著作《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Dying )里,继续探讨这个主题,试图让社会大众用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末期病患。
启动居家安宁照护的力量安宁疗护的历史不算长,而且安宁护士所扮演的角色与一般医院护士截然不同,所以,很多人都无法了解这份工作。
安宁护士是跨科目医疗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包括医生、护士、社工、牧师和志工,还会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应需要前来协助,如营养师、物理治疗师、呼吸治疗师等。整个团队只有两个核心任务:疗护病患和协助家属。
他们教导家属如何在家照护病患,以及当患者的病情起了变化,家属需有什么心理准备。
他们还必须判断照护者是否需要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协助,以便熬过这场严峻的考验。病患往生后,他们也提供家属或照护者抚慰性的支持。
居家照护的兴起,意味着以前只有在医疗院所能提供的各种医疗机具,现在可以在家里使用了,而且不一定要由专业人员执行,例如,监看病患的生命迹象、施打静脉注射的止痛剂。
这让病患得以留在最没有压力、最舒服的地方,由家人照顾,而家属也能随时联系安宁疗护团队,就连夜间或假日都有医生和护士待命。
协助居家照护的安宁护士虽是整个团队的一员,但多数时候独立工作,照护六至十个病患。
家庭访视一次约一、两个钟头,长度和频率依病患和家属的情况而定。刚开始,护士每周探访两、三次,死亡将近时变得频繁,甚至天天探视。
安宁疗护的理念是尽可能让病患明白他想了解的资讯,包括自己身体的变化、疾病的可能进程,甚至死亡的可能状况。没有人受到任何勉强;疗护方式并不出于专业上的方便或临床实验,而是由病患自己决定。
当然,任何一种末期疾病,充其量只能做到缓解而已──减缓病情恶化的速度和强度,减轻体能衰竭的程度,减少症状的数量和严重性。
为了平衡病患对自己身体已经无法控制的想法,安宁疗护团队会鼓励他们选择自己的药物和疗法,甚至决定自己想在哪里辞世。
由于拥有一些自主权,病患将可竭尽所能地享受其剩余时日。安适心灵,减缓苦痛安宁疗护中所谓的症状控制,是针对生理、心理、社会和灵性等四个层面,减轻痛苦并增加安适。
身体上的痛苦像酷刑一样难熬,但经审慎评估和有技巧的治疗后,往往是最容易控制的,例如疼痛可以缓解、恶心可以抑制、便秘可以改善;其他三个层面反而比较难处理,且牵涉到病患以外的其他人。
病痛会引发沮丧、愤怒、焦虑、恐惧,或任何一种因为死亡将至而产生的不适情绪。
病患要如何处理这些情绪呢?他需要什么协助呢?
疾病末期也会造成社交上的不顺,而伤害了病患与别人的关系。他的配偶或父母是否悲伤得几近崩溃?
孩子是否对于病患的改变,感到难过、生气或惊恐? 朋友是否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而避开了他? 病患或他的家人,是否感到被排斥或被遗弃呢?
灵性上的不适,是指凡人难免一死的事实,对病患和家属所造成的冲击。病患是否质疑自己的生命值不值得? 是否思考生命有何意义?
死亡又代表什么? 死后有另一段人生吗? 如果有,会是什么模样? 对于笃信宗教的人,可能会对上帝或所信奉的神明,产生许多疑问:“祂怎么能让这事发生在我和我家人身上? 祂为什么容许这样的痛苦?”同时开始怀疑这个在此之前都能带给他心灵慰藉的信仰。
生理上的不适比较好处理,另外三个层面的不适却不好处理。情绪上、社交上和灵性上的不适,非但微妙而难以辨识、修正,随着病患个性和家庭生活型态的不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医药已经是高度专业的技术,专精于身体的某个特定系统或某种疾病。但病患和家属是以整个复合体存在的,他们交互影响,一起奋斗,要闯出这个充满了痛苦和焦虑的迷宫。
想走出这个迷宫,需要投入大量的关切与意愿,去倾听与了解。临终者的沟通模式很不可思议,有时是很奇怪的方式,需要耐心与洞察力,才能解读这些透过动作、表情、寓意或符号所表达的讯息。
很不幸地,这些讯息屡屡被人遗漏或误解。经过研究,我们写下这本《最后的拥抱》,就是为了修正这些状况。
为“临死觉知”定名我们决定探讨“临死觉知”,起始于同事之间的一次午餐闲聊。这类闲聊经常聚焦在病患为了沟通做了多少努力,以及医疗人员多么难以理解这些混乱的讯息。
每个同事都能说出不同的故事,说病患为了突破某个点,做了好几次尝试;有一天,这些故事好像突然之间出现共通点了──它们有相通的语言模式或动作模式。
我们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倾听病患的那些似乎不相干的说法之后,决定做一些检视,发觉其中潜藏的重要讯息。
分析之下,发现那些主要的沟通模式当中,有着一再出现的主题,于是我们着手研究,最后累积了两百多个案例。
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寻找能够解释那些模式的相同元素。用这种语言沟通的病患是否都罹患相同或类似的疾病?
譬如特定的脑疾病、骨疾病,或因为肝、肾问题导致体内的化学物质失衡而影响知觉?
有没有哪位病患的脑部因缺氧一段时间而改变了意识? 行为上或心智上的改变,是否导因于体内的水分或盐分失衡?
这些病患是不是全都在使用药物(如止痛用的镇静剂),而模糊了他们的思考? 以上任一种因素,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病患做出“意识混乱”的沟通。
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相同的因素,导致我们看到或听到的状况。我们的病患罹患着不同的疾病──各种不同的癌症、不同的心脏或肺脏疾病、先天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爱滋病等。
部分案例中,病患的脑部氧气、体内水分、盐分指数都被记载为正常。他们使用的药物各式各样,有人根本没有用药,有人用很多药。总而言之,没有明显的生理特点能解释他们的沟通模式。
文化、性别、年龄、种族的差异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我们的病患包括各种年龄的男性和女性,来自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家。他们各有不同的宗教背景,有些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
然而每一个人都有话想说、有讯息想传达。我们检视愈多搜集到的资料,就愈兴奋,因为我们看出了那些讯息,主要可分成两种:
‧ 第一种讯息主要是在描述病患的经验:与某个过世的人同在一处;必须准备好去旅行或要改变了;提到某个只有他们能见到的地方;或提到他们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发生。
‧ 第二种讯息牵涉到某件事或某个人,他们需要完成它,才能安然辞世:他会要求你,帮他移除一些阻碍,好让他修复私人的、灵性上的、道德上的关系。
我们的收获愈来愈多,足以帮别人解读这些讯息,同时观察到这样的了解不只能帮助病患和家属,也能帮助专业的照护人员。
为这个理论命名是最难的。当病患愈来愈接近终点时,他们似乎对于人、地、物发展出独特的体会。
这种体会以缓慢渐进的方式形成,似乎是意识到现存的世界,又意识到自己飘向另一个世界,这种意识,随着病患愈接近死亡而愈强。最中心的三个关键字眼是觉知、临近和死亡,因此我们选定了名字:“临死觉知”。@(待续)
摘编自 《最后的拥抱:来自资深安宁护士、抚慰病患和家属的温暖叮咛》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