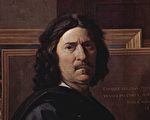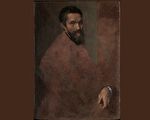呼吸著聖潔而又燦爛的光芒,在神聖的讚歎聲中,巴洛克的時代步入藝術的殿堂……
西洋繪畫
大瘟疫發生最令人恐懼的景象之一就是目睹人們大規模的死去,屍骨堆山,多得來不及清理,遺體不分貴賤地腐臭潰爛,悲慘景象就像人間地獄。凡是經歷過大瘟疫的倖存者必然會被這些恐怖的畫面深深烙印在腦海中。
在西方描寫瘟疫的繪畫作品中,以普桑的《阿什杜德瘟疫》最為著名,許多關於瘟疫的繪畫都以它為藍本或參考。
位在意大利佛羅倫斯的卡爾米聖母大殿(Santa Maria Carmine)內,這裡保存了文藝復興早期最重要的壁畫系列之一。它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題材,而是馬薩喬 (Masaccio,原名Tommaso di Ser Giovanni di Simone)使用了創新的壁畫技巧描繪聖彼得的故事。
柯爾生於英國卻是像早期典型的美國人自學而成,而英國成長的經歷與教養背景,給了科爾另一種視角。他的人物畫並不像學院派訓練出來的準確,但是風景畫卻能讓人屛息凝神,蕩氣迴腸。
今日頭條
NEWS
HEADLINES
4月6日上午10點15分,布碌崙班森賀華人社區發生一起駭人家庭暴力事件,一名男子疑似在精神失常情況下,手持沾血砍刀與菜刀刺傷四名年幼女孩,最終遭警方開槍擊中,目前情況危急。
排行榜
TOPARTI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