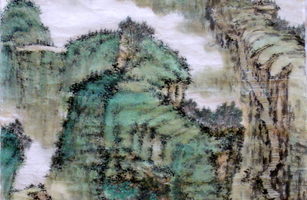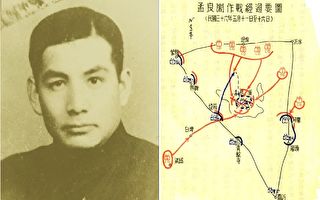白雲隻身一人飛往加拿大,開始了她人生中一段新的旅程。飛機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緩緩降落在溫哥華機場,在機場等待幾個小時之後,再轉機飛往多倫多。

現代中篇小說
白雲在少女時代喜歡看愛情小說,對完美的愛情和情人充滿著夢想,心中憧憬著那幸福的情感。想像中初戀的日子應該是甜蜜的,從未想到過自己初戀的日子並不像想像的那樣花前月下,海誓山盟。
二千年末,大法弟子正法的浪潮,風起雲湧。邪惡雖然非常猖狂,但是對於大法弟子能夠有這麼多人走出來證實大法,還是有些措手不及的。回頭看看,那時大法弟子對師父的講法確實有許多認識不清的地方。就拿那時的董嬙來說吧,對師父的經文“走向圓滿”,“理性”,“去掉最後的執著”等認識的就比較模糊。
那一年的暑假,白雲沒有回家,一方面是為了準備托福考試,另外一方面也是不太願意回到那片物是人非、充滿了傷感記憶的舊地去觸景傷情。剛一放假,白雲和一個同學一起去了長白山和內蒙的大草原,希望走到千里之外的天涯海角,能讓自己從往昔的記憶和心中的傷痛中解脫片刻。然而,面對似乎遠在天邊的美麗的天池水和遼闊的蒙古草原,白雲還是發現,哪怕是天涯海角,過去的記憶和心中的傷痛仍然是如影相隨,不經意間又會冒出來。
轉眼暑假也快結束了,慧清想乘著暑假期間把白光新的骨灰送回故鄉大理去。光新生前曾一直想回大理老家去看看,那裡還有他的一些親人。慧清也覺得故鄉那美麗的蒼山洱海之間,才能讓光新安息他的餘生。
思維也像是在穿越著遙遠的時空,周圍的一切,比方在眼前走過的人啊什麼的,雖然是剛剛發生過的事情,但是都給人一種非常遙遠漫長的感覺,好像已經發生了無數無數年一樣。
平生第一次品嘗到了那種生離死別的痛苦。看著由於操勞和傷心過度而一下顯得蒼老了十歲的媽媽,白雲突然感到生命原來是如此的脆弱和無奈,人們總是希望通過自我奮鬥來改變命運,可是命運卻是那麼的令人難以捉摸。
中學時候,白雲寫了一篇散文,題目為《星橋》,發表在當地的一個刊物上。表達心中對於現實世界人心冷漠、心與心之間的距離為何比天上的星星之間的距離還要遙遠的困惑,以及對理想中美好世界的嚮往,白雲願意做一個星與星之間和心與心之間的橋樑,縮短這個世界上人與人心之間的距離,熔化那份冷漠,憧憬著讓這個世界成為一個充滿了愛,坦誠,人人互相關心幫助的美好地方。
白雲小的時候最喜歡聽大人講故事;八仙過海的故事;人參娃娃、仙女下凡的故事等等。她最喜歡看那深藍的天空,浩潔的明月。在她幼小的腦海中常常在想:月亮上是否有奔月的嫦娥?遙遠的星空中是否有神仙世界?小小的心靈中充滿了幻想。
嚴冬的早晨,乾冷的空氣凜凜的。凌晨的霧,凝固成寒霜,掛在樹枝上、電線上、枯草枝上,撒在地上、牆上、屋頂上。冰冷的、光禿禿的樹枝外面,包掛上一層厚厚的白霜。所有的枝條都呈銀白色,霎時間,乾枯的樹枝換了一層銀裝,真是別樣景色。遠遠望去,美不勝收。
雖然白光新上中專時學習成績非常優異,總是班裡的第一名,可中專畢業時卻被分配到了邊遠地區工作。由於那裡的瘴氣很重,白光新經常下鄉工作,晚上常常睡在農家的牛棚上, 被成群的蚊子叮咬染上了嚴重的瘧疾。再加上貧困地區缺醫少藥,使得白光新落下了終身的病根,每到冬天和春季的時候,特別是新年就很容易發病。在白雲上小學前的那些年裡,慧清也不記得有多少個新年是她帶著小白雲在醫院裡照顧光新度過的。後來白光新從邊疆地區調到一個城市的一所中專教書。在這個期間,由於上級要點名批判當時的校長,出於良心,白光新和楊慧清兩口子沒有寫揭批校長的材料,因此被認定為“不與黨組織保持一致”,受到了長期的調查和壓制,到處去搜羅白光新的黑材料,本來就出身不好,再加上這麼一條,真可謂雪上加霜。
慧清和剛明在這兒上了小學和中學。初中畢業,剛滿十六歲的慧清參加了工作。不知不覺中,慧清已出落成一個水靈靈的大姑娘,這個在邊陲地區長大的姑娘,卻映育出故鄉大理那風花雪月的清美與嫵媚。瓜子臉,白淨細嫩的皮膚,高挺的鼻梁,明亮的雙眸,一頭濃密的黑髮梳理成一個大辮子,高高的個子挺拔俊俏。慧清的身材、容貌以及爲人、工作樣樣出衆,大家都喜歡跟她聊天交往。自然,她也成了許多小夥子追求的目標。
那段黑暗日子的記憶,秋雯不再願意觸及。特別是在邪惡鎮壓還沒有停止的今天。在他被非法關押的以後幾天,陸續又有幾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關進了他們監室,他們是“五十一”,“五十五”,“老仁義”幾位。監獄裡不成文的規矩,所有被關押者,都有綽號一類的稱呼。
楊之同在省城讀書時,結識了一個秀麗可人,聰慧伶俐的女孩子─段秋宜。段秋宜出生在省府的一座豪華宅院,段家是大理南詔古國段王爺的王族後裔。秋宜的父親段子越是講武堂出身的軍人,抗戰時期李宗仁手下的將領,台兒莊戰役中身負重傷,後被封為國民黨將軍。之後棄政從商,來往於香港和大陸之間,經營珠寶生意。
無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中白雪始終覆蓋蒼山之頂,如果從遠處眺望山峰,可見頂峰那瑩白的積雪,不禁令人神清氣爽。每當夏末初秋雨後初晴之時,又可見山腰的白雲漫舞,多姿多彩,宛若仙女的玉帶繚繞。
門口直接連著的是通長的木板鋪,剛探進上身,就聽見黑暗處那麼多喉嚨發出惡狠狠的、低沉的餓狼般的聲音,“爬、爬、爬!”爬過幾米長的板鋪,來到前面鐵窗前,才有機會抬頭看看周圍,“呃 -? 這麼多熟悉的面孔!好像在哪裡見過。”
其實,在秋雯、馮姐她們沒去北京上訪之前,穆姨和洋姐就到馮姐家裡去了一次,重點是交流如何走出來護法。這時穆姨和洋姐已經從監獄被放了出來,她們通過談自己在正法過程中的境界提高,來鼓勵那些在此問題上還悟不透的,還在觀望的同修。馮姐在猶豫,彩雲說自己沒路費錢,能湊夠路費就去。可能這次的交流對後來馮姐盡快走出來,起到了不小的促進作用。
講什麼呢?李璽有點為難。每次給他講從大法網站看到的故事,已經講了很多,而上次聰明說今後再講,請叔叔講自己身邊發生的修煉人的故事,平凡的也行,精彩的更好,離奇的最好。
擦地的時候,心中萬般難捨的感覺,和想到監獄這個字眼時帶來的恐怖壓力,真的是感到即害怕又痛苦。當擦地結束,決心已下,那些揪心的東西似乎也沒了。“不能退縮,不能成懦夫而被恥笑,在大法中受益,就要為大法仗義執言。”
瑟瑟深秋,穹空一抹濁黃籠罩著北京城。天安門廣場上劍拔弩張,持槍的綠衣武警,弄棒的黑衣警察,還有嗅著氣味逡巡的便衣;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密密麻麻,把天安門廣場管制得水泄不通。
夜,漆黑的夜,暴雨被狂風捲著,打著旋渦,擰著勁,在抽打一切地傾瀉。路,泥濘的路,水在地上流,坑在水下伏,每一步下去,都深淺莫測,每一步的拔起,都是緊咬牙關,泥濘中深深的腳窩,很快被雨水淹沒。這樣的雨,這般的夜,人們啊,在溫馨的夢鄉甜蜜著,在美酒桌旁歡樂著 ……
公元二零零零年深秋時節。華北平原上一個罕見的寒風陣陣陰霾沉沉的白晝。從烏縣公安局傳開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一位年輕女子在被審訊時從公安局六樓的窗口摔下來,當場死亡。公安局的人說是畏罪自殺。可是縣城裡的傳聞就不同了:“那女子死的太慘了,渾身都是血啊!……”“聽說被公安局審訊了兩天兩夜,打的都不會動了,哪裡還能跳樓?”“哪裡的女子?究竟犯了啥法啊?”“只聽說是個法輪功!去北京,被抓回來了。”“過去的皇帝還允許擊鼓鳴冤哩!”“上北京,不就是有冤去告狀麼?!”……
太陽黃黃,礦山的公路上行人稀少。葉少榮蹲在路邊的高坎子上,被深秋的太陽晒得懶洋洋的。他覺得這是個無聊的日子,大腦空空,什么作為和主意都被太陽晒跑了。他抬頭看看天,天藍得一塌糊涂連云都沒有一絲。這与他燥動、總有些事儿要做的性格不吻合。他無聊而又無奈地躺到草地上,用胳膊橫在臉上擋住天上的陽光。這是一九六九年的一段時光。
他們在救度眾生,他們在修煉自己,他們在播撒春天的種子,他們在成就宇宙的希望。可是這一切,在世間的表現,卻那麼的平靜,那麼的平凡,那麼的平常。大法弟子轟轟烈烈,史詩般的正法壯舉,而那匆匆忙碌的世人,卻全然不知。
氣溫不冷不熱。天湛藍的,雲雪白的。全無夏日的悶熱和煩躁,肆虐的風兒,還沒光顧。空氣爽爽的,陽光暖暖的,舉首四望,遠遠的。人們的著裝,更容易變換和搭配了,樸實化的,個性化的,入時化的,凸現魅力風採。
去過興城的人多半都要到菊花島走一圈,邊勇他們也不例外。普通的小島,散住著不多的人家,據蓄立為一個鄉。繞島走一周,也沒什麼特別的印象。碼頭上有賣螃蟹的,有賣紀念品的,如今也無非是個完全靠旅遊吃飯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