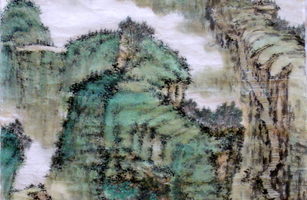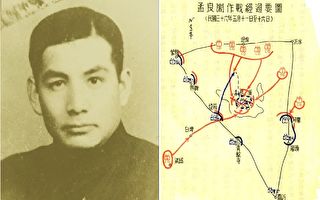那意思是什麼,所有的孔雀心照不宣——譯成鳥語就是:「而孔雀麼,又要在眾鳥之間勇奪桂冠。」貴族血統的孔雀懂得社交手腕,任何時候牠們決不在鳥手上落下把柄…

現代中篇小說
高山上,天帝布置下巨大的森林,那是鳥幽深而又輝煌的宮殿。樹是鳥的家園,所以樹冠豐滿,樹幹高入雲霄。廣大的風和雪是天帝遺留在鳥國的備忘錄,把遙遠帶到鳥的身邊,勾起牠們久遠以前的回憶……
第二天一早﹐立夏帶著明河去了徐州﹐拜訪李大學家。大學見到立夏父子﹐格外熱情﹐忙著沏茶倒水﹐安排飯菜。大學離開小湖﹐一直經商。公私合營時﹐將家產交了公﹐自己成了店員。他的三個子女﹐都已成家。
立夏在縣城工作﹐雖然幹部不大﹐供銷社主任﹐也有實權。他為人低調﹐沒有政敵。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在縣裡也吃得開﹐大小幹部及親朋好友﹐求他幫忙的不少。「文革」雖然受衝擊﹐主要是他出身問題及路線錯誤。是縣裡第一批解放的幹部。到了市場經濟時期﹐供銷係統不行了﹐他藉故身體不好﹐早早自動要求退養。
立冬回到小湖﹐正好趕上秋收﹐今年又是個大豐收。在立冬外出期間﹐小湖出現很大變化﹐首先是李子業承包了大湖供銷社﹐這原來是人人羨慕的單位﹐現在不行了。其次﹐糧店關門了﹐沒有人來這裡買賣糧食。
取消了糧﹑油﹑糖﹑布﹑肉五大票證﹐已經習慣使用票證的中國人﹐還有點不習慣。第一疑問是﹕「這是真的麼﹖」﹐害怕又一次上了「說大話的當」。倒霉的還是老百姓﹐悄悄地留著後手。
新年過後﹐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牛鬼蛇神走進「牛棚」﹐就是接受工農再教育﹐下鄉勞動改造。緊接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敲鑼打鼓奔向新疆﹑東北﹑雲南等邊遠地區。胡州回到小湖接受改造﹐他沒有了昔日的蠻橫﹐見人總是點頭哈腰。群眾看到胡州落魄樣子﹐又覺得很可憐。
「你們為什麼抓人﹖他開會發言﹐就是有錯也不能抓人﹗」小湖群眾因為李子義被抓﹐有二十幾人到公社講理。「他破壞大批判﹐攪亂會場。」黃金華解釋著。本來抓人是為了「殺雞給猴看」﹐不想會鬧出這麼大動靜。
剛剛平靜了一年﹐人們剛剛有了頓飽飯吃﹐醞釀災難的六四年﹐就匆匆而來。報紙開始批判「三自一包」﹐否定土地承包。批判「海瑞罷官」﹐說有人為彭德懷翻案。開始與蘇聯展開論戰﹐批判修正主義。
「我是從來沒有向你要過東西﹐這次不行了﹐過不去了。你姐一家四口﹐實在走頭無路﹐到了我家。我不能見死不救﹐只好收留他們﹐二人的飯六人吃﹐怎麼行。你再困難﹐也得支援一些。」爸爸說完﹐立夏一聲不響﹐坐在那裡。
這一天,潔梅與兒子告別,將明明抱在懷中:「明明,媽媽出一趟門,你跟爸爸在家,要乖,要聽話。想媽媽的時候就在心裏說一聲法輪大法好,或者真善忍,媽媽就知道了。」明明:「媽媽,你可快點回來,明明等著媽媽回來給明明唱歌。」
警察逼迫韻梅寫保證書。韻梅堅決不寫,並以絕食抗議。韻梅平和的對這個所的副所長說:「你迫害修煉人,其實就是迫害你自己。」副所長叫段淮綜,這時其呼機使勁的響了起來:「丈母娘病重,送醫院了,趕快去市第二醫院。」
李鈞看了看同屋的犯人,說:「你們知道麼?我進來前還是一個處長呢。」犯人們一聽,有幾個圍了過來。「我以前還曾經是一個重病號,看了多家醫院吃了很多藥,都沒好。後來煉了法輪功,沒花一分錢,身體全好了。很多的法輪功學員都有類似的經歷,你們說,這給國家節省了多少醫藥費。我們身體好了,痛苦沒了,你說我能不煉嗎?」
沂坊是膠東半島上的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南依山,北臨海,中部是一片遼闊的平原,自古以來名人輩出,民風淳樸,歷史上又是一個著名的手工業城市。當地的百姓,用各種帶有濃厚地方特色的傳統民間藝術,如泥塑、刺繡、年畫、風箏等等,將這個城市點綴得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