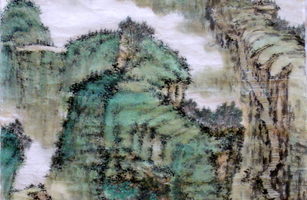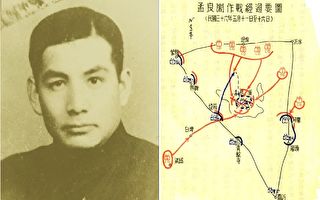我們告別了同學、班排長,坐上司務長去領給養的中型吉普,來到孟拱的美軍第三野戰醫院。我們將軍醫處的轉院許可證交給一位金髮碧眼的漂亮護士,她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將我們的名字,部隊的番號,登在本上後,就發給我們每人一套天藍色的病號穿的衣褲並帶領我們到外科手術室。

社會/紀實文學
南下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一列南下的火車載著萬念俱灰的柳在快速的行駛著,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一閃而過的景象始終沒有吸引她的地方。
列車已經進入南方的土地,比起北方肅殺的景色綠色漸漸多了起來,此時的柳腦海裡顯現的...
他告訴我,他不時會質疑自己的印度教信仰,但他也相信諸佛菩薩終有一天會還他一個公道,也就是讓我回來。我的歸來深深影響了他——或許這代表他心中長期的傷痛終於得以療癒,也有人一起分擔重擔了。
當地的新聞媒體聽說走失多年的小男孩已經長大成人,無預警地出現在加尼什塔萊街頭。地方媒體與國家媒體一同出現,電視臺攝影機在我家門前一字排開。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大部分都是透過翻譯,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