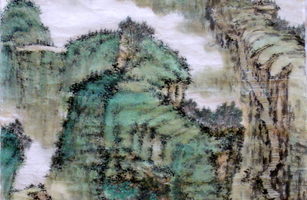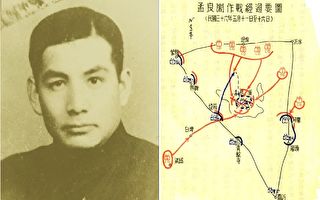立泰先到廠部,由廠部找到隊部,最後才找到我。對一個遠道而來的職工親屬,按照勞改單位的規矩,隊長必然要向他介紹我的情況,立泰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哥哥是這樣一個人!

社會/紀實文學
這些被政治運動迫害的難友們休假去沙灣趕集,路經磚瓦隊時,經常來找我玩,彼此談談心,我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患難朋友們都是舉目無親的光棍單身漢,見面時格外親切。我們互通訊息,各訴自己對形勢的看法,都盼望著黨早日給我們平反。
此時的二娥山區,正是寒風刺骨,雨雪交加嚴冬季節。白天,我帶領著大家冒著風雪嚴寒,在沒有人煙的荒山野嶺中挖礦石;晚上,工棚外山風吹得吱吱的響,棚內點著一盞昏暗的菜油燈,在遍地鋪滿了稻草的地鋪上,勞教分子們圍坐著開鬥爭會、或學習會、生活檢討會。
此時的我,再也不敢有1957年「反右」以前那樣認真而又剛直的個性了,不得不學會在所謂「好人」與「壞人」之間周旋,在人與人的利害關係中圓滑地求生存。我想,我的這種做法上帝也會原諒我,因為我的本性被暴力扭曲了。
從老家帶來的餅子,我在路上捨不得多吃,此時還剩下一點。餅子都長白毛了(黴變了)。看見餅子,又想起了山東老家,想起了我娘,還想起了臨別前的那天晚上,四叔背著我老祖母,到我家的炕上與我告別的情景……
這位跟著我四年,面容慈祥,心地善良的老保姆的形象立即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一陣心酸,幾乎流出眼淚。我長歎一聲,恐怕今後難以再見到她了。果然,1979年我冤案平反時,她已去世多年。
更可怕的是,在這個社會裏,一旦你被定為「階級敵人」,你就成了「人民公敵」,或者說成了「瘟神」,任何人,包括親戚朋友,都要躲著你,都必須同你「劃清界線」,否則就要受處罰。
這天夜裏,我第一次聽到地、富、反、壞、右聯在一起的「五類分子」的稱號,以前只叫四類分子,沒有把「右派」排進去。我從這些人的口裏知道,我已經被排在「五類分子」的行列中了,我已經成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敵對階級中的一分子了。
一天,全隊吃菜包子,在那個年代,這是個了不起的「享受」,黃隊長叫炊事員悄悄拿了三個大包子給我,叫我不要聲張,找個地方悄悄吃。我感到一股暖流湧向我全身,眼淚流下來。我趕快回宿舍蒙著被子吃完了這三個包子。這輩子我永遠忘不了黃隊長和三個菜包子。
我剛進集訓隊時,與剛進勞改營一樣,感到自己和這些人為伍,在人格上是對我極大的侮辱,大有無顏對天地祖宗之羞愧。不過,我想到歷史上那些忍辱負重的落難英雄,想到為了生存必須適應,想到忍受加上時間煎熬就是希望。
這些人(也包括我在內)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面黃肌瘦或黃腫爛胖,頭髮鬍子長得很長,兩眼癡呆無神,走路氣喘吁吁,衣服破爛不堪,滿身蝨子,老遠就傳來一股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