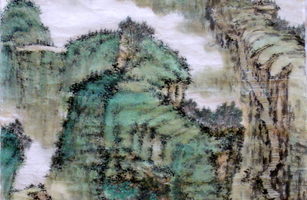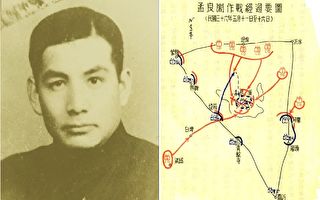看那很狹窄的店面裡,懸掛的竟是一些洗淨了的補巴衣服!這使我注意到了街上行人們的衣著,與三年前的解放服和中山裝為主體的衣著沒什麼區別,色彩依然的藍、灰、白,三種流行色。

社會/紀實文學
上午黨總支大會通過對我們三人57年的「右派」問題的決議,我們的「右派」是錯案,決定改正平反。他說,黨總支已電話報告了機械局,待春節以後向局補辦審批手續。
中共建國後毛澤東用「階級鬥爭」搞「政治運動」來治國,致使千千萬萬無辜者慘遭專政鎮壓,他們的親屬也遭到株連迫害。甚至把劉少奇也打成「階級敵人」被活活整死……毛用暴力治國(馬克思加秦始皇)是不得人心的。
在我心目中的毛澤東早已不1956年「八大」以前的那個毛澤東了。如果1957年還沒有看透他,那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人們應當看清楚了。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把整個國家弄到崩潰的邊緣,也是他的政治品德,思想靈魂的徹底大暴露之時,他已經成了國家和人民的罪人!
我想:難道千百萬革命烈士的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就是今天這個「秦皇封建社會」嗎?我暗暗驚喜,人民是不可欺的,「物極必反」,我要咬緊牙關,等到「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的那天到來。
不久,「批林整風」運動到來,階級鬥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原來的那些「牛鬼蛇神」根據政治需要一夜之間也變成了「林彪的社會基礎」,當然包括我也在內。
這時候各種各樣的人的靈魂,都徹底暴露無遺,利用「階級鬥爭」踏著別人的鮮血往上爬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趁機報仇者有之;為了保護自己,把別人當作犧牲品者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