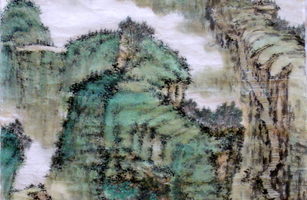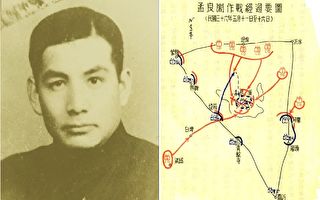兩個罐子就這麼並立在窗口上,直到晚上炊事員送來了晚飯,看到那窗台上早上和中午的飯菜紋絲不動原處擺著,而我卻仍躺在草堆裡面壁而臥。他喊了幾聲,我沒有應,於是他立刻抽轉身向隊部走去。

社會/紀實文學
對於傳統的優秀道德文化「以革命的名義」進行掃蕩、清除、滅絕。長驅直入的進行了幾十年。我們這些人首當其衝的成為了「思想改造」的對象。因為不僅要我們「換腦筋」,更要我們去驅使更多的更多更多的人群去「換腦筋」。我們的人性和人格首當其衝的受到了顛覆性的挑戰!
在當時的黨校、團校、革命大學、軍政大學、幹部學校……要進入革命隊伍,全都如此,無一例外。統統列入你的個人檔案。伴隨你一輩子。「疤疤」捏在「組織」手頭。「渾煮白切」只能夠「聽憑宰割」了!這些「原罪」列入了檔案。伴隨你的一生。
在「解放」初期,黨校、團校、幹校、革命大學……之類,學習期間書本、文件是很少的,作「報告」就是上大課,很有點「言傳身授」的味道,叫作發揚革命傳統,這些大首長來作的報告。我們都視之為真理。實際上是「洗腦」。
最根本的是毛澤東為了「推翻國民黨」而一手「策劃」。「運動」學生而發動起來的被扭曲了的運動。亦如「紅衛兵運動」一樣。是毛澤東為了把「黨天下」走向「家天下」,而把「紅衛兵」作為「炮彈」進行「清君側」的工具。都同樣是把千萬「無知」幼稚的青年人玩弄於其股掌之中!
對於這一事件,幾天之後,《川中晨報》報導稱之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因為在此之前,自貢市的學校一直風平浪靜、規規矩矩的,敢於像我們這樣罷課、鬧事確實是「破題兒第一遭」!所以被稱之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當然也只是「死水微瀾」,一個小小的前奏曲!
在幾十年之後,在那勿忘的蹉跎歲月裏,中華民族在饑餓中掙扎,餓死了四千多萬人,當我也嘗過了餓飯的滋味,患了中華民族流行病——水腫病。險些成為餓殍!在那「階級鬥爭天天講」,當我被打倒在地,還要被踏上無數隻齷齪的腳,人格掃地,無奈領略過了人間底層的諸多屈辱,看過了我的中華民族的兒女所受過的種種苦難,我才懂得了老舍悟出的那條真理是一條永恆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