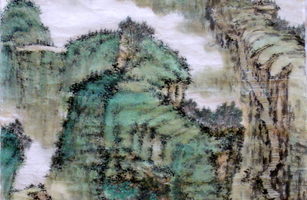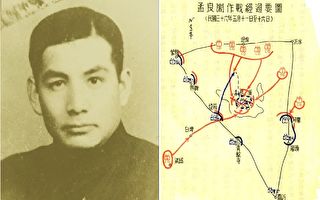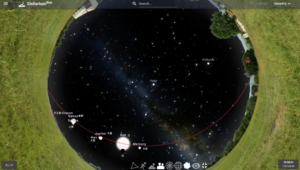又或者,人世間最情真意切的重逢,莫過於風雪夜歸人。大雪裡行路的人,走到天黑,才尋到那一戶人家。千里萬里投奔而來的激越情感,都在這大風大雪裡、寒夜風急裡,變得細小而具體。朔風暮色,又飄起了一點小雪,朱錦照例地裹在厚厚的長款羽絨大衣裡,頭上帶著絨線帽子,整個人裹起來,一路跑著,飛快地穿過石板巷落,經過城隍廟前那座長橋。

現代長篇小說
這是她的世界中最真切的事實。她愛他的一切:他的微笑、他睡夢中的喃喃自語、他打噴嚏後放聲大笑、他洗澡時大唱歌劇。
「夜鶯計畫」拯救了無數人,但挽不回生命。那些來不及解釋的歉疚,來不及道出的愛,與那個永遠不願掀開的祕密――塵封在閣樓置物箱的那張身分證,讓這一切重新翻湧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