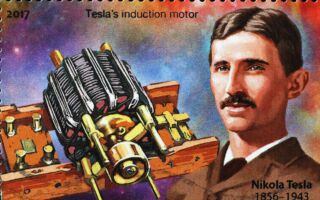第六章
「不過,貝吉多傑畢竟知道他要尋找什麼,我卻只知道自己缺少靈魂的歸宿,而不知道應當如何去尋找……。」珠牡無聲地自語道,厭惡地直視著眼前的黑暗,好像她心中的迷濛應當歸罪於這北京冬末的混濁的夜色。剛才飄過她意識的回憶,是發生在五年前。一九九二年的夏天,珠牡用重金買通了勞改營的警戒部門的頭兒,得到特許到勞改營中看望貝吉多傑。當時貝吉多傑也正巧因為抗拒「思想改造」,不肯按照官方要求詛咒流亡海外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而受到懲罰,被捆在峭壁下讓烈日暴曬,這樣她才獲得了與貝吉多傑單獨相見的機會。
對於珠牡,這個回憶是艱難的。艱難之處在於每一次回憶過後,她都會在銳利的痛苦中感到她與貝吉多傑之間的心靈的距離,那距離漫長得似乎用她的一生都無法丈量。不過這種感覺卻不能淡化她對貝吉多傑情感的依戀。相反,彷彿距離就是魅力,越是感到他們之間心靈的距離,她對貝吉多傑的依戀便越沉迷,就像是在柔情無限地遙望永遠不能忘卻的金色聖山。而且,她對貝吉多傑的感情此時已經不再只與她個人的命運有關了。奉獻給英雄人格的崇敬和對於真理的迷戀使那種感情變得更加豐饒,也更加高貴而悲愴。這種感情的變化則起步於一次事件,貝吉多傑就因為這次事件被關進勞改營,成為苦役犯。
一九八六年,胡耀邦在專制頑固派發動的一次小規模「宮廷政變」式的奪權活動中失去了權力。此後,儘管胡耀邦的宗教寬容政策還在慣性中滑行,但是,像傻兒子一樣對專制頑固派俯首帖耳的李鵬,卻已經開始利用剛得到手的職權,強化對西藏宗教活動的專制控制。就在這種背景下,珠牡的父親丹增班覺受當局之命,於一九八八年春陪同宗教歷史地位略低於達賴喇嘛的一個大活佛進藏,主持幾項宗教活動。經過幾十年時而冷酷摧殘時而溫情撫慰的、充滿詭詐政治權術的精神同化活動,共產黨官僚集團已經成功地利用人性的弱點,將這位大活佛訓練成一位能按照專制政治節奏翩翩起舞的宗教舞大師,而丹增班覺則早已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可以由當局任意擺放的政治花瓶。大活佛平時只能耽在北京,當局這次讓大活佛進藏,是為了利用他的宗教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在西藏的精神影響--共產黨官僚集團從精神上控制了大活佛後,就希望大活佛從精神上控制西藏僧侶和佛教信徒。
那時,珠牡已三年沒有見過貝吉多傑,得知父親要陪同大活佛去西藏主持哲蚌寺的祈禱大法會,對貝吉多傑的思念猶如突然爆發的壯麗的雪崩般不可遏制,於是她臨時決定隨父親一起到拉薩去。
到達拉薩的第二天早晨,珠牡便動身趕往色拉寺。因為,她已經得知,今天哲蚌寺的僧人要同色拉寺的僧人一起在色拉寺的辯經園內辯經。
辯經的地方在色拉寺主殿東邊的一個園子內。辯經園實際是一片白色圍牆圍起來的柳林。古柳粗糙的樹幹呈現出灰黑色,像是被歲月的艱難扭曲的生銹的鐵柱,樹幹上垂掛下來的柳枝則隨風搖曳,有一種超脫而飄逸的情調;陽光使柳樹翠綠的葉片上閃爍起怵目的銀火焰,地面上灰白色的碎石則被透過茂密的葉片灑下來的陽光鍍上凝重的銀灰色。
二百多名年輕僧人聚集在辯經園內,他們之中年齡小的只有十幾歲,年齡大的很少超過三十歲。他們身披的僧衣是深紅色的,那是一種很濃艷的色調,令人不禁想起盛放的玫瑰或燃燒的血跡。只有幾位如枯樹,如風蝕岩石的年老上師的僧衣是褐色或金色的。
珠牡趕到時辯經剛開始。此次辯經的主題是與龍樹菩薩所著的《中觀論》有關的內容。所有年輕的僧人分成兩人一組,一個專門進行答辯,另一個專門提出問題,進行詰難。答辯者盤膝坐在地上,詰難者則採取站立的姿勢。
走入辯經園柳林的綠蔭後,珠牡立刻感到熾烈的生命氣息迎面而來,而智慧碰撞中迸濺出的蓬勃生機像燃燒的美酒一樣令她沉醉。做為答辯者的盤膝而坐的僧人,有的瞑目端坐,披著僧衣的身體如裸露出地面的深紅色岩石般結實,只用從緊閉的雙唇迸濺出的簡短詞語反擊詰難者;有的苦惱地用雙手捧住自己的頭顱,額頭上現出道道土稜般的皺紋,苦思冥想該如何答辯;有的眼睛裡閃爍著狡黠的光亮,斜視站立在自己面前滔滔不絕地提出問題的詰難者,並準備以一個簡捷的反問使對手的問題崩潰,而他的樣子就像一個躲在在草叢深處的狐狸,隨時準備竄躍而起,攫取從草梢上飛過的鳥;有的則在對手一連串難題的攻擊下,露出痛苦欲絕的神情,而身軀像暴風雨中的樹一樣劇烈搖晃。
做為詰難一方的僧人,一邊以高山陡坡滾落而下的巨石般的語調,提出問題,一邊手舞足蹈地圍繞坐在地上的答辯者快步行走。他們幾乎都是狂呼怒喝似地提問,而他們身體的姿態卻又風格各異:有的舞動手臂,像是一隻從高空俯衝而下,撲擊獵物的鷹,要用鐵翅擊碎答辯者的頭顱;有的因為對手沒有能立刻回答自己的難題,而得意得猶如迎風展翅起舞的醉鶴;有的漲紅的脖頸上隆起道道青筋,深深彎下腰,焦灼地將頭顱垂到盤膝端坐的對手面前,乞盼地瞪視著對手的眼睛,同時痙攣的雙手手指鐵鉤般地撕扯自己的胸膛,似乎是試圖把自己心掏出來給對手看,以使他弄清楚自己的問題的真正含義;有的則由於體味到了自己提出的難題中蘊涵的智慧,而昂首向天狂笑,宛似一隻痛飲了烈酒的花斑豹。
珠牡面頰邊飄浮著沉迷的微笑,漫步在兩百多名辯經的僧人中間,而她心中動盪著明麗的民族自豪感--為這些雕刻著雄性之美的年輕生命在人性普遍物化的時代還能熱烈地沉醉於精神而自豪;為自己的民族宗教在古老的歲月中就創造出了辯經這種極具精神自由魅力的學術研究方式而自豪。然而,自豪的後面她卻觸摸到了堅硬的遺憾,並有些迷惘地想:「辯經的主題還是千年之前結出的精神果實,什麼時候,這些年輕的生命才能以這種自由的方式討論現代的思想課題?」
珠牡一直沒有用目光尋找貝吉多傑,她畏懼自己的目光同他的面容猝然相遇的時刻,她怕那一瞬間,她的情感會難以抑制地趨向瘋狂的極致,從而褻瀆了這精神聖地。可是,已經在辯經的僧人中漫步了許久,卻還是沒有發現貝吉多傑,這又使珠牡不安了--她畏懼與貝吉多傑相遇的瞬間,但又刻骨銘心地思念他,日夜都期待與他相見。
珠牡的目光一次比一次焦灼地從每一個僧人臉上掠過,她眼睛裡失望的陰影卻越來越沉重了。就在珠牡絕望地想要放棄尋找時,在一個下意識的回顧中,她卻看到了端坐在辯經園一個角落中的貝吉多傑。儘管驀然湧出的淚水很快模糊了她的視野,但在短暫的第一個注視中,她已經看清了貝吉多傑的面容,看清了他面容上的那道可怕的刀痕。
「不能說那刀痕使他更英俊,但確實使他的面容更生動,更剛毅。噢,還有一種動人心魄的悲愴意味……。」珠牡迷亂地想,而她的心沉浸在又苦又甜的感覺中。等擺脫了最初的眩暈之後,珠牡慢步向貝吉多傑走去,這時她才注意到,貝吉多傑是一個人坐在那裡冥想,沒有人同他辯論。於是,珠牡向一位身穿金黃僧衣、指導辯經的上師問這是為什麼。而那位上師回答的聲音像是綻出翠綠苞芽的鐵黑色枯枝,顯得既乾枯、又清新:「他也在辯經--同自己的心在辯。」
珠牡面對閉目冥想的貝吉多傑坐下,她那由於長久的思念而顯得憔悴的目光,猶如屬於高山之巔的淡紫色晚霞,飄落在貝吉多傑的面容上,沉迷地審視他與自己的心的辯論。
貝吉多傑的面容上覆蓋著燦爛的寧靜,這使他頗具雄性高貴感的頭顱猶如在夕照中變成金色的聖山一樣,呈現出輝煌的莊嚴肅穆,而他唇邊青銅色的微笑給人以堅硬、剛烈的沉醉感。珠牡覺得此刻的貝吉多傑美極了,那是在燦爛的寧靜中巍峨崛起的大勇敢的雄性之美,那是凜然不可犯的高貴之美,任何物慾的誘惑都不能污染他,任何暴力都不能屈服他。然而珠牡只能滿含晶藍的淚水欣賞他輝煌的美,因為,她知道那美不屬於她而屬於他所理解的真理。
突然,--事先沒有任何徵兆地,貝吉多傑的身軀劇烈震撼了一下,他面容上燦爛的寧靜於瞬間之內就崩潰了,破碎了。他的臉色呈現出死屍似地青灰色,頰邊的肌肉彷彿忍受焚身的痛苦般抽搐起來,而那道縱貫面容的紫紅色刀痕宛似要從形態猙獰的黑雲中躍出的雷電。
「烈火……!」一聲猶如受傷的猛獸發出悲憤的吼嘯,隨著猩紅色的血霧,從貝吉多傑岩石裂縫似的嘴唇間噴濺而出,「黑紅色的火……像牲畜一樣在火中交配……在聖潔的甘丹寺前--噢,--我是使聖地蒙羞的生命……噢,黑紅色的火焰,燒得我眼睛疼,燒得我心疼……。」
貝吉多傑下意識中說出的話被他自己的一聲聲短促的慘號撕碎了,但是,珠牡仍然毫無疑義地確信自己理解了貝吉多傑話語的含義,明白了是什麼使貝吉多傑痛苦如狂。她失魂落魄地自語道:「貝吉多傑,--此刻,他一定又看到了甘丹寺前的那塊裸露出地面的岩石,他的父母就是被迫在那塊寬闊的岩石上公開性交的。那裂開巨大縫隙的、深紅的岩石真像一團被狂風吹裂的火焰,堅硬的火焰……。」
貝吉多傑的身體痛苦地震顫著,他的神情變得更獰厲可怖了。突然,他悲痛地責問蒼天般仰起頭顱,話語像是猩紅的血跡,從他野獸一樣潔白的緊咬的牙齒間迸出:「產生於罪惡的生命還能夠成為大慈大悲大勇嗎?!……黑紅色的火,你能把我的心燒裂,為什麼不能燒焦我的心?!--你把我心中的驕傲燒成灰燼,我的心就不再疼了……。」
貝吉多傑的話語最後變成了就要窒息的嗚咽。珠牡想為貝吉多傑放聲悲哭,可是,她發現自己心底裡只伸展著荒涼的沙漠,沒有淚水的源泉。注視著貝吉多傑的痛苦卻不能為他做點什麼,這使珠牡幾乎要將自己的雙目挖出。在一陣瘋狂的衝動中,她迅速抽出腰際的袖珍藏刀,殘酷地在自己的手臂上切割起來--她所能做的只是陪伴貝吉多傑痛苦。
貝吉多傑清秀的鼻翼像野獸似的敏感地翕動了一下,他的眼睛突然睜開了,而那雙燃燒著痛苦的黑火焰的眼睛,立刻被身前地面上的血跡誘惑了--那血跡是從珠牡手臂的刀傷中湧出的。這時,一塊血流濺落在上面的石頭竟然裂開了,不知是被珠牡灼熱的血燙裂的,還是被貝吉多傑眼睛中熾烈的痛苦燒裂的,或者是被透過柳枝的間隙照射進來的陽光曬裂的。
貝吉多傑猙獰地瞪視著血跡,身體彷彿被陡峭而沉重的蒼穹壓迫著,慢慢俯向地面,俯向那片將石塊燒裂的艷紅如火的血跡。終於,貝吉多傑的嘴唇艱難地親吻在血跡上,就像親吻了一片美麗而妖冶的誘惑。
這樣過了片刻,貝吉多傑身體痛苦的震顫消失了。這時,珠牡聽到貝吉多傑胸膛裡傳出低沉但卻格外清晰的聲音:「……染就是淨,淨就是染……。」她知道,這是密宗經典中的一句話--她的父親就經常在沒有外人時低誦這句話。
等到貝吉多傑的身體重新緩緩挺直時,他的眼睛又閉上了,臉上獰厲可怖的神情也被疲倦的寧靜抹去,只是臉色還是青灰色的。他雙唇輕輕翕動著,吐出一句話:「用罪孽的火熔鑄出清淨無垢的佛性。」隨後,一個荒涼、沉寂的微笑飄拂在他的唇邊。
珠牡從來不敢對佛教稍有不敬,不過,她也無法迫使自己相信,密宗經典中那麼一句話就能使貝吉多傑免於痛苦,而且,她隱隱覺得什麼也不能消除貝吉多傑的痛苦,因為,那痛苦是刻在他的命運上的,是刻在他的心上的,甚至讓生命平靜地消逝於死亡,那痛苦也不會凋殘--唯有艷紅雷電般震撼人心的死亡,或許才能擊碎那猙獰的痛苦。
珠牡放下衣袖,遮住被自己的血洗過的手臂,而她的思緒猶如雪峰上被風撩動的雲縷一樣紛亂:「與他的命運之源相連的痛苦一定時常像今天這樣折磨他,他只能靠野犛牛白骨般堅硬的意志與痛苦搏鬥。噢,我高貴的貝吉多傑哥哥,我驕傲的貝吉多傑哥哥……今天,他是為了讓我不再用刀割自己,才逃離了與痛苦的搏鬥。要不然,他寧靜的神情不會是青灰色的,他的微笑也不會如此荒涼……他親吻了我的血跡,但卻不肯親吻我。因為,我曾拒絕了他對我的心的要求,而這侮辱了他高傲的心。可是,……。」
這時,貝吉多傑睜開眼睛,寧靜地望著珠牡,那是漫天黃葉在蒼白的秋風中飄落的寧靜。過了片刻,貝吉多傑聲音艱澀地說:「媽媽在送我當僧人前告訴我,英俊的男人只能給女人悲哀--如果他靈魂卑陋,就會帶給女人恥辱的痛苦;如果他靈魂聖潔,就會帶給女人高貴的痛苦,因為,要保持心靈的聖潔,他必須選擇人世間最艱難、最痛苦的命運之路……媽媽她還說我太美了,是女人的災難;我進入寺院,遠離女人,就是一種慈悲--對於可能愛上我的許多女人來說,是大慈悲。當時,我沒有聽媽媽的話,想要你同我到藏北無人區去,去尋找荒野中的自由命運。但那是罪過。」
說完,貝吉多傑站了起來,轉身離去。珠牡隨之站起來,並伸出手臂,緊緊抓住貝吉多傑僧袍的一角,聲音中閃爍著瑩澈的淚影,說:「我需要高貴的痛苦,否則,我會死於麻木,死於庸俗!」
貝吉多傑的腳步停下了,冷峻地沉默了片刻之後,他從僧袍下抽出一柄藏刀,像割裂深紅的火焰似的,割下珠牡握住的那角僧袍,冷漠地說:「我的痛苦與罪孽相連。你到別的靈魂中去尋找高貴的痛苦吧。」
@(待續)
(節自《金色的聖山》第六章)
※文章由博大出版社授權大紀元首發,歡迎轉載,請標註轉載自大紀元※
◎有興趣購買此書的讀者請向博大書局購買
訂購電話:1-888-268-2698
網上訂購:www.broadbook.com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