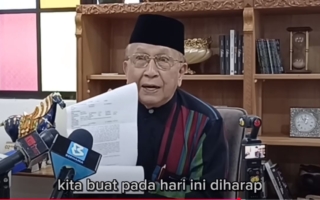疼痛是普遍存在的,但我們並不都以相同的方式體驗它。
1980年,學界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的一項經典研究發表後,對這一現象又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研究人員讓習慣於將重物搬運上喜馬拉雅山坡的尼泊爾搬運工評估他們感受到的電擊痛苦程度。當他們的回答與參加同一行程的徒步旅行的西方人的反應進行比較時,搬運工報告他們的痛感比對應的西方人要輕得多。
然而,兩組人對疼痛刺激表現出相同的神經反應——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如何感知這種疼痛。
該項研究的作者將疼痛敏感度的差異歸因於「文化性堅忍主義」,並指出搬運工的佛教精神修煉或許是一個重要的調節因素。
正念——尼泊爾搬運工佛教精神傳統的關鍵組成部分——是「通過有意識地、在當下時刻、非評判性地關注經驗的逐刻展開而產生的覺知」。過去幾十年來,科學界對正念實踐的興趣日益增加,這使得研究人員對正念如何改變大腦對疼痛反應的機制有了更多的了解。
解開自我與痛苦的糾纏
一項發表在《疼痛》(Pain)期刊上的調查揭示了一個與上述觀察一致的發現。
研究人員要求兩組參與者在聆聽引導式正念冥想或中性有聲讀物前後,對熱刺激的痛感強度進行評估。其中正念組的參與者報告的痛感強度顯著較低。
最關鍵的是,根據磁共振成像的分析,正念組在疼痛處理中心與楔前葉及腹內側前額葉皮層之間的連接減少了——而這些大腦區域與自我的建構和維持有關。
作者指出,正念冥想的鎮痛效果部分來源於「分離」我們的自我意識與外來疼痛刺激之間的神經連接。換句話說,正念冥想通過將我們的疼痛體驗與自我認同分離來發揮作用。
想像一下站得離火很近,然後退後幾步。你仍然會感受到熱,但感覺已沒有那麼強烈。正念可以訓練我們的大腦,在疼痛與自我之間建立一定的距離。
著名的正念導師、公眾演講者和作家巴恩特‧薩蘭帕拉(Bhante Saranapala)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表示,正念冥想有助於我們將持久的自我感與短暫現象區分開來。
他說:「冥想的作用在於,它會幫助我們放下我們所執著的東西。假若你能夠放下你的痛苦,那麼這种放下就是帶來緩解的過程。」
《疼痛》期刊中報告的研究結果表明了「放下」不僅僅是空想,而是已經在神經層面上被編碼,進而導致大腦發生持久的生理變化。
這些變化似乎會隨著練習的深入而加深。以往的研究發現,經驗更豐富的正念練習者相較經驗較少者,其大腦中涉及疼痛處理跟自我意識的區域之間連接更少。
如何練習正念
自1980年尼泊爾搬運工的相關研究以來,大腦掃描技術的進步使得研究人員能夠實時了解正念是如何工作的,同時練習者也能夠洞察他們在正念實踐時大腦的活動。
埃利沙‧戈爾德斯坦(Elisha Goldstein),臨床心理學家、作家和一家基於正念的治療輔導全球項目創始人,將正念視為一項可以學習的技能。
「如同任何事情一樣,當你有意識地進行練習並重複時,大腦就可以開始記住它。」他向《大紀元時報》表示。
即便是簡短的正念練習也能對我們的正念傾向產生持久的影響。一組研究人員發現,僅僅三到四次每次20分鐘的正念練習,就能使人們的正念傾向平均提高13%,進而導致痛感知覺的持續減少以及神經層面的重塑。
正念的核心組成之一即是專注於呼吸——薩蘭帕拉稱之為「呼吸的藝術」。
「我總是鼓勵人們像海豚一樣呼吸。」他說,「每當海豚面臨不利情況時,它會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氣,然後放鬆。通過這种放鬆,它重新回到不利的境況,並幫助其它同伴。」
根據戈爾德斯坦的說法,對呼吸的關注讓我們扎根於某種永恆的事物。
「通過正念呼吸,你會意識到你的身體變得穩定,心境變得平和與寧靜。正是這種寧靜,正是這種穩定,正是這種身心上的放鬆,帶來了治癒。」
他建議先以可實現的目標開始練習。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每天可以做10分鐘,我會告訴他們從5分鐘開始。這裡的關鍵在於堅持下去。我們想確保它感覺是可行的,這樣我們才能在一週內堅持下去。」戈爾德斯坦說道。
他的方法之一是將正念與其它事務結合起來。
「有時候,在送孩子們到某個地方時,我可能會在車裡停下來幾分鐘,進行實際的正念練習,亦或是在我還沒坐到電腦前時,我也常常會花一點時間練習。」戈爾德斯坦提到。
他還建議加入一個有老師及社區的組織項目,認為這是將這些實踐融入生活並促進學習的最佳方式。
現代神經科學幫助我們理解,尼泊爾搬運工所表現出的耐痛力是一種精神狀態,如果加以培養,它有潛力重塑我們的腦神經,從而進一步將我們與痛苦相隔離。
「痛苦本身是無常的,且不在我的控制之內」,薩蘭帕拉說道,「凡是不受我控制的,就不屬於我。凡是不屬於我的東西——我就必須放手。」◇
英文報導請見英文《大紀元時報》:How Mindfulness Disconnects Our Sense of Self From Our Feelings of Pain。
身處紛亂之世,心存健康之道,就看健康1+1!
責任編輯: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