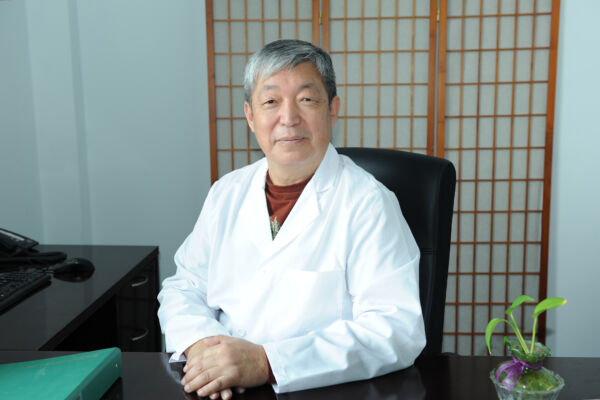【大紀元2025年03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陶靜慈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出身名醫世家的楊醫生(Garry Yang)雖得家傳絕學,卻憧憬實證科學。後來,他在人生經歷中感受到中醫的珍貴,治好了很多醫院治不好的疑難病人。
他是如何完成從低估中醫到珍視中醫的轉變呢?
名醫世家的傳承
楊醫生的祖上是從山東遷入東北的,那時候東北有一家與北京同仁堂齊名的藥房,叫世一堂。這家藥房早在中華民國時期的1915年就曾獲得過巴拿馬博覽會金獎,因此也有「外有世一,內有同仁」之說。而楊家從清代開始,好幾代人都是在世一堂中坐診的名醫。
能夠世代承襲醫術並成為名醫,他們是如何將自己的祖傳醫術傳承下來的呢?楊醫生說那就是紮紮實實打基礎。
楊醫生回憶說,那時候,他的爺爺除了到世一堂坐診外,他們家還有一個自家的小診所藥房。當年,他就是在那裡每天跟著爺爺學醫。他說:「小時候也不知道是學(中醫),反正就是跟他亂比劃。」
爺爺最開始讓楊醫生背《藥性賦》,將每一味藥的藥性熟記於心。這樣,就不用像其他的醫學生那樣去背那些海量的藥方了。
楊醫生解釋說,比如像《傷寒雜病論》(包括《傷寒論》及《金匱要略》)裡有三百多個方子,但他家的祖先中已經有人把那這些藥方結構的精華抽了出來,變成了一個方子,比如說治肺,就把《藥性賦》中治肺的藥往那個方子裡一帶,就是《傷寒論》中治肺的方子,這樣就省下了背《湯譜(頭)歌》的功夫。當然前提是你得對每味藥的藥性非常熟悉。
除此之外,楊醫生還跟著爺爺認藥、製藥,認識身體上的穴位,因為這些是基礎中的基礎。
之後,爺爺就開始教他研究《傷寒雜病論》的方子,每一條都要認真研究,看人家是怎麼用藥的。
然後,楊醫生還要學中醫的各種辨證方法,因為那是治療的前提和依據。
由於中西醫的理論體系不同,西醫對疾病的認識是基於人體解剖學、病理及生理學,強調對人體結構和功能的具體分析,靠病人自己感受到的症狀、各種檢查、化驗等指標來診斷疾病。
而中醫認為疾病是人體陰陽是否平衡的結果,基於陰陽五行、藏像學說等理論,強調人體的整體性和與自然環境的協調。診斷方法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辨證施治,注重個體差異。根據症狀和體征(舌象、脈象等),分析歸納成為比症狀更能說明疾病本質的概念。這就是中醫講的「辨證」的過程。
憧憬實證科學 不識中醫珍貴
雖然爺爺一直在刻意教授,但楊醫生自己只覺得跟著爺爺「亂比劃」是件很開心的事,並沒把它當成是學習。而楊醫生的媽媽是西醫,很看不上中醫。中醫注重整體觀和個體化,而西醫更強調科學驗證和標準化。受到媽媽的影響,楊醫生在上大學選專業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醫生這條路,覺的學醫沒有什麼用,不如做個工程師,可以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
為了逃避家族傳承的責任,楊醫生大學畢業之後不久,就來到了加拿大。他說:「那時候不知道中醫的珍貴。」
西醫治不好的感冒 楊醫生隨手就治好
剛到加拿大不久,楊醫生發現同宿舍裡的一個朋友老是感冒,反反覆覆怎麼都治不好。楊醫生為朋友著急,最後實在忍不了了,就跟朋友說自己有個方子,要不要試一試?朋友照著楊醫生的方子去抓了三副藥,只吃了一副就完全好了。
朋友非常驚喜,說:「看不出來你還會這個(中醫)。」還到處跟他的朋友說。結果,楊醫生會中醫,而且還治好了其他醫生看不好的病這信息就在朋友圈中不脛而走。
西人患病要被截肢 楊醫生救下他的腿
楊醫生有個鄰居,是一位三十多歲的西人男子,有一段時間這人每天晚上都哭。一個大男人天天哭,楊醫生就關心地去問了問。那個鄰居說,他得了脈管炎,然後就把褲管拉開,楊醫生看到他的腿上有一條紅線,一直從大腿根延展到腳趾頭,腿又燒又痛,很硬,走不動路。醫生建議他盡快截肢,因為脈管炎有毒,如果毒性通過血液到達心臟就會出大麻煩。
楊醫生很想幫他,但又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中醫。就說,你要是相信中國的中醫,可以試試,如果用中醫去治的話,是絕對不會截肢的。沒想到楊醫生只講了幾句,這位鄰居就相信了,說要試試。楊醫生以前雖然沒有治過脈管炎,但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一看就知道是熱毒。所以楊醫生就給他開了三副去熱毒的藥。
第一天吃了藥之後,這個鄰居的腿就感覺涼了,疼痛也減輕了很多。第二天他腿上的紅線就基本看不出來了,鄰居高興得不得了。三副藥之後,他就去醫院做檢查。原來他是需要拄著枴杖才能走路的,但這次他已經不用枴杖了,自己走路去了醫院。檢查之後,醫生很驚奇地說,你這個病好得很快啊,現在可以考慮不用截肢了,但要再觀察一下。之後的一個星期,他一天比一天好,最後還去上班了。當然,他沒有截肢。
病好之後,這位鄰居對楊醫生更是感激,不久,他介紹了幾位朋友來找楊醫生看病,這些人也都說楊醫生治病效果很好,他們又各自推薦自己的朋友來找楊醫生。就這樣,楊醫生的病人就像滾雪球似地在增長。因為這位鄰居介紹了很多糖尿病、高血壓患者,又總是楊醫生幫他們去抓藥,以致於唐人街中藥鋪老闆一個勁地建議楊醫生到他店裡來坐診,專治糖尿病、高血壓。但儘管如此,楊醫生仍然沒有想要真正當個醫生。
從不識珠玉到發現中醫之奧妙
楊醫生是學機械的,當時八十年代,加拿大經濟很差,學機械的都找不到工作,所以一群學機械的學者們就商量開個餐館,於是楊醫生也離開了魁省和他們一起到薩省去開餐館。
後來同事中有人患感冒,甚至燒到40度以上,怎麼治也退不了燒,楊醫生三下五除二就治好了,這下大家又開始傳了,說他的感冒藥靈,到醫院退不了的燒,吃了他的藥就能退燒。
還有一個十幾歲的西人男孩,差不多每個星期不落地患感冒,鼻子上永遠掛著鼻涕。楊醫生把他治好了,以後就基本上不再感冒。孩子的媽媽是一個作家,作為西人,她一直很自豪地認為高科技的西藥要比中藥好很多。而讓她困惑的是,兒子的感冒,西醫一直治不好,中醫怎麼輕輕鬆松就治好了呢?這讓她大感驚奇,也因此開始了解中醫,並成為中醫的鐵粉,甚至寫了很多文章去提倡中藥,質疑西藥。
這件事也讓楊醫生認識到中醫並不像自己過去認為的那麼簡單,他說:「這對我觸動也很大,這麼小的事,它(西醫)怎麼搞得這麼複雜。」
特別是後來,又有幾位廚師因為長期在高溫的火爐邊,也得了脈管炎。西醫也都是要他們截肢。楊醫生再度運用自己所學無一例外地將他們治好了,避免了他們被截肢的命運。
楊醫生:中醫勝在激發人體免疫力
楊醫生過去受母親影響,總覺得西醫比中醫先進,他說:「尤其在我還是小孩的時候,因為我們中藥要吃一大包嘛,西醫有一小粒藥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反正還是對西醫有點崇拜。」
但這些事一樁樁一件件的,都在衝擊著楊醫生的認知,他就想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西醫就是治不好呢?就非得弄到讓人截肢呢?帶著這樣的疑問,楊醫生開始認真研究中西醫的區別。
他說:「現在我就比較清楚一點,因為西醫就是打抗菌素到脈管裡。抗菌素,它一般都是在分子層面起作用,但這種病毒它一般都在原子層面,而在原子層面,西醫就特別弱。」
而中醫並不是針對表面的病毒去治療,「它(中醫)激發人體的免疫功能來抗病」,楊醫生說,「免疫功能是什麼層次都有的,分子層次、原子層次、更低的層次它都有,因為整個人體各個層次都有免疫功能。」
就這樣,楊醫生不僅會治病而且醫術高明的消息,再次快速發酵。於是,有人得了高血壓、糖尿病,來找楊醫生看;中風後遺症來找楊醫生看;得了不孕不育的也來找楊醫生看;得了很嚴重的腎炎,全身嚴重浮腫來找楊醫生;還有很多華人女性一到加拿大就絕經,也來找楊醫生。大家慢慢發現,只要楊醫生接手,就能藥到病除。於是,他的名聲傳得更快了。
而這些親身經歷越多,楊醫生就越能體會到中醫的珍貴,以及為病人解除病痛時的開心。
用祖傳醫術開診所救病患
當這一切累積起來之後,楊醫生就動了要自己開個診所的念頭。因為畢竟以前的很多病人其實都是親朋好友,也不好意思推脫。
那時候加拿大經濟好轉,他已經找到了自己本專業的工作。於是他就想利用週末的時間開兩天,不做廣告,知道的就來,這樣,親朋好友能照顧到,兩天應該也能應付過去。
儘管沒做任何宣傳,真做起來的時候,楊醫生覺的還是難以應付。因此,一般的小病,看不過來就推出去,因為別的醫生也能治好。最後楊醫生就好像是只治疑難病的醫生了。楊醫生無奈地跟大紀元記者解釋說其實開始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想法,但病人大多都是一坐下來就開始說,找了這個醫生、那個醫生了,西醫也看過了,不行。
他說:「他們都是一來跟我就是伸手(讓搭脈),然後就說我這個病找誰看過,不行。我一聽,那就沒辦法推了,這個習慣就這樣養成了。」
現代中醫與傳統中醫的差異
楊醫生並不是從中醫學院出來的,但他的醫術卻超過了許多正式中醫學院畢業的醫生,這是為什麼呢?楊醫生告訴大紀元記者說,真正從醫之後,他也學習了現代的中醫,但他發現現代的中醫和自己當年學的中醫有很大不同,其中以各種辨證最為顯著。比如,被視為中醫臨床診斷的重要方法的八綱辨證中,陰陽兩綱,每一綱裡都有表、裡、虛、實、寒、熱。但現代的中醫不太講陰陽,也就是只講了陽綱裡的表、裡、虛、實、寒、熱,而把陰綱裡的表、裡、虛、實、寒、熱給丟了。
他說:「所以在診病的時候,起碼缺少了一半的信息,那你診病的準確度就下降了,這就是我們現代中醫比較悲哀的地方。」
楊醫生說他後來發現在現代中醫裡這種不見了一半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臟腑辨證,就少了腑的辨證。但腑的辨證其實是比臟的辨證更重要,楊醫生回憶當年學習的時候,僅小腸(六腑中的一腑)的辨證就學了一年。
他解釋說,因為腑為表,臟為裡。病來時從表到裡,病去時從裡到表,病從這兒進,也從這兒出。
他說:「你不研究腑的話,那你就把關鍵東西丟了。」
大紀元記者問楊醫生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楊醫生沒有正面回答,但說了一個現象。他說他的爺爺當年有很多學生,但只有那些道德品質特別好的,非常孝順的,才會把所有的東西傳給他,其他的學生就只教一部分。
而中共建政後,許多真正醫術高明的醫生不是被迫害致死就是被冷藏。比如在「文革與當代史研究網」上就列出了36名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醫藥界著名專家學者。而楊醫生的爺爺在1949年之後也被打成地主,不再執業,最後鬱鬱而終。
回憶當年跟著爺爺學習醫術的日子,楊醫生感慨於雖然沒有像學校裡那樣正正規規的上課,但學的東西卻非常的紮實。
楊醫生說:「把這些基本功打紮實了,看病就很輕鬆了。」◇
責任編輯: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