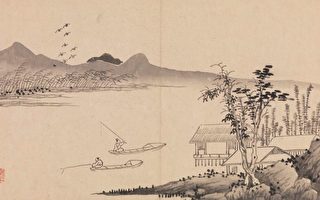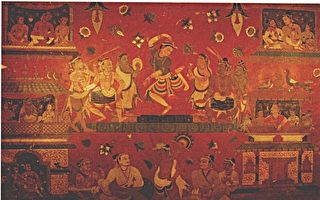元代文人,除少數名臣作過散曲外,大抵是布衣、府吏之類。而元初有位文人,自是名門貴公子,更有在朝堂平步青雲的捷徑。然而就是這麼一位名流,卻自甘「沉淪」,終生不入仕途,還投身秦樓楚館,陶醉詩酒風月。不過元代文壇有幸,他留下了大量詞曲和傳世雜劇,最終名列元曲四大家。
他就是跨越金、元兩朝的白樸。此人初名恆,字仁甫,後改為白樸,字太素,號蘭谷先生。單從名字的變化,便可一窺他的生平和內心世界:前者代表了儒家理念,也承載了家族的期許;後者卻是白樸主動追尋的人生理想,拋卻世俗煩惱,回歸質樸的真我。他希望自己,能像空谷幽蘭一般不媚世俗,永遠飄散著傲世清香。
在《錄鬼簿》中,編書者將白樸置於早期的名公才人作家群中,緊隨關漢卿之後,排在第二位。屬於他的輓詞這樣寫的:「峨冠博帶太常卿,嬌馬輕衫館閣情。拈花摘葉風詩性,得青樓、薄幸名。洗襟懷、剪雪裁冰。閒中趣,物外景,蘭谷先生。」身負青樓薄倖名,懷抱超然遁世心,這樣的白樸既矛盾又特別,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場曲折複雜的戲劇人生。
元白再續佳話
唐朝有惺惺相惜的大詩人元稹和白居易,世稱「元白」;到了元朝,也有著名文人元好問和白樸這對忘年之交。元好問就是那位,唱出「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的北方文壇盟主。他對白樸,如父如師,更有再造之恩。這段故事,還要從汴京(今河南開封)的壬辰之亂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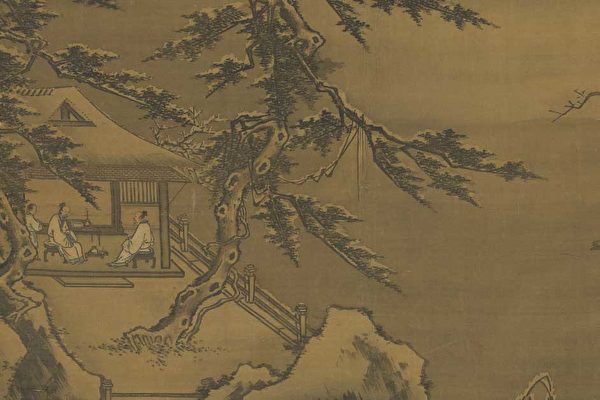
白樸雖不做官,他的家世也不簡單。金朝末年,來自山西的白氏家族已經是汴京顯赫一時的望族。白家出了兩位進士,即白樸的伯父、父親白華。白華一直在國都汴京做官,供職於樞密院,是皇帝的一位近臣。白樸的同輩、後輩,都不乏位高爵顯者,讓白氏家族成了真正書香世宦之家。而白樸身後得朝廷封贈官位,正是子輩之功。
再說白華,他在政事之餘,也喜好結交大批文士。多年以後,他回憶起在金朝的這段錦繡歲月,最感激的便是結識了大才子元好問。白樸出生時,正值家族的鼎盛之時。然而金朝氣數將盡,即使是錦衣玉食的白少爺,也難免飽嚐人世悲歡。
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蒙古大軍圍攻汴京,金兵不敵,金哀宗倉皇出逃,史稱「壬辰之亂」。白華是隨行官員,把妻兒都留在城中。蒙古兵破城後,燒殺搶掠,白樸的母親為亂兵所擄,生死未卜。父親遠走、母親失蹤,年僅七歲的白樸和姐姐瞬間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
兵荒馬亂中,元好問義不容辭收留了姐弟倆,給予妥貼的照拂和悉心的教導。無論被俘還是逃難,元好問一直把兩個孩子帶在身邊,幾經輾轉飄零,流寓山東一帶。元好問非常喜歡白樸,對他視如己出,親自教他詩文。白樸的文風就受到元氏的影響,時人更認為他就是元氏風格的繼承者。
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白樸十歲的時候,白華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元好問這才將白樸姐弟送還白家,讓父子三人團聚。白華非常感慨地歌詩致謝:「顧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從此白樸隨父親進習儒業,專攻詞賦,也是金朝科舉的考試內容。
後來,元好問也未忘記共患難的白樸小友,每次經過真定一定要去白家作客,詢問白樸的學業。白樸天資聰穎,又得元好問賞識,學業突飛猛進,年紀輕輕便聞名於世。元好問曾作詩讚他:「元白通家舊,諸郎汝獨賢。」
真定才子 不問功名
自從和白華團聚後,白樸就在真定度過了少年、青年時光。真定是元初的一個文化、尤其是雜劇中心,對白樸的創作也有很大助益。真定的繁榮主要歸功於其管理者史天澤。他是元初名將,也是元朝唯一的漢人宰相,忽必烈以大將郭子儀、曹彬比之。
史天澤治理真定時,樂善好賢,多行善政,在金元易代的亂世中打造一方安定繁榮的樂土。北方士庶慕其名,紛紛前來歸附,其中就包括楊果、王惲、張德輝、李治、王若虛、元好問等名士,當然還有白華。史天澤為這些人提供避難的棲身之所,更是將他們奉為上賓,禮遇甚厚。
此外,史天澤雅好文學,本人也是散曲作家,族中亦有創作雜劇之輩。他常常和名士們談論經史,論說風雅。這些名士除了輔佐史氏處理政事,還從事當地文化教育活動,更積極參與元曲的創作。白樸就在這個開明而風流的文學勝地成長起來,成年後亦是史天澤麾下一位文學侍從,經常隨他遊歷各地。
隨著年紀漸長,白樸堂堂男兒,自幼接受傳統儒學教育,年少時也有志於天下。然而元朝廢除科舉,父親也不再是達官顯貴,白樸雖然學識淵博,精通詞賦,憾無用武之地。不過,他的長官史天澤頗具慧眼識人之能,凡他舉薦之人,大多仕途顯達。中統二年(1261年),元世祖命各路宣撫使舉薦有文學才能的士人,供朝廷錄用。史天澤對白樸愛重已久,鄭重推薦了他。
那一年,白樸三十五歲,正值施展宏圖抱負的盛年,然而他再三辭謝,主動遠離權力中心,時人形容他「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王博文《天籟集原序》)。這樣的舉薦在他晚年還有一次,白樸仍是回絕,自斷仕進,一生布衣。一個才華橫溢的名臣之後為何這樣抗拒做官呢?
這大概與他童年飽受喪亂之苦有關,功名富貴逃不過末世悲劇,也救不了至親之人,如過眼雲煙一般飄渺虛無。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白樸懷著這種禍福無常、興亡無定之嘆,仕途之心逐漸索然。
放情山水 詩酒趁年華
不做官的日子,白樸在做什麼呢?他既清高又中庸,時人剖析他的內心世界:「既不欲高蹈遠引以抗其節,又不欲使爵祿以污其身,於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孫大雅《天籟詞後序》)身歷金朝、南宋的滅亡,白樸總是鬱鬱不樂,於是走上一條半隱半俗、詞曲自娛的遺民式生活。。

一方面,他冶遊風月,放浪勾欄,與歌兒舞女、雜劇演員相知相交。正如關漢卿有個紅顏知己朱簾秀,白樸也有個愛賞有加的天然秀。另一方面,他遁跡林泉,樂享山水,與文人墨客交遊唱和。特別是在拒絕出仕後,他更是壯遊大江南北長達二十年,飽覽自然風光。
晚年時,白樸的足跡已遍及建康、江西、九江、岳陽、揚州等名城。最終他選擇建康(今南京)作為終老之地。當時的監察師董巨源再次推薦白樸出山,他再一次毫不猶豫地謝絕,並填詞表明歸隱決心。此後,白樸與友人遊覽古蹟,吟賞山水,詩酒趁年華,走過餘生。
這樣的生活,表面上是滑稽戲謔遊戲人生,骨子裡依然是憂傷苦悶的悲涼,或者是了悟人間百味後的蕭索。這些經歷、心緒融入創作之中,也形成了白樸或奔放灑脫、或沉鬱雄渾之作。他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詞、曲、雜劇等。
在曲代詞興的金元之交,白樸仍舊偏愛填詞,把自己的一百多首詞作編成《天籟集》。而他的藝術成就主要來自元曲,他有四十多首散曲傳世,《太和正音譜》評其風格「如鵬搏九霄」,中有一股磊落磅礴之氣概;他的雜劇更屬元人第一流,其中以唐玄宗為主角的《梧桐雨》,被王國維稱讚是和《漢宮秋》《倩女離魂》比肩的千古絕品。
飄然遁隱 貧士亦風流
接下來簡要談談白樸的散曲。其作品多涉及隱逸避世、寫景詠物及歌詠戀情等內容,是元曲中常見題材,但白樸憑藉深厚的詞賦功底和超然的精神境界,形成了散曲清秀俊逸、俊爽豪放的特點。

經歷了山河易主、幼年漂泊等苦難,白樸終其一生無意於功名,時常在詞曲流露歸隱出世之意,這也是他抒懷言志,用曲詞慰藉落寞之心的方式。不過他那愁苦悲憤之情,到了形式活潑的散曲中,就轉變為看似豁達平和、實則深沉含蓄的情感。
在這類隱逸避世的作品中,白樸以冷峻客觀的目光追溯歷史,以古代著名隱士為生活的目標,表達擯棄功名利祿、追尋逍遙人生的情懷。套曲《陽春曲·知幾》中,首尾兩支曲詞頗為經典:
「知榮知辱牢緘口,誰是誰非暗點頭。詩書叢裡且淹留。閒袖手,貧煞也風流。」
「張良辭漢全身計,范蠡歸湖遠害機。樂山樂水總相宜。君細推,今古幾人知。」
所謂「知幾」,便是了解世事變化的先兆。第一支曲子中,白樸闡述自身的處世態度。知榮,是懂得盈虧消長的規律,做到持盈保泰;知辱,是懂得適可而止的道理,做到知足不辱。
作者看破世情,也懂得誰是誰非,卻三緘其口,也就是不願陷入是非恩怨的風波之中。他能做的,就是深入書山,流連詩文,做一個不問世事的長者。哪怕是家境清貧,他也獲得內心的寧靜安逸,正是「貧煞也風流」。
結尾這支曲子,作者講的是袖手旁觀、安貧樂道的深層原因。他先列舉張良辭漢、范蠡歸湖的歷史舊事,兩位定國安邦的賢士,不約而同走進山水自然的懷抱,正是看透了功名富貴之下的危機,因而都以隱士身分遠離官場,避禍全身。
白樸和古代名士的選擇,表現了淡泊名利、返璞歸真的處世哲學。然而白樸同樣感慨,這樣的大智慧,從古到今能有幾人參透?
而白樸寫景的散曲,既是他遊賞山水的生活寫照,也是他淡然忘我的情懷流露。他筆下的風景潔淨純粹,白描勾勒美景,彷彿是自然造化的再現,表現出一種無我之境。他也有一首類似馬致遠的作品《天淨沙·秋》:「孤村落日殘霞,輕煙老樹寒鴉,一點飛鴻影下。青山綠水,白草紅葉黃花。」
二人的作品,題目有一字之差,白樸少了一個「思」,便是少了主觀之情,而是用客觀真實的筆法表現秋天景色。雖然白樸同樣選用一系列精緻典型的意象,羅列鋪陳完成曲詞,但是他採用的形容詞,幾乎沒有感情色彩,意在如實表現景物特色。因而,他的文字呈現出一幅靜美雋永的秋景圖,沒有求而不得的愁悶,也沒有羈旅漂泊的孤獨。
同樣是《天淨沙》,馬致遠的作品會激發讀者強烈的情感共鳴,白樸的文字卻給人一份靜謐閒適之感,各具神采。白、馬作品的風格差異,正是由於兩人身世閱歷、性情志向的不同。讀曲亦是讀人,所謂作品的藝術風格,也正是作者精神境界的外化。白樸名如其人,曲如其人,他的一生展現了元代文人群體的又一個側面。
點閱【元曲大家】連載文章。
訂閱【古韻流芳】頻道:
https://www.ganjingworld.com/channel/1f6ohq5s6k02uAcaIynG91Ez41nq0c
責任編輯: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