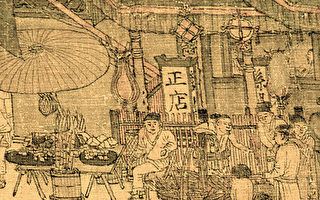趙子龍懷著幼主絕塵而去,那是野史傳奇的世界裡一個傳奇的畫面。
1.救援
當趙子龍懷裡抱著嬰孩從長坂坡殺下,像一支剪刀剪開了敵方的人陣,這割裂的速度與方向驚動了在遠方瞭望的曹操。
曹操問那是何許人?
趙子龍懷著幼主絕塵而去,那是野史傳奇的世界裡一個傳奇的畫面。我從小愛這個故事,早在當年我還讀的是少年文庫注音版《三國演義》的時候。我不喜歡迪士尼公主,我喜歡趙子龍。
策馬衝撞生死疆界,把一個孩子從亂軍之中死亡逼臨之境,帶到他父親身邊安全之地的畫面感,力道遠大過灰姑娘舞會裡悶煞人的旋轉。
不知這一切是否對性別認知造成過影響,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幾乎所有我們當時能接觸到的讀物,英雄都是男身。另一個我喜歡的人物是成吉思汗鐵木真,也是個策馬的傢伙。
我從沒想過,這些書中偶像是否殺伐之氣太重對一個女孩而言。但如今想起來,趙子龍和鐵木真又不太一樣。他是個不一樣的英雄,他沒有那麼大的帝國。
他也不像三國裡的其他人如劉、關、張,有比較多戰場外的戲分。他在戰場之外的形象很模糊,出場時幾乎都是緊張的決戰時刻,甚至是危局。千鈞一髮中趙雲忽然關鍵性地殺出,情勢為之一變。
趙子龍在《三國演義》中的第一次出場,是作為公孫瓚的部下。
白馬將軍公孫瓚和袁紹發生軍事衝突,袁紹的大將文丑殺入公孫軍陣中,公孫瓚本人被打得丟盔落馬,滾下山坡,性命垂危之際,忽有一騎人馬從旁切入,硬是擋下文丑,救了公孫瓚性命。這人就是趙子龍。
那時趙雲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感謝救命之恩的同時,也拔擢他當軍官,安排他統領一支兵馬,繼續在第二天的戰局裡效命。不過畢竟是新來的,在排陣形時,就把趙雲排在後軍。
公孫軍的陣形漂亮,帥旗在風裡獵獵作響十分顯眼。顏良、文丑設下埋伏,引公孫瓚深入,鞠義衝上前來砍倒帥旗,公孫軍立刻陣腳大亂。混亂之中又是趙雲單騎快馬趕來護主,刺死鞠義。這一下穩住陣腳,公孫軍反轉情勢,拿下一勝。
在公孫瓚身邊立下這兩次擎天保駕之功,但彷彿趙雲也就不欠公孫瓚什麼了。後來他遇見劉備,感覺他和劉備之間是立即就有了默契,決定這是他想跟的人。加入劉備軍不久,就有長坂坡救阿斗的戰績。那又是一次救人的逆襲,也是趙雲最出名的一戰。
這幾次危機中的出場,給人一種印象:這是個擅長救援的戰將。他統領的兵馬不必多,但總是快。目標明確,救人便走,不戀多餘的戰。入則如入無人之境,出則全身而出。
為什麼會想到說這些?這幾天,我開始想起我小時候心目中的英雄。但那時我知道的只是少年文庫注音版裡的趙雲。一個簡單鮮明的救人者。有一點遭人誤會的悲劇性(他在逆勢衝入敵陣救阿斗的路上,被誤會為投敵去了),更多些不瞻前顧後的勇敢果決。心念一動就出手了,沒有拖泥帶水的空間。因為是救人,這決絕並不讓人感覺是任性妄為。
或許複習小時候的英雄,也是成長變化的一部分吧!決定他繼續是你的英雄,或是承認自己小時候很傻、很膚淺。
也有第三種可能,你變了,但英雄也變了,在你的認識裡默默地轉變,彷彿他和你一起長大了。你還是認他為英雄,但理由和小時候完全不同。他和你一起變化了模樣。
2.善後
我對趙雲的重新想像,從他離開公孫瓚的理由開始。
公孫瓚是個極修邊幅的人,沒落的貴族出身,外表好看。但在趙雲救援了公孫瓚兩場戰役後,他或許發現,公孫瓚的白馬部隊、紅底金字的帥旗,好像並不實用。
不是說,軍隊的外表威嚴沒有用。聽說當年公孫瓚守遼西,烏桓族人吃過敗仗,從此記得了白馬將軍的厲害。白馬成了一個符號,足以嚇退烏桓人。但倘若實力不足以在一開始樹立這符號,恫嚇便屬無稽,接下來死的是誰就不知道了。
帥旗本來應該是震懾對方用的,結果反而暴露主帥的位置,旗子一倒又滅自己士氣。趙雲開始覺得,公孫瓚執著於這些形式的美,有一天會害死自己。即使,他也喜歡白馬,也喜歡看旗幟在風中獵獵地翻飛。但為了在戰場上活命,帶著自己的人馬活命,有一天這些都得拋棄。
不,不是有一天。是在現在,這一秒鐘,立刻判斷:什麼是重要的,什麼不是。不重要的事物,絕不能讓它在戰場上絆住自己。
後來趙雲聽說公孫瓚兵敗,縊死妻女、姊妹後點火自焚。他不意外,這一切符合他預見的公孫瓚的死法,這一切十分公孫瓚。寧願自焚而死,不願落於敵手,有一種潔癖的美,屬於白馬將軍的潔癖。他沒有從自己創造的符號裡脫身。
但戰場不是個清潔的地方。公孫瓚身上的火焰還沒熄滅,敵軍便一擁而上,砍下他的首級。那並不是基於讓公孫瓚解脫的願望,只是為了陣前爭功搶得敵帥首級。
公孫瓚滾燙的頭顱被幾個士兵拋來搶去,黑血從嘴、耳朵、斷掉的脖子切口湧出,皮肉發出難聞的焦味,非常不美。
非常不美。這些,他彷彿看見。在他虛構的記憶裡,知道會有這麼一種結局的選項。也許趙雲也曾一度猶豫了,他應該在記憶裡也扮演一個救援者嗎?
他應該阻止自己去想到那些最壞的、最惡的可能,或是他該任由一切心象起落經過,因為惡也是世界眾多可能性的一部分、不知惡便不知善、不知死之悲便不知生之歡?他能同時救援現實與想像嗎,或者他只能二擇一,人一次只能在一個時態裡活?
這些不是趙子龍,是我懷疑過的事。
因為這些懷疑我想像了趙子龍,想像當他離開公孫瓚去奔劉備時,那是一個時間的分歧點。那時他知道了、或選擇了,對他而言虛幻的是什麼?
他從那個虛幻的陣營脫出,從此不再救援它。將所有的力量投注在唯一的現實:這些真實的片刻,戰場上的血腥氣、塵土、耳邊響起的嚎哭、從頭頂掠過的箭矢、持槍痠疼的臂膀、懷裡嬰孩的溫度。
另一個在歷史紀錄上浮現的趙雲形象,是低調謹慎而理性的。箕谷之役後諸葛亮問鄧芝,為什麼此役雖寡不敵眾,而仍能編制整齊地撤退。鄧芝答,因為是趙雲親自斷後的緣故。
小時候喜歡,書裡那個孤軍深入,破敵救援的趙雲。但少年文庫注音版《三國演義》不會寫到他的另一面:那個善於固守、撤軍斷後的趙將軍,那是少年文庫讀者還無法領會的價值。
他不只是搶救者,也是個照顧者、固守者。
然而這些也是符號。這個月夜結束以前,我也要輕身而過,從我創造的符號……◇
——節錄自《比霧更深的地方》/ 木馬文化出版公司
(<文苑>選登)
責任編輯: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