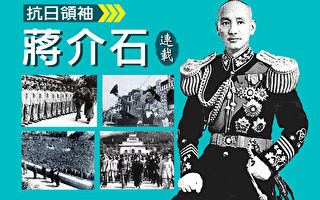第四節 薛伯陵長沙展軍威
二、不堪回首的長沙大火
抗日衛國戰爭正當同日寇酣戰之際,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三日凌晨在長沙發生了一場人為的毀滅性大火。因為十二日所發的電報代碼是「文」,大火又發生在十二日的夜裏(即夕),所以這場大火又稱為「文夕大火」。火勢猛烈,持續數日,人員、房屋、物資損失慘重。
陳誠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感慨萬端地說,抗戰八年,有兩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銘甘心作漢奸,一件就是張治中長沙放火。
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後,統帥部原本預定設於湖南長沙,不料就在其時發生了長沙大火,於是蔣委員長飛駐衡山,轉往重慶。
據《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中史料記載,長沙大火,原是張治中等人之陰謀,聲言日本軍隊已過新牆河,應當堅壁清野,仿照俄共對抗德軍之策略,若倭寇進攻長沙,應採行「焦土政策」,燒光長沙再撤退。於是張治中便一面秘密命令準備許多放火材料,如汽油、破布……等;一面將警衛團士兵分編為三人一個小組,名之為放火小組,命令如見市區內起火,便以之為信號,大家即對市內重要設施目標一齊縱火。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張治中曾召集湖南各廳處長委員齊集在城外省主席官邸開會,會上張治中指示說:「日軍已由岳州南下,過新牆河,省府還是先撤退到湘西沅陵去較妥,我與財政廳尹廳長暫留在長沙,秘書處酌留一兩位秘書及科員待命。其餘由秘書長廳長率領,當晚出發前往沅陵,至遲在明晨必須完成撤退事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8.《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P328-329)
就在這次省府會議上,關於有計劃縱火焚燒長沙城,事關長沙市民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張治中竟不作說明,更未做行動前必須提前發出警報、通報市民的任何安排。
張治中也並未暫留長沙,而是會後即暗中走往湘潭,對他採用的「焦土政策」,對長沙市民毫無預告指導疏散措施,就這樣,在歷史上不能不給世人留下「蓄意使全市人民生命財產在敵人未來之前,先一律葬身火海」的事實。
「十二月(應為十一月,可能是排版出錯。)十二日晚上十二點半左右,所謂「文夕大火」,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未料此時南門外傷兵醫院,突然失火發生火警。於是警衛團放火小組的士兵,誤認為就是信號,乃照預定計劃紛紛放起火來。加上事先既未對市民預告和指導疏散措施,軍警間也無聯繫,以致火舌席捲了整個長沙城。在午夜二時三十分左右,張治中的副官敲他的房門,報告長沙城內有大火。此時張治中在湘潭還假裝不知道有這回事,就披衣下床,假惺惺打電話到警備司令部查詢。……隔了一小時,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匆匆忙忙坐車趕向張治中請示: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酆悌司令也正是在睡夢之中被驚醒的,立即發動消防人員及警察局警衛團人員分頭救火,可是哪裏救得熄呢?救的救,縱的縱,亂成一團,一直燒到第二天下午,火勢才慢慢緩下來,然而長沙城中,八角亭、中正路、南正路一帶街市及機關、官署、學校、第一紗廠……等等,都已化為灰燼,全城精華變為頹垣殘壁,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最可憐的是老百姓,事前不知道,許多人關上了門在屋內做好夢,臨時單身逃命或葬身火海的軍民為數不少。此次大火對民心士氣之影響極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8.《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P329-330)
至於十二夜裏火警的起源究竟是甚麼,實際上是一個歷史之謎,不過一般的說法是由傷兵醫院不慎失火引發而起的。十三日大火整整燒了一天,十四日以後火勢始漸小,直到十六日猶有未熄之餘燼。
文夕大火,長沙全城近七百條街道被燒得片瓦不存,五百多條街道僅存幾棟房屋;明德中學、周南中學等數十所學校變成廢墟;兩千多年的賈誼故居付之一炬;千年名樓定王臺連同所藏的萬卷善本古籍,在大火中毀之殆盡;全市250多家米廠、糧行燒掉谷米190多萬擔,損失銀元1000萬元以上;大火中所有湘繡繡庄連同繡品、畫稿無一倖存。長沙有名的江西富商余太華金號,其珍藏的國寶44顆漢印,在大火中連同保險櫃一起被熔化成銅塊鐵餅。上述損失雖說巨大慘烈,但畢竟是物質上損失,可以用金錢來計算,令人最為痛心的是數萬同胞葬身火海,成為中華民族最為痛心的傷痕。
「所謂「民主將軍」張治中早已喪失人格,其禍國殃民,長沙大火即為明顯之一例。大火後第四天,即十二月(應為十一月,可能是排版出錯。)十六日,蔣委員長驚聞其訊,親由南嶽趕到長沙,視察火災狀況,並慰問民眾,市內遍地瓦礫,步履困難,目擊慘狀心酸,忍不住落淚。當時想設一個茶會招待受火災之難民及尚留在長沙的外僑,哪知道連茶葉都買不到。後來還是在一位教友家中,邀請居留在長沙的外僑們茶會,親自表達沉痛遺憾之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8.《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P330)
此時陳誠是第九戰區的司令長官,長沙是第九戰區的心臟地帶,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給長沙民眾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的大火,職責所在,不能置身事外,乃於十七日上書自劾,書云:
「委員長蔣鈞鑒:此次長沙有計劃、有組織之暴行,其慘狀令人聞而心酸,何況目睹?影響所及,足使軍心動搖、民眾失望,顯可成為抗戰之危機。昨聞鈞座蒞臨,實不勝喜懼。喜者,必有以昭示天下而挽人心也;懼者,此種慘狀,鈞座目睹,必增加煩惱與 憂慮也。今數聆訓示,僅及掃街、巡查、救護、警戒、收容等末節,則鈞麾似無蒞止長沙之必要矣。以職之愚,實深感姑息優容、諱疾忌醫之非計,憂憤曷勝!竊維一切大計,鈞座固自有成竹,今日職之態度,自知失體,顧心所謂危,不能不痛切陳之。尤懇明令處職以應得之罪,以慰湘民,而定軍心,迫切陳詞,伏維垂察。謹此,敬叩鈞安。」 (《陳誠回憶錄》(十五): 長沙大火)
陳誠將軍非常痛心的對部屬說,僅僅為了堅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燒城,並不計較有無成效,致使萬萬千千無辜的人民作毫無代價的犧牲,這就談不到甚麼計劃或政策了,而是一種無可原恕的殘暴。「為成功不擇手段」,我們猶且以為不可,何況既不擇手段,又不能成功,這豈是有天良的人所忍出此!有知識的人所肯出此!
「長沙大火」是一樁空前大案,自然要嚴辦。軍法單位會審結果,警備司令酆悌處有期徒刑十年,警衛團長徐昆、警察局長文重孚各判有期徒刑七年。專案呈報最高當局核示,奉批:「瀆職殃民,一律槍決,張治中撤職查辦。」長沙大火,最高當局揮淚斬馬謖,非如此緊急處置不足以平息輿情。
「 書上,委員長令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嚴懲肇事人員。二十日,軍法會審訊結: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判處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革職留任,責成善後。以此為斷,罪魁禍首應當是酆悌以下三人,但省主席張治中又為甚麼革職留任呢?倘因其為主使者,則罪應在酆等三人之上;倘如全不知情,似又不應有罪。於是街談巷議頗不以此種處置為然,公開張貼文字詆斥張治中者,隨處可見。有一副嵌入張治中姓名的聯語及橫額,最為一時傳誦。聯云:「治績雲何,兩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云:「張皇失措」。即就文字而論,亦是可傳之作。兩大政策雲者,張於到任之初,即宣佈組織全省民眾抗日救國自衛團,歸他自己統率,此其一;再則就是宣佈於寇兵進犯之時,實行焦土政策,此其二。這兩大政策之前者,未聞有何交代,大概是說說算了。後者算是兌現了,但卻是在寇軍並未進犯之時付諸實施的,未免荒唐得出奇。」 (《陳誠回憶錄》(十五): 長沙大火)
據說,長沙大火酆悌並不是主謀,勉強說只能是個從犯,因為他是長沙警備司令,直接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張治中指揮,而張治中之所以要他放火,是因為匪諜故意造謠,說敵人已越過新牆河,以為新牆河距長沙很近,無險可守,張治中就下達亂命,禍國殃民了。
「酆悌一身承擔,頗有好漢氣概,酆悌個性固然如此,但其中尚有內幕。當在大火發生後,張治中自知難逃法律制裁,乃先把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找來,當面同他們商量,認為在蔣委員長震怒之下,沒人敢出面說情,唯一的辦法只有他置身事外,方可向委員長為他們三人求情。酆悌等三人認為也只好如此,攀上張治中則四人同死,不攀張治中也許還有一線生機,這是酆悌等為張治中洗脫之原因。但張治中脫罪後,根本就未為酆悌等人去求情,也許正是他事先早已安排之脫身毒計,這種毫無人格的人,其狠毒心腸,也非常人可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8.《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P331)
陳誠在其回憶錄中說,他十三日午間見到了張治中,問起大火起因,他說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統所為,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真虧他說得出口!
毫無疑問,長沙大火之發生,是抗戰八年中一大慘劇,對民心士氣之打擊實在太大,當時不少人的內心中曾有這樣一個問號?像這樣不負責任的張治中,如何能帶好兵?又如何能打勝仗?!
文夕大火雖然將古老的長沙毀滅了,但嗣後薛岳將軍同日寇廝殺中的長沙三次大捷,可昭告天下,古老的長沙浩氣永存。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五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