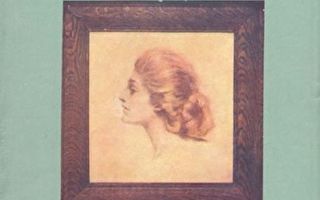八 長鏈(5)
珂賽特,雖然感受有所不同,但也一樣膽戰心驚。她不懂這是什麼,她吐不出氣,感到她所見到的景像是不可能存在的,她終於大聲問道:「爹!這些車子裡裝的是什麼?」
冉阿讓回答說:「苦役犯。」
「他們去什麼地方?」
「去上大橈船。」
這時,那一百多根棍棒正打得起勁,還夾著刀背也在砍,真是一陣鞭抽棍打的風暴,罪犯們全低下了頭,重刑下面出現了醜惡的服從,所有的人一齊靜下來了,一個個像被捆住了的狼似的覷著人。珂賽特渾身戰抖,她又問道:「爹,這些還算是人嗎?」
「有時候。」那傷心人說。
那是一批犯人,天亮以前,便從比塞特出發了,當時國王正在楓丹白露,他們要繞道而行,便改走勒芒大路。這一改道便使那可怕的旅程延長三至四天,但是,為了不讓萬民之上的君王看見酷刑的慘狀,多走幾天路便也算不了什麼。
冉阿讓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裡。這種遭遇是打擊,留下的印象也幾乎是震撼。
冉阿讓帶著珂賽特一路走回家,沒有留意她對剛才遇見的那些事再提出什麼問題,也許他過於沉痛了,在不能自拔的時候,已聽不到她說的話,也無心回答她了。不過到了晚上,當珂賽特離開他去睡覺時,他聽到她輕輕地,彷彿自言自語地說:「我感到,要是我在我的一生中遇上一個那樣的人,我的天主啊,只要我走近去看一眼,我便會送命的!」
幸好,在那次慘遇的第二天,現在已想不起是國家的什麼盛典,巴黎要舉行慶祝活動,馬爾斯廣場閱兵,塞納河上比武,愛麗捨官演戲,明星廣場放焰火,處處懸燈結綵。冉阿讓,橫著一條心,打破了他的習慣,領著珂賽特去趕熱鬧,也好借此沖淡一下對前一天的回憶,要讓她遇見的那種醜惡景象消失在巴黎傾城歡笑的場面裡。點綴那次節日的閱兵式自然要使戎裝盛服在街頭穿梭往來,冉阿讓穿上了他的國民自衛軍制服,心裡隱藏著一個避難人的感受。總之,這次遊逛的目的似乎達到了。珂賽特一向是以助她父親的興作為行動準則的,並且對她來說,任何場面都是新鮮的,她便以青年人平易輕鬆的興致接受了這次散心,因而對所謂公眾慶祝的那種乏味的歡樂,也沒太輕蔑地撇一下嘴。因此冉阿讓認為遊玩是成功的,那種奇醜絕惡的幻象已不再存在了。
過了幾天,在一個晴朗的早晨,他們兩人全到了園裡的台階上,這對冉阿讓自定的生活規則和珂賽特因煩悶而不出臥房的習慣來說,都是又一次破例的表現。珂賽特披一件起床時穿的浴衣,那種像朝霞蔽日那樣把少女們裹得楚楚動人的便服,立在台階上,睡了一個好覺而顯得緋紅的臉對著陽光,老人以疼愛的心情輕輕地望著她,她手裡正拿著一朵雛菊,在一瓣一瓣地摘花瓣。珂賽特並不知道那種可愛的口訣「我愛你,愛一點點,愛到發狂,」等等,誰會教給她這些呢?她本能地、天真地在玩著那朵花,一點沒有意識到:摘一朵雛菊的花瓣便是披露一個人的心。如果有第四位美惠女神,名叫多愁仙子而且是微笑著的,那她就有點像這仙子了。冉阿讓癡癡地望著那花朵上的幾個小手指,望到眼花心醉,在那孩子的光輝裡把一切都忘了。一隻知更鳥在旁邊的樹叢裡低聲啼唱。片片白雲輕盈迅捷地飄過天空,好像剛從什麼地方釋放出來似的。珂賽特仍在一心一意地摘她的花瓣,她彷彿在想著什麼,想必一定是件怪有意思的事,忽然,她以天鵝那種舒徐的優美姿態,從肩上轉過頭來向冉阿讓說:「爹,大橈船是什麼東西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