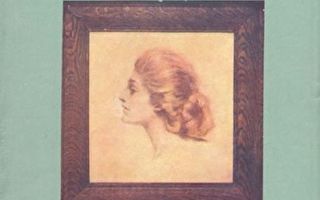五 歷史所自出而為歷史所不知的事物(4)
快到工人們休息時,有人看見兩個人在比克布斯便門和夏朗東便門之間,在兩堵牆間的一條巡邏小道旁的一家大門前、有一套暹羅遊戲的飲料店附近碰頭。一個從工作服下取出一支手槍,把它交給另一個。正要給他時,他發現胸口上的汗水把火藥浸潮了一點。他重新上那支手槍,在藥池裡原有的火藥上添上一些火藥。隨後,那兩個人便分頭走開了。
一個名叫加雷、日後四月事件發生那天在博布爾街被殺的人,常誇口說在他家裡有七百發子彈和二十四顆火石。
政府在某天得到通知說最近有人向郊區散發了一些武器和二十萬發槍彈。一星期過後,又散發了槍彈三萬發。值得注意的是,警察一點也沒有破獲。一封被截留的信裡說:「八萬愛國志士在四個鐘頭以內一齊拿起武器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所有這些醞釀活動全是公開的,幾乎可以說是安然無事的。即將發作的暴動從容不迫地在政府面前準備它的風雷。這種仍在暗中進行、但已隱約可見的危機可說是無奇不有。資產階級泰然自若地和工人們談論著正在準備中的事。人們問道:「暴動進行得怎麼樣了?」問這話的語氣正如問:「您的女人身體健康吧?」
莫羅街的一個木器商人問道:「你們幾時進攻呀?」
另一個店舖老闆說:「馬上就要進攻了。我知道。一個月以前,你們是一萬五千人,現在你們有兩萬五千人了。」他獻出了他的步槍,一個鄰居還願意出讓一支小手槍,討價七法郎。
總之,革命的熱潮正在高漲。無論是在巴黎或法國,沒有一處能例外。動脈處處在跳動。正如某些炎症所引起、在人體內形成的那種薄膜那樣,秘密組織的網已開始在全國四散蔓延。從那既公開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產生了人權社,這人權社曾在它的一份議事日程上寫上這樣的日期:「共和紀元四十年雨月」,雖經重罪裁判所宣判勒令解散,它仍繼續活動,並用這樣一些有意義的名稱為它的小組命名:
長矛。
警鐘。
警炮。
自由帽。
一月二十一。(1)
窮棒子。
流浪漢。
前進。
羅伯斯庇爾。
水平儀。
《會好的呵》。
(1)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刑。
人權社又產生了行動社。這是一些分化出來向前跑的急躁分子。另外還有一些社在設法從那些大的母社中徵集社員。組員們都因為此拉彼扯而感到為難。例如高盧社和地方組織委員會。又如出版自由會、個人自由會、人民教育會、反對間接稅會。還有工人平等社,曾分為三派,平等派、共產派、改革派。還有巴士底軍,一種按軍隊編制組合的隊伍,四個人由下士率領,十個人由中士率領,二十人由少尉率領,四十人由中尉率領,從來沒有五個以上互相認識的人。一種小心與大膽相結合的創造,似乎具有威尼斯式的天才。為首的中央委員會有兩條手臂:行動社和巴士底軍。一個正統主義的組織叫忠貞騎士社,在這些共和主義的組織中蠕蠕鑽動。結果它被人揭發,並被排斥。
巴黎的這些會社在一些主要城市裡都建立了分社。里昂、南特、裡爾和馬賽都有它們的人權社、燒炭黨、自由人社。艾克斯有一個革命的組織叫苦古爾德社。我們已經提到過。
在巴黎,聖馬爾索郊區比聖安東尼郊區安靜不了多少,學校也並不比郊區平靜多少。聖亞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館和聖雅克馬蒂蘭街的七球檯咖啡館是大學生們的聯絡站。跟昂熱的互助社以及艾克斯的苦古爾德社結盟的ABC的朋友們社,我們已經見過,常在繆尚咖啡館裡聚會。這一夥年輕人,我們以前曾提到過,也常出現在蒙德都街附近一家酒店兼飯館的稱作科林斯的店裡。這些聚會是秘密的。另一些會卻盡量公開,我們可以從日後審訊時的這段口供看出他們的大膽:「會議是在什麼地方舉行的?」「和平街。」「誰的家裡?」「街上。」「到了哪幾個組?」「只到一個組。」「哪一個?」「手工組。」「誰是頭兒?」
「我。」「你太年輕了,不見得能單獨一人擔負起這個攻擊政府的重大任務吧。你接受什麼地方的指示?」「中央委員會。」
日後從貝爾福、呂內維爾、埃皮納勒等地發生的運動來判斷,軍隊和民眾一樣,也同時有所準備。人們所指望的是第五十二聯隊、第五、第八、第三十七、第二十輕騎隊。在勃艮第和南方的一些城市裡,種植了自由樹,也就是說,一根頂著一頂紅帽子的旗桿。
當時的局勢便是這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