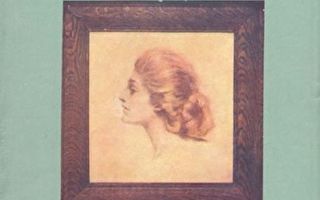二十 陷害(7)
德納第說得對,這一細節是實在的,儘管馬呂斯在慌亂中沒能察覺出來。白先生只稍稍說過幾句話,並且沒有提高過嗓子,更怪的是,即使是在窗口旁和那六個匪徒搏鬥時,他也緊閉著口,一聲不吭。德納第繼續說:「我的天主!您原可以喊上一兩聲『搶人啊』,我決不會感到那有什麼不妥當。救命啊!在這種情況下是誰也要喊的,在我這方面,我絕對不會說這不應該。當我們看見自己遇到了一些不能使我們十分相信的人時,我們哇哩哇啦一陣子,那原是非常簡單的。要是您那麼做了,我們也不會打擾您的。連一個塞子我們也不會塞到您的嘴裡。讓我來告訴您這是為什麼。因為這屋子是間啞屋子。它只有這麼一個優點,但是它有這個優點。這是間地窨子。您就在這裡丟一個炸彈吧,最近的警察哨所聽了,也只當是個酒鬼的鼾聲。在這裡,大炮也只『呯』那麼一下,雷也只『噗』那麼一下。這是個舒服的住處。但是,總而言之,您沒有喊一聲,這樣最好,我佩服您的高明,我並且要把我從這裡得出的結論說給您聽:我的親愛的先生,要是您喊,誰會來呢?警察。警察來過以後呢?法律制裁。因而您沒有喊,足見您並不比我們更樂於看見警察和法律制裁來到我們身上。也可以看出——我早已懷疑到這一點——由於某種利害關係,您就有某種東西需要加以隱藏。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也有同樣的利害關係。因此我們是可以談得攏的。」
德納第一面這樣談著,他那雙盯著白先生的眼睛,彷彿也在著意要把從它瞳孔裡冒出的尖針一一刺到他俘虜的心裡去。此外,他所用的語言,雖然帶著一種溫和而隱蔽的侮辱意味,卻是含蓄的,幾乎是經過一番斟酌的。這人。剛才還只是個盜匪,現在在我們的印象中卻是個「受過傳教士教育的人」了。
那俘虜所保持的沉默,他的那種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來堅持的戒備,對叫喊這一極自然的動作的抗拒,這一切,我們應當指出,對馬呂斯都是不愉快的,並且使他驚訝到了痛苦的程度。
這個被古費拉克栽上「白先生」綽號的人,在馬呂斯的心目中,原是一個隱現在神秘氛圍中的嚴肅奇特的形象,現在經過德納第的這一切合實情的觀察,馬呂斯感到更加看不清楚了。但是,不管他是什麼人,他雖已受到繩索的捆綁,劊子手的層層包圍,半陷在,不妨這樣說,一個隨時往下沉的土坑裡,無論是在德納第的狂怒或軟磨面前,這人始終巋然不動,馬呂斯此時也不能不對這沉鬱莊嚴的容貌肅然起敬。
這顯然是個恐懼不能侵襲,也不知什麼叫驚慌失措的心靈。這是一個那種能在絕望的環境中抑制慌亂情緒的人。儘管情況是那麼極端凶險,儘管災難是那麼無可避免,這裡卻一點也沒有象慘遭滅頂的人在水底下睜著一雙驚駭萬狀的眼睛的那種悲痛神情。
德納第從容不迫地站起來,走向壁爐,挪動屏風,把它靠在爐旁的破床邊上,讓燒著一爐旺火的鐵皮爐子露出來,被綁的人完全可以看見躺在爐子裡的那把已經燒到發白、密密麻麻散佈著許多小紅點的鈍口鑿。(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