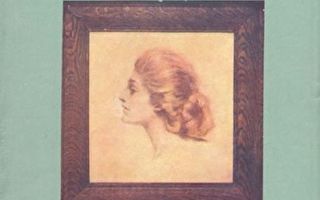二 當年的一個紅鬼(1)
當年如果有人經過小城韋爾農,走到那座宏大壯麗的石橋上去遊玩(那座橋也許不久將被一道醜惡不堪的鐵索橋所替代),立在橋欄邊往下望去,便會看到一個五十左右的男子,戴一頂鴨舌帽,穿一身粗呢褂褲,衣衿上縫著一條泛黃的紅絲帶,腳上穿的是木鞋,他皮膚焦黃,臉黝黑,頭髮花白,一條又闊又長的刀痕從額頭直到臉頰,彎腰,曲背,未老先衰,幾乎整天拿著一把平頭鏟和一把修枝刀在一個小院裡踱來踱去。在塞納河左岸橋頭一帶,全是那種院子,每一個都有牆隔開,順著河邊排列,像一長條土台,全都種滿花木,非常悅目,如果園子再大一點,就可以叫做花園,再小一點,那就是花畦了。那些院落,全是一端臨河,一端有所房子的。我們先頭說的那個穿短褂和木鞋的人,在一八一七年前後,便住在這些院子中最窄的一個,這些房屋中最簡陋的一所裡。他獨自一人住在那裡,孤獨沉默,貧苦無依,有一個既不老又不年輕,不美又不醜,既不是農民又不是市民的婦人幫他幹活。他稱作花園的那一小塊地,由於他種的花的艷麗,已在那小城裡出了名。種花是他的工作。
由於堅持工作,遇事留意,勤於灌溉,他居然能繼造物主之後,培植出幾種似乎已被大地遺忘了的鬱金香和大麗菊。他能別出心裁,他漚小綠肥來培植一些稀有珍貴的美洲的和中國的灌木,在這方面他超過了蘇蘭日.波丹。夏季天剛亮,他已到了畦埂上,插著,修著,薅著,澆著,帶著慈祥、抑鬱、和藹的神氣,在他的那些花中間來往奔忙,有時又停下不動,若有所思地捱上幾個鐘頭,聽著樹上一隻小鳥的歌唱或別人家裡一個小孩的咿呀,或呆望著草尖上一滴被日光照得像鑽石一樣的露珠。他的飲食非常清淡,喝奶的時候多於喝酒。淘氣的孩子可以使他聽從,他的女僕也常罵他。他簡直膽小到好像不敢見人似的,他很少出門,除了那些敲他玻璃窗的窮人和他的神父之外,誰也不見。他的神父叫馬白夫,一個老好人。可是,如果有些本城或外來的人,無論是誰,想要見識見識他的鬱金香和玫瑰,走來拉動他那小屋的門鈴時,他就笑盈盈地走去開門。這就是那個盧瓦爾的匪徒了。
假使有人,在那同一時期,讀了各種戰爭回憶錄、各種傳記、《通報》和大軍戰報,他就會被一個不時出現的名字所打動,那名字是喬治.彭眉胥。這彭眉胥在很年輕時便已是聖東日聯隊裡的士兵。革命爆發了。聖東日聯隊編入了萊茵方面軍。君主時代的舊聯隊是以省名為隊名的,君主制被廢除後依然照舊,到一七九四年才統一編製。彭眉胥在斯比爾、沃爾姆斯、諾伊施塔特、土爾克海姆、阿爾蔡、美因茨等地作過戰,在美因茨一役,他是烏沙爾殿後部隊二百人中的一個。他和其他十一個人,在安德納赫的古壘後面阻擊了赫斯親王的全部人馬,直到敵人的炮火打出一條從牆垛到斜堤的缺口,大隊敵兵壓來後他才退卻。他在克萊貝爾部下到過馬爾什安,並在蒙巴利塞爾一戰中被銃子打傷了胳膊。隨後,他轉到了意大利前線,他是和茹貝爾保衛坦達谷的那三十個衛隊之一。
由於那次戰功,茹貝爾升了准將,彭眉胥升了中尉。在洛迪那天,波拿巴望見貝爾蒂埃在炮火中東奔西突,誇他既是炮兵又是騎兵又是衛隊,當時彭眉胥便在貝爾蒂埃的身旁。他在諾維親眼見到他的老長官茹貝爾將軍在舉起馬刀高呼「前進!」時倒了下去。在那次戰役裡,由於軍事需要,他領著他的步兵連從熱那亞乘著一隻帆船到不知道哪一個小港口去,中途遇見了七八艘英國帆船。那位熱那亞船長打算把炮沉到海裡,讓士兵們藏在中艙,偽裝成商船暗地溜走。彭眉胥卻把三色旗繫在繩上,升上旗桿,冒著不列顛艦隊的炮火揚長而過。駛過二十海里後,他的膽量更大了,他用他的帆船攻打一艘運送部隊去西西里的英國大運輸艦,並且俘虜了那艘滿載人馬直至艙口的敵船。(待續)